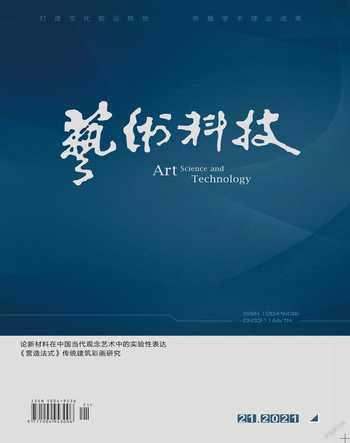族群認同意識下的怎雷村散雜居苗族的文化傳承問題
張晨 彭學艷
關鍵詞:族群;族群認同;怎雷村苗族;散雜居;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21-00-03
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城鎮化進程持續推進,信息技術不斷發展,身處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我國族群隨著社會環境與歷史進程而發生改變。當前我國社會經濟、文化均在發生變化,這使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更為頻繁,有些文化甚至相互交融,因此族群認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基于這樣的現實情況,再結合學者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文章就族群認同意識下的中國怎雷村苗族作為脫離苗族聚居主體區的散雜居族群如何傳承文化問題進行探究。
1 怎雷村散雜居苗族的現狀
1.1 怎雷村的基本概括
三都水族自治縣都江鎮怎雷村位于中國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內,以寨中年長居住者的敘述為依據,再結合田野調查信息判斷,怎雷村村寨在清朝康熙年間就已出現,距今有300余年歷史。怎雷村是少數民族聚居地,生活著水族、苗族等少數民族。其中,水族人口占總人口數的65%,苗族人口占35%。在怎雷村中,水族、苗族共同居住已有300余年,寨中的居民可以使用水語、苗語以及漢語進行日常溝通交流。水族、苗族居民已經熟悉對方的語言。怎雷村位于邊遠山區,交通閉塞,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因此水、苗兩族的傳統文化習俗得以完整保存。長時間以來,怎雷村的水族、苗族居民和諧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團結友愛。由于生活在共同的地域環境中,生產生活的方式也基本一致,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民族間文化的交融,但即便如此,三都怎雷村的水族和苗族依然保留著獨具特色的民族風俗文化。
1.2 怎雷村苗族的散雜居特性
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環境的動蕩變化導致人口遷移,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不同于聚居民族,散雜居是我國人口居住分布的主要形式之一。徐光有和袁年興在《散雜居民族的共生和內生》一文中對“散雜居”這個概念有較為全面的闡釋:“散雜居”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分散混合分布和居住的狀況[1]。形成這些特點的原因跟我國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共同影響相關。正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各個民族的分布與居住呈現散雜居是較為常見的現象。其中“散雜居少數民族”是在我國少數民族居住分布情況的界定中常常使用的一個概念。關于“散雜居少數民族”的解釋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事務委員會網站:一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數民族;二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內但不實行自治的少數民族。怎雷村苗族居住于三都水族自治縣都江鎮怎雷村,并且三都水族自治縣隸屬于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完全符合“散雜居少數民族”這個概念。許憲隆在國家民委九五重點課題“民族地區近現代化模式研究”中認為:我國散雜居少數民族分布具有廣、多、雜、散、偏、弱等特點。怎雷村苗族脫離苗族聚居主體區,居住分布相較于苗族聚居主體區來說體現了“散”這個特點;怎雷村地處三都水族自治縣,水族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部分,民族種類上體現了“雜”這個特點;怎雷村還受限于較為惡劣的生存環境,地處邊遠山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體現了“弱”這個特點[2]。此外,怎雷村是兩個族群共同生活的村寨,水族人口占大多數,因此怎雷村苗族在日常生活中與水族的交往更頻繁、更緊密。
2 怎雷村散雜居苗族的族群認同
2.1 族群的定義
“族群”這個概念最先是由西方學者提出并解釋的,一般指生活方式或文化與其他團體存在差異的團體,是多種群體分類的一種方式。群體以語言和文化認同為特征,主要強調的是一定社會群體的文化特征。專攻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周大鳴教授認為:“族群”是指一個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的一種群體。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地域環境中,“族群”一般用來指稱少數民族[3],而“民族”更多指具有或者有資格具有國家地位的族群、多族群共同體或者人類共同體。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是具有國家地位的多族群共同體,而56個民族則是居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族群。由此可見,“族群”是一個含義極廣并動態活性發展的概念,是一種構建在身份認同基礎上的共同體。
2.2 族群認同理論
因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族群內部也隨之發生著或多或少的變化,而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也更為頻繁,有些文化甚至相互交融,因此族群認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新編21世紀社會學系列教材《人類學通論》第四版對族群認同作了如下闡釋:族群認同并不是為了認同本身,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原生的、象征的情感。族群認同以族群意識為前提,“認同”作為人們社會經驗中積累起來的一種觀念意識,最早應用于哲學和心理學研究領域。后來又逐步擴展到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領域,主要反映的是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社會學中的“認同”這一概念強調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而構成族群認同的文化因素有人們相同的歷史、相同的居住環境、相同的語言、相同的信仰、相同的習俗等,這些因素也體現在歷史文化傳統和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換句話說,族群認同是群體內部對自身的認知以及與外部環境相互影響的過程,注重個體與不同角度、不同環境的相互轉變。族群內部主體將“我者”作為中心,突出與“他者”之間的區別。最后,族群在地方實踐過程中開展自我定位,形成自我認同[4]。
族群認同新的含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自我認同。認同是自我肯定的升華。族群認同與性別認同、階級認同存在顯著區別。族群認同是融于人們對其所處的文化環境中的,與精神、信念有密切關系。從這一角度來看,可以將族群認同看作族群內部的自我認同。同時,族群認同是一種通過追溯起源來升華的自我肯定,所以其在一定意義上是感性的、具有象征意義的、非客觀的。第二,他者認同。族群認同不僅涵蓋了源自族群內部的自我認同,還與“他者”有密切聯系。族群認同是由于所處地理環境不同,在與“他者”溝通接觸的過程中,文化差異會形成文化辨識。因此,族群外部人員對族群認知會產生差異的先寫。基于此,族群認同這一概念不能只是從自我認同的角度來剖析,更要從族群所處的社會環境、政治形態、經濟狀況等入手,或者站在與“他者”溝通互動的層面來剖析。由于在與“他者”溝通互動的過程中,自身所處的位置是可以變化的,所以族群認同能夠隨位置的變動而發生改變。各個族群的民俗文化、傳統習俗、歷史進程各有不同,但受社會組織、生產生活的多方面影響,不同族群間呈現出相互交融的情況,所以在交融過程中要認識到與其他族群的差異性。族群認同不僅體現在自我認同上,而且還體現在他者認同上。
2.3 怎雷村苗族族群認同的具體體現
從相關論述可以看出,族群認同的形成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為自我文化認同,這是基于體質、文化等客觀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在于與其他族群接觸交流的過程中產生的辨識,認識到“我者”與“他者”的差異后,從而形成“他者”對族群的認同。這兩方面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族群認同”。以中國怎雷村苗族為例,怎雷村苗族與怎雷村水族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共生系統。在這樣的共生系統下,他們在生活勞作中有著密切往來,但水族與苗族之間存在和而不同的共存關系。也正是因為和而不同,族群認同在文化傳承當中顯得尤為重要。
族群認同在生活中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民族傳統節日。民族傳統節日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是民族身份的獨特代表。恰恰由于民族節日是民族身份的代表,怎雷村苗族舉辦其特有的鼓藏節就體現了苗族族群內部的自我認同,也展現了怎雷村苗族的民族自信心。在苗族各支系中,關于鼓藏節的由來傳說很多,各不一樣,然而從節日的形式與內容來看,卻擁有相同的主題,即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幸福生活的祝愿。由此可見,怎雷村苗族用民族獨有的節日表明自己的族群身份,建立和聚居主體區的苗族的情感聯系。第二,民族的傳統工藝品。怎雷村水、苗兩族雖居住在一起,但傳統工藝仍保留著各自的文化特色。在怎雷村,還保存著許多傳統的手工藝:水族有馬尾繡,苗族有刺繡、蠟染等。怎雷村的苗族工藝相較于水族而言更多樣、更復雜。例如,怎雷村苗族女性頭上的頭帕尤為特別,配色雅致,工藝精熟,極具苗族特色。蠟染旗幡是人工手作,旗幡象征著家族的興旺與發展,怎雷村苗族的手工藝品保留著原有的苗族特色,怎雷村苗族人民在穿戴這類手工藝品時,表明了自己的族群身份,體現了怎雷村苗族族群的自我認同。第三,傳統的文化習俗。怎雷村苗族文化習俗中有許多活動體現了族群認同,如苗族的斗牛習俗活動。斗牛活動原本是苗族祖先崇拜中最隆重的儀式,怎雷村散雜居苗族舉辦斗牛活動體現怎雷村苗族對自我文化的認同,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現。而水、苗兩族在長期的生活交往中,形成了文化共享的命運共同體。除此之外,苗族在過端節和吃新節時,還會舉辦跳月活動,怎雷村苗族居民在壩子上跳月,而水族居民則在旁邊觀賞。這樣的習俗活動說明怎雷村水族認識到了各自的文化差異,作為觀賞者與其互動,說明了“他者”對怎雷村苗族族群的認同,進而推動了兩族的和諧互動。
3 怎雷村散雜居苗族族群的文化傳承
怎雷村散雜居苗族族群與居住在一起的怎雷村水族構成了一個共生系統,在這樣的環境下,怎雷村苗族和怎雷村水族在怎雷村300余年的同居同生發展歷程中,逐漸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命運共同體。在怎雷村,苗族與水族都能掌握對方的語言,而且兩個民族還能通婚。這些事情說明了水、苗兩族的親密關系。但是,怎雷村苗族作為苗族的支系,卻遠離苗族聚居主體區,缺少和苗族其他支系的交流和聯系。筆者認為,怎雷村散雜居苗族如何傳承發展苗族文化這個問題必須基于族群認同理論來回答,也必須基于族群認同理論來尋找處理手段,主要涉及自我認同和他者認同這兩個概念。
3.1 在族群認同理論中的族群內部自我認同角度
由于怎雷村苗族居住于三都水族自治縣,遠離苗族聚居主體區,成為散雜居少數民族,除了擁有散雜居少數民族的特點外,還缺少和苗族其他支系的聯系。基于以上情況,建立和苗族其他支系的聯系,拓展怎雷村散雜居苗族的社會關系網絡顯得尤為重要。例如,苗族支系合族舉辦苗族文化節,共同舉辦鼓藏節、吃新節,不僅可以凝聚族群內部的向心力,還可以增強怎雷村苗族的自我認同感,改善怎雷村散雜居苗族村民的生活面貌。
3.2 在族群認同理論中的族群間的他者認同角度
怎雷村苗族和水族在怎雷村300余年的同居同生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共生系統,在相同的居住環境、相同的生產生活中可以看到文化相互交融的情況。怎雷村苗族在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的同時,也在多元環境中傳承著本族群文化。基于這種情況,怎雷村苗族要認識到和其他族群的差異性,在和其他民族交融的過程中,要在明確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再吸收先進的寶貴經驗和發展理念。怎雷村散雜居苗族要保持區別于另一個群族的文化特征和族群心理,一同建構族際融合、尊重差異、包容不同文化的美好環境。這個過程既是文化自信的彰顯,更是在發展考驗面前的奮發之舉[5]。
4 結語
中國怎雷村苗族作為脫離苗族聚居主體區的散雜居族群,在文化傳承上應積極把握機遇,迎接挑戰,不只要滿足于接受先輩們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還要緊隨時代主流吸取先進文化,為怎雷村苗族優秀傳統文化注入全新的生機與活力。怎雷村苗族在與其他族群交融的過程中要把握自身,展現怎雷村苗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格,激發怎雷村苗族村民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情感認同。這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就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體現,應通過彰顯文化自信增強傳統文化的傳承效果。
參考文獻:
[1] 徐佳晨.散雜居少數民族族群認同的變遷:以江西撫州金竹畬族鄉為例[D].武漢:中南民族大學,2013.
[2] 荀利波,關云波.散、雜居少數民族概念辨析[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5(1):1-4.
[3] 袁同凱,朱筱煦,孫娟.族群認同、族群認同變遷及族屬標示及認同[J].青海民族研究,2016(3):33-37.
[4] 高峰,劉彥.散雜居民族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再造:合群經驗的視角[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9(4):10-17.
[5] 周小藝,興盛.衰落與重建:黔北仡佬族歷史演變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1.
作者簡介:張晨(1995—),女,湖南祁東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民族民間舞蹈。
彭學艷(1969—),女,貴州貴陽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民間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