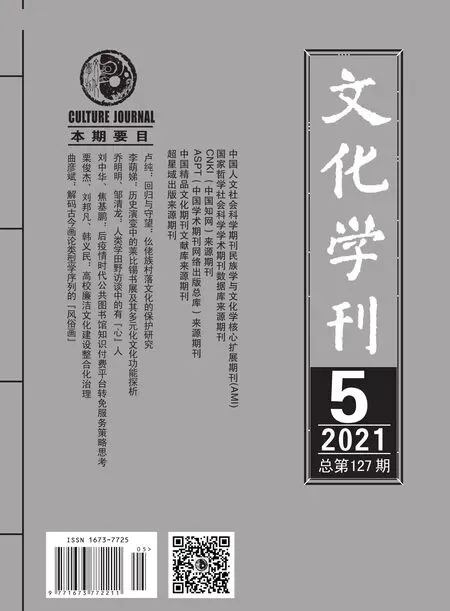論古希臘時期的道德哲學及其歷史局限性
陸書劍
在歷史上,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對道德展開了探索。古希臘時期,研究道德哲學的代表人物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人物都對道德發表了深入見解,并形成自己的道德觀點或體系。通過對他們的道德哲學進行剖析來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對當下的道德建設有所啟示。
一、蘇格拉底的道德哲學
在古希臘的倫理思想發展史中,蘇格拉底首次提出將探索倫理道德作為哲學研究和哲學實踐的目的。他提出了“認識你自己”這一經典命題。關于對人的理解,蘇格拉底與智者學派是完全相反的,蘇格拉底理解的人是理性的人,而智者學派理解的人則是感性的人,這導致蘇格拉底在道德哲學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上與智者學派相左。智者學派的代表人物普羅泰戈拉依據不同的人其感覺存在差異得出結論:道德是相對的,也是具體的,不存在普遍的道德。而蘇格拉底則認為,道德雖然是相對的,但是在這些“相對”的背后存在著一個不變的善,這個善貫穿在具體德行之中。
如何發現這些“相對”背后的一般性的善呢?蘇格拉底認為需要依靠人的智慧來實現。人借助自己的智慧對具體的、個別的美德進行探索,從而發現這些美德背后普遍的善,只有具備這些普遍善的知識,人才能自覺作出合乎道德的行為。這就是蘇格拉底所講的“美德即知識”。“美德即知識”這一命題與智者學派將人的感性欲求作為道德標準是截然對立的,蘇格拉底將人的感性欲求與物質利益排除在自己的道德哲學之外,要求人們多去關注自己的靈魂,而不要去追求名利等身外之物,因為這些東西會損害個人的道德。
在蘇格拉底的認知中,“神的理智包含了真善美,神是人的幸福和善的源泉”[1]68。于是乎,關于修養道德,他認為需要通過人神相通的形式,以神智對人的啟示為準則來修養道德。那么,如何才能獲得神的啟示呢?蘇格拉底認為,人必須拋棄感官認識,完全求援于自我的心靈世界,這是一個與自然及人類社會生活無關的過程。蘇格拉底自稱常常能夠聽到神的聲音,從而獲得了美德的知識。因此,在他那里,道德是一種天賦而無法被教會,只有通過他的所謂辯證的方法,才能將原來存于人心靈之中的知識激發出來,從而使人在道德上得以完善。
二、柏拉圖的道德哲學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杰出的學生,他繼承了蘇格拉底道德哲學的基本原則,并通過智者的感性主義哲學進行駁斥,大大發展了蘇格拉底所開創的理性主義道德哲學。善的本體學說和靈魂不死的學說是柏拉圖道德哲學的理論基礎,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則是其道德哲學努力實現的目標。
柏拉圖是客觀唯心主義者,他反對智者把感覺經驗作為道德價值準則的主張,認為一切具體行為的善的本源是理念世界中的善本體。在柏拉圖看來,善本體是一,而具體行為的善是多,具體行為只有符合善本體這一客觀準則,才能稱其為善。柏拉圖不僅將善本體作為道德的來源,還將其視作萬物的本源,于是乎,在柏拉圖的思想中,真與善在客觀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得以結合,善即是真,真即是善。柏拉圖還提出了四種社會中的主要美德來與善本體相對應,分別是智慧、公正、節制和勇敢。
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是不朽的,靈魂由理智、意志、情欲組成,其中意志就像一匹受過馴養的馬,情欲就像一匹未受訓的劣馬,“而人的理智或理性才是駕馭這兩匹馬并使人生之車奔向至善目標的真正騎手”[2]41。柏拉圖主張靈魂是輪回的,肉體死后靈魂要接受審判,如果合乎道德生活,靈魂就能升到天國,反之靈魂則要墜入地獄。那么,靈魂如何才能合乎道德生活?柏拉圖認為要排除欲望,靈魂只有排除肉體的欲望才能進入一個光明的世界,但是這種境界人只有在肉體消亡以后才能達到。因此,柏拉圖要求人們首先放棄現世的幸福,將希望寄托于來世;其次通過愛情來實現,柏拉圖所指的愛情是一種人神相通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精神狀態。柏拉圖指出從愛個別的美少年開始,逐漸上升直至完全領悟美本體,人一旦進入這樣的精神境界,就可不再留戀世間具體的感官享受,而是沉浸于絕對的美本體之中。
柏拉圖認為道德問題是一個社會制度層面的問題,個人只有在良好的社會制度下才能完善道德。在他看來,良好的社會制度就是社會中的所有人能夠各盡其職的狀態。“智者尚德于智慧,武士尚德于勇敢,平民則尚德于節制。”[2]41只要各階層能夠各安其位,尤其是武士和平民能夠服從統治者,那各個階層的人就具有了美德,整個國家就秩序井然、和諧美好了。但是,正義的國家并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只有當“最高善”的理念在社會占據主導,并且由“哲學王”來統治國家,社會才能成為道德與政治相結合的理想國。
三、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學
亞里士多德被馬克思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雖然他是柏拉圖的學生,但是他能夠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術信仰,對老師的一些思想進行批評,并糾正老師道德哲學中的理想主義偏頗。他在總結古希臘各派道德哲學的基礎上,創立了屬于自己的道德哲學。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功能或人的本性就是心靈遵循理性原理的主動行為”[1]99,因此,人類的德行從本質上講是心靈的德行。關于人的心靈,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心靈由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兩者組成,而理性部分又可分出理智理性和實踐理性兩個子集,其中實踐理性支配著人的道德行為。總體而言,理性部分在人的心靈中占據主導地位,它能夠調節人的欲望,使人作出合乎道德的行為并使人幸福。在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學中,“中道”是其核心原則,即在諸多潛在的價值選項里,人們根據具體的人與事,選擇最合適的行動方案和價值選項以達至“好生活”。“好生活”與“好人”是密切相關的。如何成為“好人”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道德可教,通過制定法律可使人去惡從善,道德教育也可培養人的道德情操。同時,他十分重視實踐在道德中的作用,認為一個人只有不斷進行道德實踐,使自我的道德行為具備恒常性,才是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
“好生活”不但依靠“好人”來實現,同時還依賴于“好城邦”。亞里士多德認為,身處城邦中的人必然要受到城邦的制約,所以好城邦是個人幸福和道德的根本保證。所謂“好城邦”,就是一個公正、友愛且富裕的城邦。關于公正,亞里士多德認為,它是一切德行的總體,公正與否的標準則在于是否守法。在他看來,只有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才能實現公正,道德生活取決于社會政治生活。關于友愛,這個道德規范主要用來調節人際關系。人們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中,依靠友愛可以維護人際關系的和諧與國家的團結。但他所講的友愛的出發點是自愛而不是為他人,與他人的交往只是為了完善自己的德性。關于富裕,就是說國家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這樣才能為人們遵守道德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
四、古希臘時期道德哲學的歷史局限性
(一)道德哲學陷入唯心史觀哲學的泥潭
古希臘時期的道德哲學采取唯心主義歷史觀來探究道德,忽視了社會存在對于道德這一社會意識的決定性作用。而將道德看成是神的旨意,呼吁人們尋求來世的幸福,抑或是將道德視作獨立于經驗之外的純粹意志。這些道德思想脫離了社會歷史發展的現狀,尤其是否定了道德的社會物質根源,使得道德帶有抽象性和形而上學性,成為一種超越于人和歷史的神秘存在。靠這些抽象的唯心的道德概念去呼喚人性、改良人性,只能使得人們“在幻想、觀念、教條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鎖下日漸萎靡消沉”[3]。
(二)道德哲學服務于統治階級
古希臘時期的道德哲學總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之上來闡述觀點,所產生的道德哲學只代表在社會上占據極少數的舊式貴族的利益而非廣大人民的利益。但這些思想在傳播的過程中,又總是披著超越階級的虛偽面紗,宣稱自己具有普適性,以此來教化民眾安于現狀,服從統治階級的統治。對于廣大普通人民而言,這些思想的積極意義是十分有限的,更多是起到麻痹人的精神,削弱人的反抗意志及粉飾階級矛盾的作用。這些理論顯然不能成為全民共同遵守的價值準則。
(三)道德哲學停留在認識領域
古希臘時期的道德哲學往往只停留在對道德生活的認識方面,而未能將理論的維度拓展至道德生活的改造方面。這些“道德學說脫離現實社會中人們的道德實踐活動,通過空洞的道德說教構造所謂的價值體系,或者進行純理論的道德研究”[4],缺乏一種現實的理論張力。其造成的結果就是現實的苦難被置于一邊,人與現實被迫進行所謂的和解,而實際上卻被禁錮在幻想的和諧之中。這些僅僅停留在認識領域的理論不能成為廣大人民認識和改造自我與社會的思想武器。
五、結語
通過剖析古希臘道德哲學的歷史局限性,我們從中得到的啟示是:其一,當下的道德建設要與現實社會情況相匹配。道德歸根結底是一種社會意識,由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因此,我們的道德建設必然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立足于社會的主要矛盾,才能構建出符合當下人民思想水平的道德體系。其二,當下的道德建設要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道德只有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才能得到真正的擁護,這就需要我們深入廣大群眾中,切實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以道德建設來促進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的提升。其三,當下的道德建設要提升實踐性。道德是以實踐的精神來把握現實的,這要求我們的道德建設要直面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從道德的角度作出符合時代和人民需要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