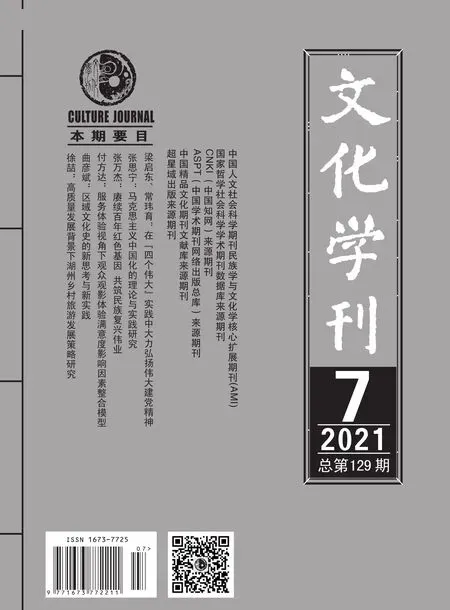論人性與自由的關系
——基于哲學史的思考
黃新佼
哲學的終極奧義是探尋世界的本質,在這一探尋過程中,作為尋找主體的人,首先要清晰地認識自我。在漫長的哲學發展史中,哲學家們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更新,且趨向一致,由此對人的本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而自由是與作為主體的人息息相關的一部分,在人的本性與追求自由之間,哲學是否存在某種特殊的作用與意義?是否可以將自由和本性這二者相等同?基于哲學發展史,本文將從其產生及發展過程來進行思考和探尋。
一、對人性的探究
希臘哲學早期建構世界的方式是神話故事,用古希臘神話解釋自然界和社會中發生的一切現象。公元前6世紀,第一批哲學家開始探尋更為真實的世界,將目光從神話轉向了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不過早期哲學家更多的是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進行思考,如世界的由來、構成等,從自然的角度入手,忽略了人自身。
到了智者學派時期,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人。古希臘哲學家探討人事問題時關于人事相關內容的爭論產生了“自然說”與“約定說”的兩個觀點,首次提到了人的本性。“自然說”中的自然特指人的本性。“自然說”認為應該按照自己的本性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應該受到外在法律和習俗的約束[1]。這里的人的本性即人性,“自然說”中用“自然”一詞來形容它,但是并未對這一詞做出更多的說明。按照“自然”來理解,這里的本性應該是指人與生俱來的一種純自然的動物性的欲望、渴求,人想要如何生活,就可按照自己的這種本性去追求。這種本性是自由的,不應受外在約束。這一時期對人性的看法是一種原始的、本能的、動物性的特性,也可以算是人原初的狀態。剛出生的嬰兒所具有的就是這種純自然的動物性的渴求。在這里借用“自然狀態”這一稱謂,但是這一“自然狀態”并非是霍布斯原意上所說的那種人人享有同等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出于自己趨利避害的本性而互相殺戮。這里的“自然狀態”更多的是想強調一種自然性、原始性和動物性,有的只是單純的原始的欲望。
柏拉圖在《普羅泰戈拉篇》里說,據說神在造出各種生物之后,又分配他們適合其本性的生存手段,唯獨人沒有得到護身的工具。人類從普羅米修斯那里得到火之后,分散居住,無法抵抗兇猛的野獸,人類之間也相互為敵。為避免人類滅絕,宙斯派赫爾墨斯把尊敬和正義帶到人間,建立政治和社會秩序,他要求把這些德性分給每一個人[2]。柏拉圖的論述本意是想通過人性來說明國家是如何組成的,通過他的論述可知,他認為尊敬與正義是人性的重要內容,且尊敬與正義是神所賦予的,這時柏拉圖的人性已經脫離了自然狀態,不再是純自然的動物性,多了道德與政治的內容,有了社會性。這樣的人性是倫理人性、政治人性。
亞里士多德在表述關于善和幸福的內容時,認為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它出自人的自然稟賦和本性,人獨特的自然能力是理性,即人性中含有理性的成分,理性指導人分辨是非善惡并趨善避惡。在這里,他所表達的是一種利他主義的道德準則,德性被分為自然德性和嚴格意義上的德性。自然意義上的德性是一種潛在的傾向,未必能夠實現。在人的本性中含有對幸福的向往,而這種理性并非是動物直覺,與柏拉圖一樣,是一種社會倫理取向,都是倫理上的人性。
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發現人的價值包括尊嚴、才能和自由,人文主義者關注抽象的人性價值,包含尊嚴、才能和自由,當轉向社會政治中看人時能看到人的政治本性。馬基雅維利認為人性惡,他說,“關于人類一般的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3]。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也都認為人的本性已經全然敗壞。“我們的本性不但缺乏一切的善,而且罪惡眾多,滋生不息……”
到了康德那里,他認為人性與道德密不可分。道德是人性的基礎,人性服從于道德[4]。康德把人分為感性的人和理性的人。感性的人就是像動物一樣追求感性肉體官能,理性的人高于動物,具有理性能力。這樣來理解,人性就有了更細化的分層,可以稱為自然人性與道德人性。在這一過程中,理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因為理性的存在,給了人向善去惡的可能性。
歷史上對人性的認識發展,經歷了從無知到知,從簡單認知到復雜認知的過程。這里說人性的發展,實際上是想從本體論角度來看人性,而非道德倫理的角度。因此,從本體論意義上來看,人性本應該是最初純自然的一種狀態,是一種純動物性的渴求,可以稱這種人性為人的自然狀態。這種自然狀態不能簡單地用善性或惡性來概括,它既有向善的可能也有作惡的可能。但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本體論意義上的人性逐漸被忽視,人們更多地關注人的政治性、倫理性。人們理所應當地從道德倫理人性層面出發考量人的一切活動,卻忽視了人的一切行為一定都是從本原的人性出發,就算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人,在行為時多了別的考量,這樣的考量也一定與自己的本性有關,然后又受外界影響,在人性的基礎上多了社會因素。
二、自由的萌芽
自由一直是哲學、倫理學中重要的命題,人似乎是與生俱來地對自由充滿了向往。而自由究竟是何時被人所認知的,什么樣的狀態才是自由的狀態,從哲學史中可見微知著。
晚期希臘哲學的斯多亞學派,雖然并未直接表明自由是什么,但談到了自由選擇。人可以自由自主地選擇對表象的態度。斯多亞學派用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人選擇表象的自由:
不要被表象弄得急不可耐,對自己說,“表象啊,等一會兒,讓我看一看你是誰,要干什么,讓我考驗你一下”。不要讓表象牽著你走,不要把你要做的事想得栩栩如生,否則你就會受到它任意支配。要用另外一個美麗高尚的表象與之相抗衡,把這個卑鄙的表象排除[5]。
斯多亞學派的這個例子所表達的選擇表象的自由,著重強調不被外界所左右的選擇就是自由的選擇。這個外界的范圍很廣,可以理解為,只要是經由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表象都是不自由的,由此人極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真正自由的選擇非常稀少且珍貴。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發現,對于人來說,最高的價值是自由,這個自由是指選擇和造就人自己地位的力量,自由是神賦予人的禮物。皮科借上帝之口曾表示過,上帝造人時人沒有任何的規定性,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做出任何自由的抉擇。人文主義者將人視為宇宙的中心,可以凝視世間萬物。人在這樣自由的境地中,可以將自己塑造成任意的形式。人文主義時期的這種自由著重強調人在世間獨一無二的地位,正是由于這種地位,所以人是自由的。
斯賓諾莎認為,自由是人自覺順應自然,當人不自覺被自然必然性所驅使時,他是被迫的,奴役與自由是相對的。這里的自然必然性不僅指外在的自然界的規則,更重要的指人的內在自然本性,在這種自然本性中會有自發產生的自然情感,如果人能對這些情感和欲望產生的外在原因及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有正確的認識,那么人就是自由的,即自由就是能夠認識、克制和管轄從人的本性中產生的各種自然情感。
盧梭在其政治學說中論述了何為自由,人生而自由,即人在自然狀態時是原初的自由狀態。當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過渡,人逐漸喪失自由,自由是一種原初的狀態,但是這種自由狀態是不持續的。盧梭的自然狀態指沒有人際交往、語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類最初的狀態,當人逐漸進入社會狀態時,自由就已經開始逐漸喪失。
洛克在談論到自由時,認為人有自然自由。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間任何上級權力的約束,不處在任何人的意志或立法權之下,只以自然法為準繩。洛克的自然自由是與處于社會中的人的自由相對應的。處于社會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經人們同意在國家內所建立的立法權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權的支配;除了立法機關根據對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意志的管轄或任何法律的約束。這里的社會自由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不是無限的,是在法律的范圍內的自由。
三、人性與自由
在人的本性之中,與生俱來地包含著對自由的向往,通過對哲學史的梳理不難發現,人性的具體內涵盡管是在不斷變化的,但是這一過程無論如何變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自由這一因素,自由與人性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特殊的聯系,是以下思考的重點。
(一)人的本性即自由的狀態
古希臘時期所探討的人的本性,即一種純自然的狀態,這種純自然的狀態沒有任何指向,不具任何道德性,就是事物最初產生的一種自然形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之下的人是自由的,不受外在社會世俗的約束。這里所謂人性的自然狀態恰好與盧梭所指向的自由的自然狀態和洛克的自然自由相契合。沒有外在的社會世俗對人的本性的影響,也就沒有對自由的奴役,因此可以說,在這樣的階段,人的本性即自由,人生而自由。這樣的狀態是一種原始的狀態,也是一種最佳的狀態。但我們只能認識,卻無法恢復。人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為自己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無法卸載的枷鎖,使人類社會成為社會應有的樣子。
(二)自由的喪失與人性的泯滅
當人從自然狀態走向社會狀態,隨著倫理哲學的發展,自由在不斷地被限制,人性也在不斷泯滅。這里的人性就是本體論上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就是不具理性因素的,沒有限制和約束的狀態。隨著人越來越多地受到外在表象的左右,人性越來越多地受到外在表象的覆蓋,于是自由狀態不復存在。人性還是人性卻也不再是人性,人性成為道德的附庸。人純自然的本性被倫理學家和政治學家賦予了善、惡等道德意味,所以這時的人性已不再是原初本體論意義上的人性。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探尋如何達到平等的路徑時,其中之一是回到自然狀態。回到自然狀態,不僅可以達到平等,也可以恢復人的本性與自由,但隨著當前社會的發展,這樣的路徑無法實現。其中之二,即用社會契約來保障社會平等,這樣能建立一個保障人們自由和平等的國家政權,但這恰恰是使人喪失自由和人性的一種方式,通過社會契約將人從自然狀態全權脫離出來,受社會的左右和約束,交出人的本性與自由,組成了國家和社會。一切都是被決定的,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是政治動物或稱社會動物,恰是泯滅了人性,再無自由可言。
(三)自由與倫理人性并存
在康德道德哲學語境中,自由即自律,是一種理性。人在社會生活中,能認識外在各種事物,了解其產生和發展。人能夠自覺主動地適應各種外在事物,自覺行善。人的本性中同時就含有善和惡的因素。當含有的善的因素處于領先地位時,自由和人性相契合,在善性的指導下,人自覺主動地行善,這時可以稱之為自由的人。當惡的因素處于領先地位時,自由的人是理性的,可以糾正惡行,向善靠攏。
但是從實際層面來看,人并不是一直自由,即人并非可以一直自律。不論是善還是惡,生活中我們都有失去理智、打破自律的時刻。這樣的時刻,不管是善還是惡都將倒向惡或更惡。同時這樣一種并存的狀態,是建立在對自然人性的泯滅基礎之上的。打破自然狀態,建立社會狀態之下的人性,依賴于道德哲學將自由和人性并存。
四、道德對人性與自由的重要影響
人性與道德的關系是復雜的,現在我們探討人性時,常將人性分為善、惡等其他不同的類型。然而人性是先于道德的,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所認為的應然的人性和實然的人性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此看來,人們常常說人性的善與惡等其他類型的劃分,顯然是一種應然的狀態。而實際上,人性本無道德劃分,只是一種純動物性欲望。在這種欲望下所導致的各種利益沖突之中,產生了道德規范,借以約束彼此來維護自身的利益,這時才賦予了人性善和惡的區別。所以可以說道德是從為人性服務出發,最終又復歸人性。
自由與道德的關系在不同哲學體系中有不同的類型。在中國古代社會,主要表現為自由受制于道德。中國古代儒家思想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復禮”,等等。諸如此類的種種道德規范是在社會習俗中漸漸形成的,并非在人的自由意志中形成。人的本性中本沒有這些克制與倫理,所以歸根結底,自由受制于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學中,自由和道德是辯證統一的,其中康德關于自由與道德的思想尤為典型。在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將道德法則視為自由的法則,他提出“自由誠然是道德法則的存在理由,道德法則卻是自由的認識理由”。前一個自由是一種他所認為的消極的自由,指不受干涉;而后一個指自律,是一種積極的自由。康德還有一句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前一個就是康德所指的消極的自由,后一個就是一種高級的自律。在這個過程中,自由和道德是辯證統一的。道德賦予了人性和自由不同的等級,道德使人性與自由更加規范化和社會化,但同時,就是因為道德的產生,將人性本自由的狀態打破,人性與自由分裂開來,成為人性和理性。
不論人的本意如何,都是產生于自然,由他的自然本性所決定,這種自然本性即人性。當人在自然狀態自主自覺地活動和選擇時,人就是自由的。當人已經無意識地被外在事物所驅使時,自由就不復存在。而倫理哲學意義上的自由和人性的約束和限制更多。因而,當人進入社會時,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再自由地行動了。正如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