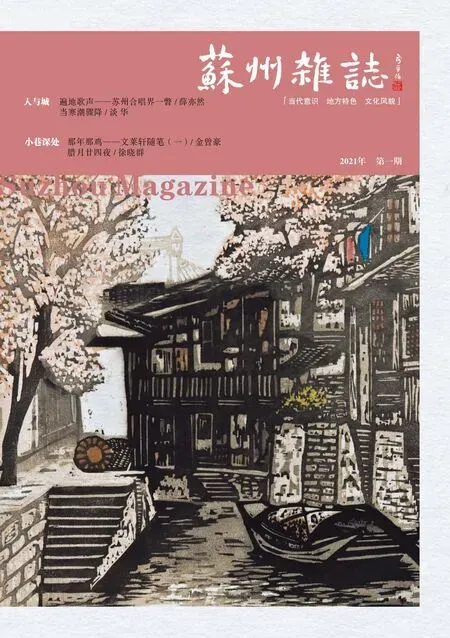吳國的寶劍傳說
林屋
蘇州虎丘山有著一個美麗動人的傳說。據(jù)東漢《越絕書》和唐代《吳地記》等書記載,吳王闔閭?cè)ナ篮笙略嵩陂嬮T外虎丘,闔閭的銅槨內(nèi)外三層,水銀池深六尺,池中漂浮著玉鳧。陪葬的有三千把扁諸劍,分別藏在三千口方井中,此外還有時耗、魚腸兩把名劍陪葬。這個墓穴征用了成千上萬民夫建造,建成后三天,金屬精氣化成一頭白虎駐扎在墓上,所以被稱為虎丘。后來秦始皇在這里尋劍無所獲,就將這里陷為一座水池,所以被稱為劍池。
虎丘劍池下面到底有沒有吳王闔閭墓和陪葬的寶劍?從古文獻來看,越王勾踐、秦始皇、吳王孫權(quán)先后在此發(fā)掘過,卻無一例外都是一無所獲。而今天考古不提倡主動發(fā)掘,所以是否真實存在仍然是個謎。
不過,這些傳說足以引發(fā)文人墨客的無限遐思。
當(dāng)然,傳說也不是無中生有,春秋晚期的吳國和近鄰越國,確實擁有獨樹一幟的劍文化。《周禮·考工記》說“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戰(zhàn)國策·趙策三》說“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莊子·刻意》說“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干就是邗(今江蘇揚州),吳王夫差曾在邗地筑城,所以文獻有時也以“干”代指吳。
除了虎丘劍池外,吳國還擁有不少關(guān)于寶劍的歷史傳說。
《新序》記錄了季札掛劍的一段佳話。季札是吳王壽夢的幼子,吳王闔閭的叔父。公元前544年,季札奉命出使北方諸侯。在經(jīng)過徐國(今安徽泗縣、江蘇泗洪一帶)時,徐國國君見到季札的佩劍,流露出艷羨的神情。等季札周游列國返回徐國時,國君卻已經(jīng)去世了。季札要將劍送給嗣君,隨從阻止說這不是國家饋贈之物。季札說,自己當(dāng)時內(nèi)心已經(jīng)許愿,要在回國后把寶劍贈給他;如果因為去世了就不送,那不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嗎?嗣君也認為自己沒有先君遺命不肯接受。于是季札將佩劍解下掛在徐君墓前的樹上。徐國人為稱頌季札高潔的誠信品質(zhì),作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左傳》中魚腸劍的傳說也是膾炙人口。公元前515年,當(dāng)時還是公子光的吳王闔閭為了篡位,趁著吳王僚的弟弟掩余、燭庸在潛之戰(zhàn)被楚軍圍困,叔父季札出使北方,宴請王僚來府上宴飲,派伍子胥推薦的死士鱄設(shè)諸趁機刺殺王僚。吳王僚也不笨,披堅執(zhí)銳的親兵從道路兩旁一直護衛(wèi)到坐席兩旁,上菜的人在門口要換衣服,在劍士的控制下,用膝蓋跪著前行,遞給上菜的人。公子光假裝有病躲入地下室,而鱄設(shè)諸則把劍藏在魚腹中,進入后趁機拔劍擊殺王僚。公子光趁機帶著埋伏的甲士殺出,雖然鱄設(shè)諸也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這場政變最終還是成功了。在后世的文獻中,“鱄設(shè)諸”也被稱“專諸”。
專諸刺僚這把劍,《越絕書》稱呼它為魚腸劍,就是葬于虎丘劍池的其中一把。據(jù)說,魚腸劍是越國劍師歐冶子所鑄寶劍之一,吳王闔閭得到了他所鑄的魚腸、勝邪、湛盧三劍。其中湛盧也頗為傳奇。據(jù)說在闔閭?cè)ナ篮螅驗榉虿钜匀搜吃幔勘R作為陪葬品自己消失了,先是到了秦國,最后又為楚王所得。勝邪劍的下落沒有交代,或許與葬于虎丘劍池的時耗劍是同劍異名。
吳國也有兩位傳奇的鑄劍師:干將、莫邪夫婦,據(jù)說干將是歐冶子的師兄弟,被吳王闔閭派往離都城二里的千里廬虛鑄劍,以三百童男童女相助。據(jù)《吳越春秋》,干將鑄劍怎么也鑄不好,不禁感慨道,當(dāng)年師父師娘以身投爐,才煉就絕世好劍啊!妻子莫邪聽到此話后,剪下頭發(fā)和指甲將其投于劍爐,這樣才完成一對絕世名劍。《吳地記》認為莫邪投入的是軀體,但在古代巫術(shù)觀念中,頭發(fā)和指甲都是人體的一部分,其實也相當(dāng)于代替人體了。劍以人名,雄劍叫干將,雌劍叫莫邪。干將將雌劍獻給吳王,吳王又送給魯國大夫季孫意如。但季孫意如發(fā)現(xiàn)劍上有個米粒大的小口,于是斷定吳國霸業(yè)不會長久,沒有接受這把劍。

虎丘劍池
這個故事到后代有多次變形,魯迅先生在《鑄劍》中也講述過,大致是按照《搜神記》的故事陳述的。在這個故事里,干將夫婦是為楚王鑄劍,但只獻雌劍而藏下雄劍。楚王發(fā)覺后殺死干將,干將的遺腹子赤比長大后,找到父親藏下的雄劍。之后在一名神秘刺客的幫助下,刺客將赤比自殺后的頭顱獻給楚王,并在油鍋邊趁機斬下楚王頭顱,最后神秘刺客也斬斷自己頭顱而死。而根據(jù)另外一些記載,赤比所殺的是晉君,又有說是魏王;還有說殺干將的是吳王,還有說干將做過韓王劍師;甚至還有說,楚王夫人抱著鐵柱有感生下一塊鐵,楚王找到莫邪鑄劍,莫邪同樣私藏雄劍被殺,后來赤比為父報仇,那么莫邪竟是男性。
以上記錄可能都只偏向民間傳說。干將、莫邪可能未必是真實存在的人物。戰(zhàn)國時期“莫邪”(或作莫耶、鏌釾等)一詞常見,都用于良劍的稱呼。清人王念孫在《廣雅疏證·釋器》中認為,干將、莫邪都是形容鋒刃的連綿詞,并非人名,從《吳越春秋》開始才將干將列為吳人,莫邪為干將之妻。筆者認為,“干將”也可能也有“干地劍將(匠)”的意思,即吳國劍師的通稱;類似的是“歐冶子”大概是“歐(謳)地冶師”的意思,謳為越地,“歐冶子”即越國劍師的通稱。雖然傳奇色彩較為濃厚,但也能反映吳國寶劍的精良與馳名。今天蘇州城區(qū)有縱橫交錯的干將路與莫邪路,相門也為匠門(干將門)之讀音訛變。
考古發(fā)現(xiàn)也有不少吳國王族用劍,其中諸樊、余祭、余眜、闔閭、夫差與季札之子所鑄之劍都有發(fā)現(xiàn),其中有些題銘讀來還頗為有趣。
1959年12月,安徽淮南趙家孤堆出土了一把“吳太子諸樊劍”,提到諸樊當(dāng)太子時就手持這把劍作為軍隊前鋒,多有斬獲,無人能敵;他當(dāng)時駐扎于江北,已有北上、南下、西征的雄心壯志(“在行之先,云用云獲,莫敢御余。余處江之陽,至于南北西行”)。2009年,浙江杭州市郊南湖出土了一把“吳王余祭劍”,提到吳王余祭認為不需要告訴大家自己有勇略,而只需要等到大家自己來了解(“有勇無勇,不可告人,人其知之”)。
最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底蘇州博物館征集到的一把“吳王余眜劍”,這把劍有銘文七十五字,是目前所見先秦劍類兵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提到在余祭時代余眜就受命攻打楚國麻地,所獲甚多,后來在御楚之戰(zhàn)中打敗楚國,楚軍潰逃,王師趁勢反攻楚國;后來又在御越之戰(zhàn)中擋住越軍進攻,使得吳國沒有受損。之前在1997年,浙江紹興魯迅路也出土了一把“吳王余眜劍”,其中提到余末(即余眜)即位后攻打過楚國巢地,后來在楚伐徐之戰(zhàn)中支援徐國,大敗楚軍并俘獲七位楚國封君。這兩件兵器可以聯(lián)系起來讀,并作為春秋軍事史料的補充。
吳王闔閭(光)、夫差父子劍則是出土最多的。吳王光劍有“以擋勇人”“以戰(zhàn)越人”“克挦多功”等字眼,均與夸耀自己戰(zhàn)功有關(guān)。北京私人收藏一把“吳王夫差劍”其中提到“霸服晉邦”,則可能與公元前482年的黃池會盟上的吳晉爭霸有關(guān)。
蘇州是一個充滿矛盾感的城市。大多數(shù)人對她的第一印象是溫山軟水,風(fēng)光旖旎,但翻閱兩千年前的典籍,我們?nèi)匀豢梢愿惺艿剑窦s之下不失英氣,溫柔之下不失陽剛的個性。兩千五百多年歷史的蘇州,劍膽與琴心并存,秀麗與剛健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