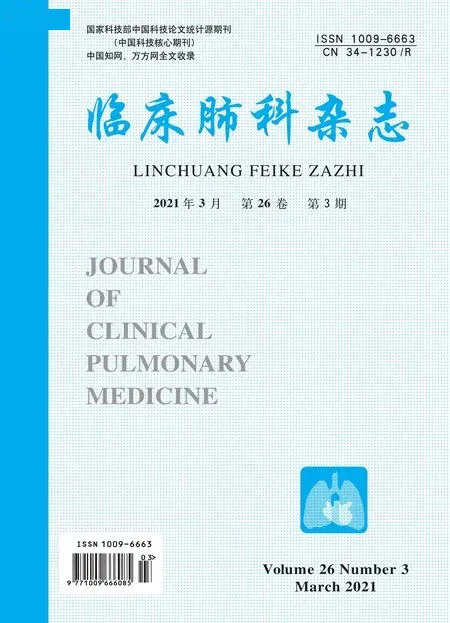缺氧誘導因子-1α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與非小細胞肺癌中臨床病理特征和預后關系的研究
路璐 潘峰 趙成 孫志鋼 張楠
目前,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圍內居于首位,也是腫瘤相關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非小細胞肺癌(NSCLC)約占所有肺癌的80%以上[1]。由于當前腫瘤TNM分期系統[2]缺乏足夠的預測價值,我們可以結合一些生物標志物來預測患者的生存率。缺氧誘導因子-1α (HIF-1α)是HIF-1基因家族的成員之一,在缺氧條件下高表達,在常氧條件下降解[3]。HIF-1α可直接調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4]和一氧化氮合酶(NOS)[5]等基因。VEGF在血管生成中發揮核心作用,促進內皮細胞增殖、遷移和侵襲,且在不同腫瘤中都有過表達[6],并可以靶向識別腫瘤細胞并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7-8]。本研究旨在探討HIF-1α和VEGF的表達與NSCLC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的關系,并進一步驗證二者表達調控的上下游關系。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在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中心醫院胸肺外科進行肺癌切除手術的79例患者。納入標準為:1)接受根治性手術并經病理證實為鱗癌或腺癌;2)診斷為I-IIIa期非小細胞肺癌;3)無明顯手術禁忌癥。大細胞癌和腺鱗癌因樣本太少被排除在外。表1顯示了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本研究由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中心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二、免疫組織化學法
所有非小細胞肺癌標本均取自79例患者,以鄰近非腫瘤肺組織作為對照組織。組織標本固定在10%中性福爾馬林緩沖液中做常規處理。將石蠟包埋組織標本切成4 μm厚的切片,用鏈霉親和素-過氧化物酶(SP)法[9]檢測組織標本中HIF-1α和VEGF的表達。簡言之,標本切片與兔抗人HIF-1α單克隆抗體(濃度1 ∶100,購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抗體編號:PB0245)或兔抗人VEGF單克隆抗體(濃度1 ∶100,購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抗體編號:BA0407)在4°C培養過夜,根據廠家說明用山羊抗兔IgG抗體(濃度1 ∶100,購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抗體編號:BA1003)制備二抗。用半定量免疫反應評分系統(IRS)測量HIF-1α和VEGF的表達水平[9-10]。將標本分為陰性表達(IRS0~2)和陽性表達(IRS3~6)。
三、細胞培養
人非小細胞肺癌細胞系A549和H1299從美國組織培養物保藏中心(ATCC)和中科院上海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獲得。細胞在含10%胎牛血清的DMEM培養基中,置于37℃,5% CO2培養箱中培養。在細胞融合至約80%時,除去培養液,PBS液漂洗3次。細胞分為3組,1組細胞加入含500 μmol/L CoCl2的DMEM 2 mL,2組加入含500 μmol/LCoCl2和200 μg/mL HIF-1α抑制劑LW6(美國Millipore公司)的DMEM混合液2 mL,3組加入含500 μmol/L CoCl2和200 μg/mL抗VEGF藥物貝伐單抗(Avastin)(購自美國Roche公司)的DMEM混合液2 mL,均置于37℃,5% CO2培養箱中培養24 h。
四、Western blotting
將細胞置于冰上,加RIPA裂解液(加蛋白酶抑制劑)裂解提取蛋白,BCA法測定濃度,95℃加熱5 min。垂直電泳槽內每孔內加入約20 μL蛋白,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分離蛋白樣品,轉膜至PVDF膜,5%脫脂奶粉封閉1 h,一抗4℃孵育過夜,TBST洗3次,每次10 min,二抗室溫孵育1 h,洗膜后加ECL顯影,Image J軟件掃描灰度值,GAPDH為內參對照。
五、統計分析
使用SPSS 13.0分析所有統計數據。計數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HIF-1α和VEGF表達的相關性采用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采用Kaplan-Meier繪制生存曲線。采用對數秩檢驗比較存活率,Cox多因素回歸分析判定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被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HIF-1α和VEGF的免疫組化表達情況及二者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HIF-1α陽性表達主要位于胞漿和胞核中(圖1)。HIF-1α陽性表達率為65.8%(52/79)。表1顯示,HIF-1α的表達與腫瘤分化程度(高41.7%vs中64.0%vs低88.2%;P<0.05)、病理淋巴結(pN(-)46.4%vspN(+) 74.5%;P<0.05)和pTNM分期(pI 47.4%vspII 62.8%vspIIIa 94.1%;P<0.05)顯著相關。
VEGF陽性表達主要位于胞漿中(圖2)。VEGF陽性表達率為64.6% (51/79)。表1顯示VEGF表達與pT (T135.7%vsT269.1%vsT3 80.0%;P<0.05)、病理淋巴結(pN(-)42.9%vspN(+)76.5%;P<0.01)和pTNM分期(pI 36.8%vspII 67.4%vspIIIa 88.2%;P<0.05)顯著相關。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顯示HIF-1α表達與VEGF表達呈正相關(P<0.01)。49.4% (39/79)的病例呈HIF-1α和VEGF雙陽性表達。且與pT (T121.4%vsT250.9%vsT380.0%;P<0.05)、病理淋巴結(pN(-)17.9%vspN(+)66.7%;P<0.01)和pTNM分期(pI 15.8%vspII 48.8%vspIIIa 88.2%;P<0.01)顯著相關(表1)。
二、影響5年生存率的因素分析
本組79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為40.5%。應用對數秩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顯示,分化程度(P<0.05)、pN(P<0.01)、pTNM分期(P<0.01)、HIF-1α表達(P<0.01)、VEGF表達(P<0.01)以及HIF-1α和VEGF雙重表達(P<0.01)與5年生存率顯著相關(圖3,表2)。COX多因素回歸分析顯示,分化程度、pN以及HIF-1α和VEGF雙重表達是影響5年生存率的獨立因素(表3)。

表1 HIF-1α和VEGF表達與非小細胞肺癌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圖1 肺癌組織切片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顯示缺氧誘導因子-1α(原始放大倍數×400)

表2 影響非小細胞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的單因素分析
三、LW6和Avastin對HIF-1α和VEGF表達的影響
在非小細胞肺癌細胞系A549和H1299中,用氯化鈷(CoCl2)處理細胞,誘導化學缺氧環境(1組),用HIF-1α抑制劑LW6同時處理細胞(2組),用VEGF抑制劑Avastin 同時處理細胞(3組),可以看到:CoCl2誘導化學缺氧誘導HIF-1α的表達,而LW6處理(2組)可以顯著抑制HIF-1α的表達 (P<0.01),同時VEGF的表達與1組相比也顯著下降。但Avastin 處理組(3組)與1組(缺氧組)相比無顯著性差異(P>0.05),表明LW6作為HIF-1α抑制劑,除了可以抑制HIF-1α的表達,也能抑制VEGF的表達。而Avastin作為VEGF的抑制劑,也下調VEGF的蛋白水平,但對HIF-1α的表達也沒有明顯的影響(圖4)。

表3 非小細胞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的Cox回歸多因素分析

圖2 肺癌組織切片免疫組化染色顯示VEGF(原始放大倍數×400)

圖3 A:Kaplan-Meier分析術后總生存率;B:根據分化程度用 Kaplan-Meier分析術后患者的總生存率;C:根據pN(-) 和 pN(+)用 Kaplan-Meier分析術后患者的總生存率;D:根據TNM分期用 Kaplan-Meier分析術后患者的總生存率;E:根據HIF-1α表達用 Kaplan-Meier分析術后患者的總生存率;F:根據VEGF表達用 Kaplan-Meier分析術后患者的總生存率;G:根據HIF-1α和VEGF雙重表達用 Kaplan-Meier分析術后患者的總生存率

圖4 Western blot檢測顯示HIF-1α和VEGF的表達
討 論
自1999年發現了HIF-1α在腫瘤組織中高表達后[11],越來越多的研究報道了HIF-1α的表達與腫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和預后的關系。免疫組織化學對HIF-1α表達的評估在多種類型的癌癥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12-13]。在以前的研究中,免疫組織化學顯示,40%到80%的癌癥患者的細胞核和細胞質中都有HIF-1α蛋白的表達[14]。然而,不同的研究表明,不同臨床特征的肺癌組織中HIF-1α的表達趨勢不同。肺癌患者HIF-1α的表達和預后存有爭議[15]。Yang[16]等人通過meta分析總結了17項試驗,發現肺癌患者HIF-1α的高表達與腫瘤分期、淋巴結轉移、組織學、分化和低生存率有關。在目前的研究中,65.8%的非小細胞肺癌組織HIF-1α表達與腫瘤分化程度(高41.7% vs中64.0% vs低88.2%;P<0.05)、病理淋巴結(pN(-)46.4%vspN(+)74.5%;P<0.05)和pTNM分期(pI 47.4%vspII 62.8%vspIIIa 94.1%;P<0.05)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為40.5%,HIF-1α陽性表達組的5年生存率明顯低于HIF-1α陰性表達組(P<0.01)。我們的研究結果符合先前提出的結論,表明HIF-1α在非小細胞肺癌中起著重要的臨床病理作用。
研究表明,HIF-1α可以調控至少60個下游靶基因,包括VEGF[17]。作為最有效的血管生成因子之一,VEGF可介導內皮細胞增殖,增強血管通透性[18]。許多研究報道VEGF在非小細胞肺癌中高表達,這已成為肺癌治療的重要靶點[6,19]。本研究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觀察了VEGF在非小細胞肺癌組織中的表達,結果顯示64.6%的非小細胞肺癌組織中有VEGF的表達。VEGF在腫瘤組織中的表達與pT (T135.7%vsT269.1%vsT380.0%;P<0.05)、病理淋巴結(pN(-)42.9%vspN(+)76.5%;P<0.01)和pTNM分期(pI 36.8%vspII 67.4%vspIIIa 88.2%;P<0.05)顯著相關。VEGF陽性表達組的5年生存率明顯低于VEGF陰性表達組(P<0.01)。我們的結果表明VEGF的表達促進了非小細胞肺癌的侵襲和轉移。
以往的報道大多是單獨研究HIF-1α或VEGF的表達,很少將它們結合起來研究[20-21]。Karetsi[22]等人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55例肺癌組織中HIF-1α和VEGF的表達。他們發現僅在肺腺癌中,T分期與HIF-1α和VEGF的表達呈顯著正相關。并且HIF-1α和VEGF的表達與總生存期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有研究發現,VEGFR2是VEGF的特異性受體,兩者結合后通過一系列生物調控誘發血管內皮細胞增值,促進腫瘤血管生長。在腫瘤血管生成過程中,HIF-α/VEGF/VEGFR2通路在腫瘤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23]。如上所述,VEGF是HIF-α的靶基因,上調HIF-α的表達可促進腫瘤新生血管的增殖。在本研究中,癌組織中HIF-1α的表達與VEGF的表達呈正相關(P<0.01)。49.4%的病例HIF-1α和VEGF呈雙陽性表達,與pT、病理淋巴結和pTNM分期顯著相關。瘤體較大組的HIF-1α和VEGF雙陽性表達明顯高于瘤體較小組(T121.4%vsT250.9%vsT380.0%;P<0.05)。有淋巴結轉移組(66.7%)的HIF-1α和VEGF雙陽性表達明顯高于無淋巴結轉移組(17.9%;P<0.01)。另外,局部晚期組的HIF-1α和VEGF雙陽性表達明顯高于早期組(pI 15.8%vspII 48.8%vspIIIa 88.2%;P<0.01)。在對數秩檢驗的單因素分析顯示,HIF-1α和VEGF雙陽性表達組的5年生存率顯著低于陰性表達組(P<0.01)。為排除混合因素對統計分析的影響,采用多因素分析確定預后因素,結果顯示分化程度、pN以及HIF-1α和VEGF雙重表達是影響5年生存率的獨立因素,是預后不良的相關獨立因素。我們的數據表明,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HIF-1α和VEGF的雙陽性表達與轉移潛能和低生存率有關。
我們進一步研究了HIF-1α抑制劑LW6和抗VEGF藥物Avastin對非小細胞肺癌細胞A549和H1299中HIF-1α和VEGF的影響,我們結果表明LW6可以抑制HIF-1α的表達,Avastin對HIF-1α的表達沒有明顯的影響;LW6和Avastin均可以抑制VEGF的表達。結果進一步證明了在非小細胞肺癌中,VEGF的表達受到來自HIF-1α的調控,針對HIF-1α的抑制劑或其他干預手段可以同時抑制VEGF的表達及活性。
綜上所述,聯合檢測HIF-1α和VEGF可更準確地預測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預后。而開發針對HIF-1α干預手段可能成為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更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因為其可以同時抑制VEGF引起的血管形成,當然這還需要進一步的基礎和臨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