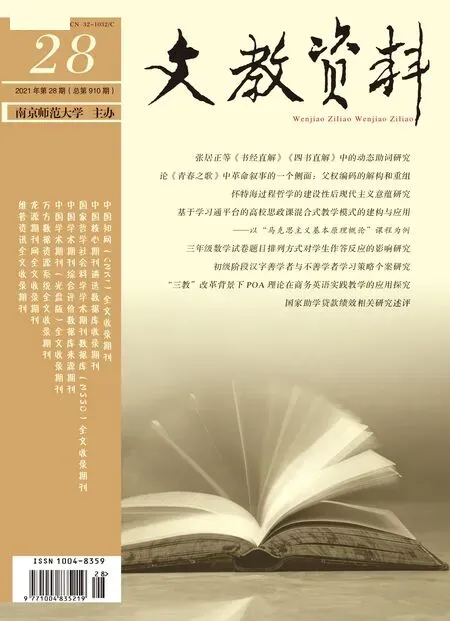論《青春之歌》中革命敘事的一個側面:父權編碼的解構和重組
趙怡然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 長沙 410000)
《青春之歌》中的父權因素是被廣泛承認的,卻很少有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解讀,其中一個原因是,無論弒父也好,救父[9]也好,最終圍繞的話語中心都是革命,革命既是子一輩的反抗實踐,也是構建“新父”的唯一正當合理的力量,這種“新父”的力量以不同的青年革命者為能指,一次次地指向革命中女性作為性別群體的能指化身——主角林道靜。革命敘事交織著父與子以及父權敘事的雙重話語表達,因此很容易成為解讀《青春之歌》的聚焦點。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在革命敘事的解讀中,僅僅涉及情感元素或成長元素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將父與子之間顛覆與重構的關系梳理清楚,我們才能夠看到《青春之歌》所使用的革命敘事的原貌。
一、革命敘事、父與子母題及《青春之歌》中父權社會的解構方式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父親”語義的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其最終都指向了權威、嚴正、不容侵犯或忤逆。主流儒家文化對“父親”的約束極為有限,相對于背負著恩情與罪責的“子”們的“子子”而言,“父父”僅僅以一種建議和感召的形式存在,與其說是儒學綱常中“父親們”必須執行的條件,不如說其僅僅是出于思想架構的完整性而設置的表象性的權力軟化和內傾的體現。子犯父是大逆不道;父犯子,則早有舜之于瞽叟的榜樣。儒學中父與子在“家”中的話語場域是對政治的直接映射,是君與臣在“國”中關系的母命題。因此在封建時代末期,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父與子的關系及其闡釋有著對立化和激化的傾向。但在封建政權沒有被推翻之前,對這一關系的反思和指控必然是有限的。直到清末民初,父與子的命題才產生萌芽,但仍然“脫離不出孝的話語”[10]。
“五四運動”不僅是20世紀中國政治的重大轉折點,在社會文化層面也成了文化解放的代名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個性、自由的張揚真正開啟了中國文學的啟蒙時代。在這一時期,隨著西方現代理論的大量翻譯和介紹,父與子命題中的矛盾似乎因為弗洛伊德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結”的引入而有了科學的闡釋。弗洛伊德超越了一切國別和文化與全人類產生對話的生物學視角,讓這一命題處于樸素、本原、難以超脫的生物性的統攝之下:所有的“子”都有自覺或不自覺的戀母情結,出于這種戀母情結,兒子潛意識中總會抗拒、顛覆父親的權威,甚至有顛覆式的“弒父”傾向[11],父與子的母題受到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傳統話語建構下的父與子關系對“子”的壓抑正處于“五四”所張揚的個性解放內核及其主導群體——青年學生、學者——的對立面,所以對這個命題的關注和其自身的發展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議程設置的發展是一致的。在西方現代理論的載體《新青年》《星期評論》《每周評論》等刊物中,現代性文本里父與子的母題是時代整體文學解放所產生的新視角中的一個分支。具體作品中,胡適的《我的兒子》、蕭軍的《第三代》以及30年代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張天翼的《包氏父子》都有顛覆傳統父子關系的傾向。40年代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也是對這一主題的繼續發展。
革命敘事的產生比父與子母題的討論略晚。“所謂‘革命敘事’產生于20—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義的史學”[12],“第一次引入了蘇聯革命理論的基本觀念”。在經濟層面,強調生產關系對經濟社會的決定性作用;在政治層面,突出革命組織帶領底層民眾反抗來自國內外的壓迫勢力的必要性,與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基礎及其在蘇聯的實踐密切相關。“五四”之后的文學經歷了一個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型過程,從早期的白話文運動被郭沫若以“破絮襖上打補綻”“污粉壁上涂白堊”但內里資產階級仍然植根其中的評價否定和批判開始[13],至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中國共產黨站上主流政治舞臺,早期共產黨人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14],革命敘事在主流文學中呈上升趨勢。隨著1928年國共兩黨合作破滅,無產階級文學聲勢凸現,一些文學雜志和“革命文學”的倡導者甚至對文壇的引領者們發動攻擊。[15]30年代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革命文學”的理論和創作都不斷發展,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手法逐漸風靡。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之后,眾多“精英作家”都進行了自我反省,以現實革命和工農群眾日常生活為主的敘事逐漸形成壓倒性的趨勢。解放區文學的要求讓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相較于“五四”啟蒙時期都呈現出單一化趨勢,父與子母題作為一種隱藏文本幾乎以常態性的姿態出現在革命敘事中。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學”延續了這一傾向,“子”一輩作為革命的引領者或是第一接受者,決定著“父”一輩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以政治標準為唯一標準,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必然被“子”一輩“弒殺”,而底層的、持有落后觀念的工農群眾往往與同時作為革命主角和文本主角的“子”一輩具有某種血緣瓜葛,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為“被拯救”“被開化”的受教育對象。
革命敘事及其文學作品載體中從來沒有強調過父與子關系存在的必然性,但與將封建地主階級的反面能指無意識地定位成衰老、頹朽、迂腐等特征并存的父輩形象相類似,作家們對父與子母題的運用幾乎是一種無意識的運用,比如《家》中高老太爺和覺慧的沖突暗暗交織著父與子的權力爭奪;《雷雨》中大罵周樸園的魯大海是具有強烈反叛意識的“子”一輩的代表;《包氏父子》中父權的覆滅以老包寄生在小包“往上爬”的夢想破滅和兒子小包在老包身上的經濟寄生貫穿始終這一對極具張力的矛盾境況呈現,等等。在《青春之歌》所處的“十七年文學”語境中,這一母題表現模式的主體性發生了偏移,父與子更多是以政治隱喻的面貌出現。與“五四”時期相比,作家們以對父與子關系的敘述和表現推動革命敘事的發展,卻沒有將其作為主題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而言,革命敘事似乎代替了一切文本含義,在同一文本中的其他敘事元素統統變成了“他者”,以一種被驅使的姿態載負著闡釋、凸顯革命敘事的任務。《青春之歌》因其敘事元素的豐富性和女性敘事而尤其彰顯了這一矛盾。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構建下,作者不得不“犧牲一些女性化的東西”,直接的表現就是林道靜雖然以“準主體”的形象出現在文本中,卻不是“精神的核心”,而某種意義上只起到了敘事聯絡作用,成為一種“結構的核心”[16]。
這一點在小說剛剛出版所引發的五六十年代的討論中也可見一斑。《青春之歌》在出版之后引起巨大反響,引發了文化界的廣泛討論,但討論的重心圍繞著“小資產階級情調”和“知識分子的革命成長道路”展開,分立兩派。性別敘事的問題、革命敘事如何構建的問題根本沒有提及。可以說,這一時期,也就是關于《青春之歌》的第一階段的解讀,是處于政治話語統攝之下的解讀,以政治視角為唯一視角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其在社會泛文本化中的表現恰恰與這一時期作品中革命敘事對其他敘事方式、革命主題對其他主題的主導姿態相印證。
“新三板”市場原指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進入代辦股份系統進行轉讓試點,因掛牌企業均為高科技企業而不同于原轉讓系統內的退市企業及原STAQ、NET系統掛牌公司,故形象地稱為“新三板”。
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探索這一時期作品的革命敘事時,反而應該從其統攝之下的子命題入手,這些子命題共同構成了革命敘事的基本內容。
在革命敘事對傳統父權編碼的解構中,父與子的關系圍繞其政治立場呈現出多種形式。本文選取林伯唐、王鴻賓為典型代表,探討兩種截然不同的“父”一輩的命運及其中隱含的各類子命題。
二、弒殺
在明確階級立場的情況下,被弒殺的“父”以對立階級的面貌出現。《青春之歌》中出現的這一類典型主要有林道靜的父親林伯唐、余敬唐、羅大方父親、胡夢安等人,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勢力、國民黨軍閥官僚勢力的化身,是這兩種勢力的核心人物,某種意義上具有精神象征作用,而他們的結局也直接地對應著政治性的隱喻。
“子”一輩對于女性而言的父權重建是文章的主體,為了突出林道靜在革命感召下的成長、凸顯“子”一輩革命者的光明面貌和引領作用,從而揭示革命正確性及必然走向成功的終極主題,舊的父權編碼的解構在小說中處于次要地位,在篇幅和敘事手法上都要為革命的新父權重構讓位。因此我們看到的這幾種革命對立面的代表,常常以碎片化的面貌,或僅僅在主角的描述中作為陪襯的角色出現。
林伯唐作為林道靜的生父,在文本中主要對應的是封建地主階級勢力,是舊的父權社會編碼中的重要因子。他在文中有兩種存在方式,一種是具象的、具有主體性的人物(大部分源于林道靜的回憶),一種作為主角林道靜身上的“黑骨頭”階級象征而存在。楊沫對林伯唐的具體塑造集中在文章開頭第二章林道靜對于自己身世的回憶中,主要情節則為玩弄林道靜生母秀妮、聽從徐鳳英的意見送林道靜上學兩節,緊接著“1931年的一天”,林道靜“高中畢業只有兩個多月”的時候,作者就從林道靜的視角道出了他的結局:“家里破產啦——我父親因為地權的事打了官司,身敗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股腦兒瞞著母親全賣光,帶著姨太太偷跑掉了。”[17]在這之后,林伯唐作為小說人物的形式,在文本中幾乎銷聲匿跡,但其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象征卻在林道靜身上得到延伸。對于這種階級精神的弒殺過程正是林道靜在“子”一輩革命人的引領下不斷走向革命的成長過程。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章中,林伯唐作為一個人物“已死”,他的舊父權以“出身”的方式在林道靜身上留下痕跡,成為小說革命敘事的起點,當林道靜徹底消磨掉自己身上的“黑骨頭”,成長為共產黨員,并順利領導了北大的學生運動的時候,林伯唐及其象征物才被徹底弒殺,而這也意味著小說的完結及革命敘事的完成。
在林伯唐一隱一顯的兩種敘事埋藏中,其實蘊含著另一個命題:顯性的地主階級主體終將走向滅亡,這是淺顯而容易的任務,但“地主階級出身”則更為復雜。從這個角度而言,林道靜在革命道路上不斷犯錯,同時帶著強烈的羞恥感和慚愧感對自己進行全盤否定式反省的成長經歷,展示了作品所處的五六十年代地主階級出身者的生存狀態。有人將她的成長解讀為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筆者認為這一身份并非林道靜處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十七年文學”所處的時代背景正是“一化三改”,社會主義改造不斷深化的過渡時期,各行各業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剔除和改造顯然仍然是主流話題。地主雖然因土地被沒收而從舊的父權寶座上跌落,但積重難返的階級矛盾并沒有立刻得到緩解。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中,階級印記明顯清晰于知識分子的群體印記。林道靜的成長過程就是與林伯唐一次又一次地割裂、分離、劃清界限,直至將其完全剔除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林伯唐作為“父”的角色在文中不斷被放逐和懸置,而林道靜對青年男性革命者的追隨,則向我們展示:“黑骨頭”的出身印記只有通過“認父”于革命及其能指,只有通過自我放逐的痛苦過程,才能完全弒去,獲得純潔無瑕的新生,與此同時,主體也將在革命事業的新起點上為自己重新命名。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林道靜與父親的決裂不僅僅是與具象能指的決裂,還是一種自我決裂。在精神象征的層面,她的“成長”過程不僅是對“父”的弒殺,也是一種“自殺”。這里用的是“自殺”,而不是“自我改造”,這是因為我們還應當看到,林道靜身上所謂的“資產階級的”“黑骨頭”的元素恰恰是她有別于常人的性格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融合了濃烈的個人印記,甚至能起到指代主體的效果。小說的敘事起點,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剛剛高中畢業的女學生是這樣一副形貌。
不久人們的實現都集中到一個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著用漂亮的白綢子包起來的南胡、簫、笛,旁邊還放著整潔的琵琶、月琴、竹笙……這是販賣樂器的嗎,旅客們注意其這行李的主人來。不是商人,卻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寂寞地守著這些幽雅的玩藝兒。這女學生穿著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里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沒有同伴,只一個人坐在車廂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動也不動地凝望著車廂外邊。她的臉略顯蒼白,兩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這個樸素、孤單的美麗少女,立刻引起了車上旅客們的注意,尤其男子們開始了交頭接耳的議論。可是女學生卻像什么人也沒看見,什么也不覺得,她長久地沉入在一種麻木狀態的冥想中。[18]
場景中人物的獨特表現,不僅讓車中人印象深刻,也很容易給閱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用漂亮的白綢子包起來”的樂器、表情寂寞,手里“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都是無產階級工農子弟們難以觸及的元素,卻極具個人色彩。而與之相對的,在文章末尾林道靜成功領導北大學生游行的高光時刻,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描述。
道靜、侯瑞、劉麗、韓林福、吳禹平摻雜在許多男女同學中間,接二連三地搶奪水龍、打碎消防器,向攔阻他們、毒打他們的軍警肉搏。道靜、曉燕、李槐英她們都幾次三番地被打倒在地上,頭發蓬亂了,臉青腫了,鼻孔淌著鮮血,但是她們和許多被打倒的同學一樣,立刻又昂然地立起來,不顧一切地繼續向前沖去。[19]
對于林道靜的描寫被對革命者集體群像的描寫所替代,個人化特征的蹤影蕩然無存。在主體將自我舍棄而投身集體的過程中,與地主階級出身標志的決裂使林道靜不以個體化的面貌存在,而成為革命集體的能指,或者說,泛指的概念化構成。
另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林伯唐的“被弒”以破產和流亡為文本中的直接表現形式,其他“父”一輩的“被弒”也并不單一表現為肉體的消亡。由于舊父權被解構的次要和他者地位,這些父親的“被弒”更多是敘事意義上的,比如羅大方的父親,在上卷第十九章羅大方與盧嘉川相見時前者的描述中出場。從羅大方與盧嘉川的對話中,我們了解到他“費盡力氣托了不少朋友花了上千的大洋”才把羅大方保釋出來,唯一的希望就是“老老實實地給我讀書”。但對于與自己政治立場對立的官僚資本主義,羅大方對即使剛剛救了自己的至親也這樣說道:“父親,你可賠了本了!我不值一千大洋,也不值得你那些朋友的隆情盛意,更值不得上美國去鍍金。”“倒霉的不一定是誰,你這塊同胡博士一起到美國鍍過的燦爛的黃金,不準哪一天就要變成糞土呢……”[20]以阻撓羅大方參與革命事業的敘事目的存在的羅父,很快在這種正面出擊中被弒殺,已經堅定了革命信念的戰士毅然決然地走向了與父輩的決裂(此處文本明確指向羅父及其朋友,意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黨羽)。羅大方和羅父的正面交鋒也是小說中“子”對“父”舊日權威顛覆性弒殺的典型代表。
與此同理,胡夢安所含有的包辦婚姻、官僚資本主義等敘事元素,也在林道靜的拒婚及成功走上革命道路的結局中被徹底弒殺,但與此同時,他所象征的官僚資本主義還在戴愉身上得到了延伸。戴愉同時處于“官僚資本主義”和“叛黨者”兩個范疇的中間地帶,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使他無法融入官僚資本主義隱喻性的政治能指象征,而只能以一種被支配者和延伸物的形式存在。戴愉身上不僅背負著“保父”的罪責,還運行著對革命之“子”的背叛,因此如果說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只作為敘事目的出場,以一種目的旁落的姿態被“弒殺”,那么戴愉所犯下的更加不可饒恕的錯誤則將他引向了肉體及其代表物的雙重消亡。
誰知就在這時,一條粗大的麻繩已經套在他的頸脖上,而且越拉越緊。他再也喊不出聲音來,可是,他卻還能夠聽到王鳳娟的聲音:“你這廢物!連一個王忠都領導不好!把北平的學校鬧得一團糟……”她突然把聲音提高,“送他回老家!給他一個整尸首!”汽車飛馳這開到了郊外。在荒漠的昏黑的野地里,戴愉又被從汽車里摔了出來。慘淡的星星仿佛嘲笑般的還在對他僵硬的尸體眨著眼睛。[21]
游離在“父”與“子”之間的戴愉遭受了“父”與“子”雙方的遺棄,為了保持“子”一輩革命者們的光輝形象,楊沫在文中對戴愉被弒殺方式的敘述中刻意強調,“這不是共產黨員江華,這是他的情婦兼上級王鳳娟。”戴愉被他投向的官僚資本主義弒殺,從敘事意義的角度,可以說是比較徹底地完成了對舊的父權編碼中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解構。就像林道靜只有經過漫長而痛苦的“自殺”過程而將自己融入革命集體中一樣,作者借戴愉的結局向我們展示了投奔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唯一下場。在《青春之歌》中,戴愉是唯一以“叛徒”的身份出現的子一輩革命者中的異類。與此相對應,我們發現,以對立的政治面貌出現的其他舊父權的舵手在文本中都不是單一的,作者不僅對其中的個體進行重點描繪,也有不少時候安排他們以集體或多主體的方式出場,比如林伯唐、余敬唐、和林道靜在農村“歷練”時期遇見的宋郁彬、宋貴堂父子,都是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典型代表,羅大方爸爸和官僚朋友們、胡夢安、鮑縣長等,都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這些人物及其代表的階級在文章中以革命對立面的方式不斷出現,用于烘托和反襯革命者的正義、頑強、大公無私,革命道路的艱險、光輝和唯一正確性。但唯有從革命者內部分化出的“叛徒”的角色由戴愉一己承擔,這才能涉及“子”一輩父權的重組問題——“子”一輩的革命實踐革命應當是純潔的、先進的。
三、拯救
革命敘事決定了“子”對“父”的主流態度必然是弒殺。或者說,“父”主要作為舊父權權力體系的能指而存在。但在現實中,“父”一輩成分是多樣的,為給讀者呈現舊父權走向光明的空間及可能性,抑或是為了再次確認知識分子的覺悟性和改造價值,與林道靜的成長相呼應而維持敘事的完整性,楊沫在《青春之歌》中也設計了幾位舊父權組成中的“異類”,其中重點刻畫的代表是王曉燕的父親王鴻賓。有意思的是,父權與子權的“異類”代表以父與子、主與客的方式在王家會面,分別背叛了他們本應隸屬的權力結構,作者視角的文本也許是想通過揭示二者結局的反差性向我們再一次印證“子”的反抗必將取得勝利,盡管在今天看來,王鴻賓的被拯救過程也許包含更多當時社會泛文本語境影響下的語義。
在得知戴愉被殺之后,作者緊接著便敘寫了王家的場景,在這個場景中,敘事主導并不是與戴愉關系最親密的王曉燕,而是已經堅定朝向革命道路的王鴻賓。片段開頭,王鴻賓就以“主角”的姿態首先出場:“王鴻賓教授在他朋友狹窄的屋地上,背著手不停地走來走去,顯得很煩躁。”在王曉燕道出兩人情侶關系的破滅時,王鴻賓已經按捺不住,不辨信息真偽地開始破口大罵。
王教授抬起頭突然把手一揮,把眼一瞪,好像戴愉就站在他面前,他凜然地呸了一口道:“我明白了!奸細,叛徒,原來是偽君子,是無恥的走狗,我們干我們的工作,量他還能怎么樣我們?最后再看誰勝誰負好了。”[22]
一系列的語言動作進一步表明了王鴻賓的政治立場朝向,在對戴愉叛徒身份的批判中,對“子”的朝向不僅戰勝了對“父”的慣性頑守,甚至戰勝了“父性”,王鴻賓因此而被異化成政治話語的代言人。王鴻賓對于這一角色的承擔實際上是不符合革命敘事規范和《青春之歌》全書的敘事慣例的,它本應當由真正的“子”一輩革命者來充當。但此處為了突出這一父輩中的“異類”所具有的極高的思想覺悟和成為革命者的潛質,王鴻賓承擔了這一功能。面對女兒在愛人是叛黨者和已經去世的雙重打擊下的精神崩潰,王鴻賓唯一明確指向女兒現狀的安慰只有一句“燕,可不要消極呵!”而這句話與其說是王鴻賓從擔憂女兒情緒狀態的角度出發給出的規勸,不如說是為下文政治話語的輸出所作的鋪墊。
“ ,還沒有問你,共產黨方面不懷疑你嗎?還可以相信你嗎?”教授皺緊雙眉莊嚴地追問了一句。[23]
作者在描寫王鴻賓的時候實際上已經無意識地把他當作真正的“子”一輩革命者看待了,因此王鴻賓“皺緊雙眉”“莊嚴”地以革命衛道士的姿態詢問王曉燕。作者在此不知不覺地應用了對革命者進行描述的話語體系。王鴻賓與王曉燕之間關于“黨是否信任”的問話,其實是“子”一輩革命者所建構的權力中心黨的自問自答:黨面對一個曾經受叛徒誤導,與叛徒結為情侶的“有罪者”的態度,是苛嚴不近人情的嗎?不是,“你問共產黨還相信我嗎?相信!完全相信!不是黨來拯救我,我就真的完了。”作者把黨的寬容和感召力的語義融入王鴻賓和王曉燕的對話當中。
與此同時,作者對王曉燕的自白的敘寫,也許是想由讀者視角再次表現黨的巨大感召性,并以這種感召性為契機,引導王鴻賓最終以父輩的身份參與學生運動,完全將自己從舊父權的編碼中抽離,而以子輩的面貌出現,但事實上,楊沫早在王鴻賓與王曉燕的這一段對話中就確認了其革命者的身份。
關于《青春之歌》所展示的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的處境和面貌,有學者認為這是作者將林道靜的“小布爾喬亞”的情感敘事被革命敘事改頭換面這一安排所集中體現的效果[24],但就文本而言,作者對王鴻賓投身革命事業過程的敘述更加能夠突出這一隱性命題。在文章的末尾,主角林道靜作為一個“準革命者”,對北大學生運動的領導是她的成人儀式;對王鴻賓而言,這也是他脫離舊父,投向新父的告別禮和接風宴。《青春之歌》第二部第四十四章中,完整記述了王鴻賓從在黨的感召下的自我檢討、自我矯正到投身運動的全過程。從知識分子群體象征的層面而言,這一章就是整部《青春之歌》林道靜成長軌跡的縮影,且在開頭部分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罪數”進行了更為明晰的清算。
在起這樣一個念頭之前,他當然不無矛盾。他想到了反動統治者的淫威;想到了多少愛國人士只為爭取起碼的自由和民主而身陷囹圄,甚至因此上了斷頭臺;他想到了他也許因此而被學校解聘而失業,甚至被捕入獄,那么妻子、他心愛的女兒們,將失掉丈夫、將失掉父親;而他自己呢,也將吃到從沒吃過的苦頭……雖然當年由于和胡適的接近,受過他的影響,許多問題認識不清……[25]
文本中敘述的王鴻賓的“矛盾”和所受的胡適的影響,其實是作者楊沫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檢討。這一點在林道靜身上,表現為面對男性革命領導者她一次次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幼稚”,每一位男性革命領路人的出現都是林道靜思想上的一次重大洗禮,男性領導者的到來也往往意味著現實困境的解脫和被拯救。但由于性別視角、階級出身視角的差異,林道靜身上背負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被弱化和被遮蔽的狀態,換言之,作為主角,林道靜身上背負的命題更加復雜化、多元化,因此對于知識分子的象征性而言必然是要被削弱的。王鴻賓雖然背負著父與子對權力的爭奪,但畢竟卸下了性別敘事,階級敘事在文本中也沒有被突出說明。因此他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其象征性是比較純粹、集中的。當王鴻賓加入學生隊伍的運動時:
第一次,王教授像一個姑娘般臉紅了。他望著這些青年學生純真的熱烈的眼睛,忍不住熱淚盈眶、喉頭哽咽。他頻頻向人群揮著手,一邊揮手一邊拉著妻子,像個小學生似的,慢慢地羞怯地走進排好了的隊伍當中去。[26]
作者在這里所運用的一系列比喻的喻體:“一個姑娘”“小學生”,是明顯與王鴻賓的身份和性別不符,甚至相割裂的。作者有意無意運用的婦女兒童的形象,在時代語境下帶有明顯的弱勢象征,在這里,王鴻賓并不以“北大歷史系教授”的身份存在,他真正代表的精神內涵蘊含在婦女和兒童的喻體之中,曾經的舊父權體系中的因子在投向革命道路時呈現出的孱弱,是這一系列在男權視角看來甚至帶有羞辱意味的描述存在于文本的深層原因。
四、結語
本文所提供的從父與子命題討論革命敘事中舊父權編碼的解構,注定只是從革命視角全部解讀的一個側面。在這一邏輯架構下,還有女性視角下“子”一輩革命者對父權的重組的命題。在舊父權的消亡和新父權的建立間,《青春之歌》所展示的女性“獨立”“自由”僅僅只是一種幻象。這種幻象因為時代的變遷在當下已經不復存在,但在作品面世后的五六十年代,卻呈現出巨大的感召力。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注意到,也應當有所認知的。本文所選取的解構視角,意在為持續不斷的《青春之歌》研究提供一種新視角和新思路,在這一道路上,其解讀無疑還有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