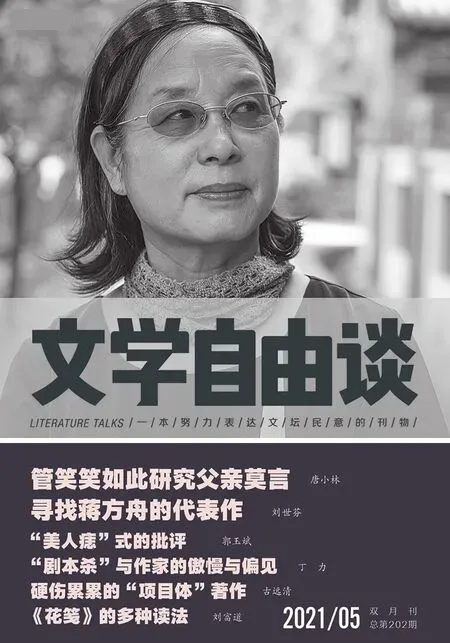斯蒂芬·茨威格的困惑
□狄 青
很早便開始讀斯蒂芬·茨威格,對他在華語世界里的巨大聲望早已習以為常,以至于某一天,當我對這位偉大作家產生了某種困惑和懷疑時,自己都嚇了一跳;但我還是感到懷疑和困惑。
令我疑惑的,不止是他對納粹針對自己猶太同胞的瘋狂殺戮少有(甚至沒有)激烈反彈,而是一直到他被迫流亡的前一天,都沒有放棄與納粹政權妥協乃至于形成某種“默契”的努力。盡管在寫給羅曼·羅蘭的信中,他表現出了對時局、對他所看到的事實相當的驚懼與惶恐。即使單純從文學創作來講,曾經有很多論者都談到,茨威格并不是那種能夠寫出“宏大題材”的作家,他的創作面實際上比較狹窄。的確,茨威格是個完全沉浸在自我精神世界里的人,他的視野并不是很寬闊,他對社會尤其是對底層社會的認知比較欠缺。事實上,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寫出傳記《瑪麗·安東內特》之后,茨威格就開始生活在對未來的恐懼和對往昔的浪漫回憶之中。他在致高爾基的信中說道:“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為了成為一名真正偉大的作家,我所缺少的正是無瑕的淳樸和從事重大構思的能力。”
1933年5月10日的晚上,德國柏林的歌劇廣場中央,大火熊熊燃燒,一群年輕的德國大學生正在歇斯底里地將從圖書館和書店里搜集來的大量書籍進行焚燒,周圍有數千人在觀看并叫好。被焚燒的包括近百位德語作家的書籍和部分被翻譯成德文的外國作家的書籍。德語作家包括亨利希·曼、布萊希特和茨威格,外國作家則包括高爾基、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等。
這一事件令居住在薩爾茨堡的茨威格驚訝得合不攏嘴。事實上,就在同一天晚上,德國多個城市都有群情激奮的學生在焚燒書籍,被焚燒的書籍中皆有茨威格的著作。茨威格一下子蒙了,他不明白,自己的書到底觸碰了第三帝國的哪項法條?而事情的發展卻已經不以他是否明白為轉移了。這無疑是一次鄭重的提醒,比他最好的哥們兒、奧地利作家約瑟夫·羅特對他的提醒更為有用。
在此之前,已有奧地利本土納粹從維也納趕到他在薩爾茨堡的家進行盤查。茨威格認為,自己被盤查,可能是因為納粹將他誤認為是阿諾爾德·茨威格了,一定是納粹認錯人了。在斯蒂芬·茨威格看來,阿諾爾德·茨威格是個不折不扣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是猶太人里的“異數”,受到盤查是“應該的”。約瑟夫·羅特告誡他說:你被盤查,不是因為你姓茨威格,而是因為你是猶太人,是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是文明的文人、自由主義者。
茨威格最初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覺得他很可能是不愿意相信羅特說的是真的,并認為自己或許能夠成為“例外”。他始終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與納粹政權相安無事。他甚至認為焚書事件并非出于希特勒、戈培爾以及任何納粹政府官員的授意,而是不懂事的大學生自發干的,他們不過是一群激進又不聽話的毛孩子而已。他在與約瑟夫·羅特的爭辯中,相信會有某種“理智”能夠慢慢戰勝當前局勢的“莽撞”。茨威格相信,納粹瞄準的是政敵、左翼人士、共產黨人以及那些爭強斗狠的人,而他——斯蒂芬·茨威格,不僅是成功作家,還是本分人士,從不與任何政治派別發生聯系,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把自己的嘴巴閉得緊緊的,不說任何讓納粹不高興的話。他相信這樣應該能從納粹政權那里得到某種妥協,可以讓他繼續留在他位于薩爾茨堡卡普齊納山上的氣勢恢宏的古堡式的家里。
彼時的茨威格甚至認為,同為奧地利出生的說德語的人,同為喜歡藝術的人,阿道夫·希特勒會對他這個馳名世界文壇的“老鄉”有所眷顧,即使不會引為座上賓,也會網開一面。許多資料都表明,茨威格對在納粹統治下閉嘴茍安尚存不少幻想。他還通過各種渠道攀附德國的權貴、出版商,極盡低調妥協之姿態。他這樣做,也是存有這場災難會很快結束的希望。一直到1933年末,他還在為自己和納粹政權之間的妥協做著最后的努力。他甚至寫信給德國的出版機構,聲言自己與德國著名的反納粹作家克勞斯·曼(大作家托馬斯·曼的兒子)“劃清界限”。
對那位與他同姓的猶太人——阿諾爾德·茨威格,斯蒂芬·茨威格從一開始就無好感。這種惡感并不僅僅來自于“文人相輕”,更源于二人在價值觀、人生觀方面的不同頻。阿諾爾德不僅是德國共產黨人、左派作家、“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斯蒂芬·茨威格看來,還是一個生活不檢點的人。阿諾爾德是德國最有錢的作家之一,為人十分高調,公開與法定妻子和情人共同生活;這讓“正統”的斯蒂芬·茨威格完全無法接受。所以,茨威格認為,像阿諾爾德這樣的人,被納粹“關注”或許是應該的,而像自己這樣安分守己的作家,對任何一個政權來說,都是無害甚至有益的。最終,還是約瑟夫·羅特將他從幻想拉回了現實,救了他的命。羅特警告茨威格:“猶太人被迫害,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么事情,而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羅特再三請求他趕緊離開薩爾茨堡,去英美或者南美,越快越好!
茨威格是帶著深深的困惑與不情愿離開納粹統治區的。他既不像他所反感的阿諾爾德·茨威格那樣,選擇逃往猶太人的出身地巴勒斯坦去尋根,也沒有像反納粹的克勞斯·曼那樣,加入盟國軍隊參與對納粹法西斯軍隊的反攻。他內心的復雜與糾結,部分反映在了流亡之后所創作的作品里。他的困惑實際上至死都沒能消除。
茨威格的困惑,事實上也是當時生活在歐洲德語區所有與他有類似身份的猶太人的一致困惑:我喜歡藝術,不偷不搶,安分守己,謹言慎行,不參與、不關心政治;如果一定要做出選擇,我會選擇支持納粹政權,甚至可以捐出大部分金錢,并自覺遠離一切左翼組織和個人,明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不與他們中的任何人接觸……可是納粹為什么還要把我關進集中營,最后還要殺掉我?
茨威格因為猶太人的身份不得不流亡。他一定想起了他喜歡的德語作家卡夫卡。卡夫卡的過早離世,讓他沒來得及看到自己的擔憂和預言成真;茨威格多活了十幾年,無奈地看到了“昨日的世界”支離破碎,讓他的“三觀”徹底崩塌。在這種心態下,他沒有選擇拿起槍桿或筆桿,去和納粹政權做針鋒相對的斗爭,做遺民也不可能,剩下的,恐怕就是避免不了的一條路了。
斯蒂芬·茨威格的困惑,事實上也是很多同時代作家的困惑。比如帕斯捷爾納克——他出生在莫斯科一個被同化的猶太人家庭。母親是魯賓斯坦的學生;父親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是莫斯科美術、雕塑、建筑學院教授,俄羅斯和蘇聯著名畫家,給托爾斯泰的作品畫過插圖,曾堅決否認自己的猶太背景,并接受洗禮。帕斯捷爾納克從小到大極少提及自己的猶太背景。當他被蘇聯作家協會“清洗”,尤其是當他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被批判,人們普遍稱他是“猶太佬”;這令他感到無比困惑。他不知道,哪怕從父輩那里就從沒自認為純粹的猶太人,卻依然要承受那些人對這個民族的排擠與蔑視。
好在,困惑的茨威格與困惑的帕斯捷爾納克都遇到了前來拯救他們的女人。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與比他小二十八歲的女人(也是最懂他的女人)伊麗莎白·綠蒂,相互擁抱著死在了巴西里約熱內盧公寓的床上。
1949年10月9日,帕斯捷爾納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因蘇聯作協的誣告被逮捕。審訊者把她關進存有幾十具尸體的太平間,逼她交待帕斯捷爾納克的種種反蘇言行。伊文斯卡婭毫不懼怕,把一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一口咬定《日瓦戈醫生》手稿是由她交到國外的,同帕斯捷爾納克無關。在被排擠的孤獨中,帕斯捷爾納克絕大部分時間都同伊文斯卡婭在一起。伊文斯卡婭對帕斯捷爾納克忠貞不二,預言他遲早會被蘇聯人民所接受,并勸他原諒現在反對他的那些人。帕斯捷爾納克曾多次試圖自殺,都被伊文斯卡婭阻止。伊文斯卡婭的鼓勵是帕斯捷爾納克能夠活下去的重要因素。盡管這個比帕斯捷爾納克小二十二歲的女人,在帕斯捷爾納克生前既沒有獲得妻子的名分,也沒有從他那里得到金錢和名聲的補償,反倒為他坐了五年牢獄,幾乎付出了自己和家人的一切。
兩個女人,挽救抑或說慰藉了兩個偉大卻并不堅強、甚至充滿困惑的作家心靈。這至少令我相信,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美好的愛情。她們或許是上天賜予茨威格與帕斯捷爾納克這兩位天才的禮物,不是誰都能夠碰到,更不是誰都能夠有幸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