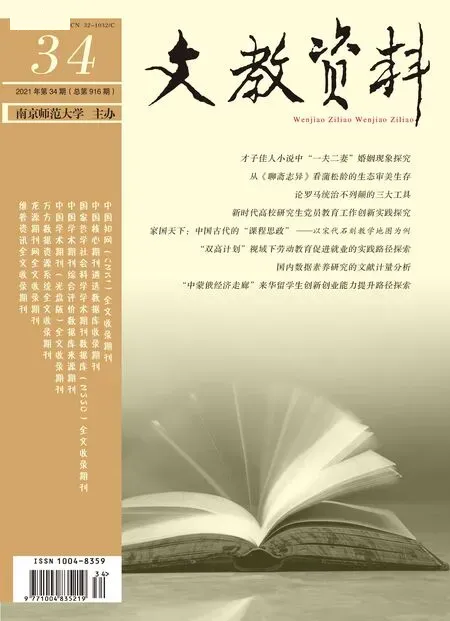虞世南與易學
于 磊 孫世平
(1.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潛艇學院 2.青島大學,山東 青島 266199)
《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對其解釋、闡發形成的易學,有著悠久的歷史。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易學研究成果斐然。相較而言,唐代易學始終是中國易學史中的“薄弱環節”,其成就僅限于《周易正義》《周易集解》等幾部典籍之上。這種“不平衡”造成一段時間內在易學研究領域唐代易學“無話可說”。因此,即使“上承漢魏、下啟宋明”[1]成為大多數學者總結、評價唐代易學時較認同的觀點,但無疑僅憑幾部易學典籍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撐起此論斷,亦不能全面展現唐代易學發展與演變的過程。不可否認,這是囿于傳統經學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的結果。有鑒于此,本文選取唐朝名臣虞世南,通過探究其現存著作中的易學理論,審視其易學成就,并進一步分析、勾勒出唐代易學,特別是唐初易學的內容、特點、趨向。
一、虞世南的易學理論特色
據《舊唐書》記載,虞世南有集三十卷,撰寫過《北堂書鈔》《帝王略論》,參加過《長洲玉鏡》《群書治要》的編纂。目前雖尚無史料表明其有專門的易學著作,但虞氏對《周易》的熟稔、重視是毋庸置疑的。如,他在《破邪論序》說到“愿力是融,晦跡肥遁”[2],源自《周易·遁》上九爻辭“肥遁,無不利”;在《書旨述》中說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3],源自《周易·系辭傳上》“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除了見諸詩文的內容外,虞世南其他著作里對《周易》的稱引更加普遍,如《帝王略論》中對《周易》的直接援引有9 處;《北堂書鈔》中對《周易》經傳作的解釋共有40 處。
虞世南出身的會稽余姚虞氏,是魏晉六朝時著名的江東世族,經學在其家族的文化傳統中一直占重要位置。在易學領域,成就最大者莫過于三國時的虞翻。“虞氏易”是兩漢象數易學的重要代表,從《隋志》《經典釋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來看,虞翻易學在隋唐之時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世族家學是魏晉南北朝思想學術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方式,作為余姚虞氏的一分子,虞世南熟悉其先祖之易說并不奇怪,故在其易學理論中可清晰地看到虞翻易學的印記。
例如,虞世南在解釋《漸》六二爻象辭“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時說:“謹案,‘衎衎’,饒樂也;‘素’,空也。明六二之爻將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俸祿,非素飽也。”[4]虞世南認為此爻“得正”,故象辭中的“不素飽”是借指才能之士恰得其所,無尸位素餐之嫌。但王弼分析此爻的立足點是“得中”,故其解釋為“本無祿養,進而得之,其為歡樂,愿莫先焉”[5],“不素飽”實為警戒之義。對照虞翻對此的解說,“素,空也。承三應五,故‘不素飽’”[6],可以發現其與虞世南觀點的相似之處,即不僅表現在對“素”字的理解,還表現在對爻的整體評價上。又如,虞世南在《北堂書鈔·藝文部一》中談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句時,雖先引用了韓康伯的觀點,但之后說:“謹案,兩儀,天地也;四象,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八卦,乾坤之屬者也。”[7]可見其并不完全認可韓氏的觀點,而是采用了虞翻的思路:“‘太極’,太一。分為天地,故‘生兩儀’也。”[8]不僅如此,虞世南對虞翻易學的承繼還表現為對其“易象”學說的熟練使用。如,他在解釋《系辭傳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時說:“謹案,乾為天,為玉,為日;坎為水,為云,為雨,是觸類而長之義也。”[9]案,“坎為水”是《周易·說卦》的觀點,但“為雨”“為云”是虞翻在解釋《鼎》九三爻“方雨,虧悔,終吉”和《乾·彖》“云行雨施”句時的觀點。特別是“坎為云”,清儒惠棟在《易漢學》里將此視為“虞氏逸象”之一,是其易學的特色、精華所在。可見,虞世南對其先祖易學的繼承、發揚是全方位的。
當然,虞世南對“漢易”的汲取并不僅僅局限于虞翻一人。如,對《師》九二爻“王三錫命”中的“錫”,虞世南說:“‘錫’猶‘賜’也。”[10]王注及之后的孔疏在分析此爻時都沒有明確將“錫”釋為“賜”。由陸德明“鄭本作‘賜’”[11]的記載可知,虞氏極有可能借鑒了鄭玄的觀點。又如,在《天部一·天一》中,虞世南在解釋“何天之衢,亨”時說:“謹案,衢,四達道也。上九處《大畜》之極,畜極乃通,故言何衢。”[12]據《經典釋文》此句的解釋“衢,其俱反,馬云:四達謂之衢”[13],虞氏“衢,四達道也”的解釋應取自東漢馬融之說。再如,其在解釋“日月之道,真明者也”之句時所說的“日月以明正之道照物”[14],與陸績“言日月正,以明照為道矣”[15]之說相似。漢儒的象數易學理論對虞世南的影響是深刻的。
在繼承“漢易”的同時,虞世南對魏晉以來王弼等開創的“玄學易”也極重視。他在《北堂書鈔·地部》的《穴篇》《沙篇》《泥篇》里引用前代易說時,將王、韓易說置于首要位置。不僅如此,信奉“夫道以簡易為尊,物以精微為貴”[15]之說的虞世南,在治《易》之時,許多觀點直接源自王、韓。如,在論及《系辭傳上》“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句時,虞世南所說的“謹案,專,一也。直,方正也。此明乾德統象天也”[17],明顯借鑒了韓康伯“專,專一也。直,剛正也”[18]的理論。
不僅如此,正所謂“前修未密,后出轉精”,虞世南在王、韓易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不少“新解”,這些內容在很多地方與日后的《周易正義》“不謀而合”。如,對《噬嗑》上九爻“何校滅耳,兇”,王弼雖解釋為“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至于‘滅耳’”[19],但并未說明為何此爻可指代積惡不改之人。虞世南說:“謹案,‘荷’,擔荷也;‘校’,枷也。受沒刑之人,為惡既積,刑罰上重,遂至滅‘沒耳’也。”[20]這樣就彌補了王弼的疏漏之處,對此爻的理解不會有突兀之感。對此,孔疏與虞世南實為同一思路:“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擔枷械,滅沒于耳,以至誥沒。”[21]又如,對《系辭傳下》中的“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韓康伯只說“變化無恒,不可為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22],對“其言曲而中”未詳細闡釋。虞世南說:“謹案,圣人制《易》,其旨趣遠,其文辭美,隨爻辭變動而委曲皆中其理,百事皆顯著也。”[23]這與孔疏在解釋“其言曲而中”時所說的“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24]頗相近。
綜上所述,虞世南的易學呈現一種綜合“漢易”與“玄學易”、超越“漢易”與“玄學易”的傾向。將此置于隋代以迄唐初的學術大背景下,可以發現虞世南的這種“理論嘗試”并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與虞世南同一時代的著名學者顏師古,在其名作《漢書注》中使用易學理論時,往往采自王、韓之說,但同時對漢儒之言也一并擇取。如,他對《蠱》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是如此解釋的:“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25]所依據的恰好是漢儒應劭的理論。又如,唐太宗貞觀初年編纂《群書治要》時,虞世南與其他共同參與此事的學者們,直接使用大量的王、韓易說,但同樣沒有將漢易排除在視野之外,如在闡發《否》卦九五爻時提出的“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為木,木莫善于桑,人雖欲有亡之者,眾根堅固,弗能拔之也”[26],借鑒的是漢儒京房、陸績的觀點。考慮到《群書治要》的編纂團隊,不得不承認以“玄學易”為本,但仍力圖兼顧“漢易”,似乎是那個時期學者們的“共同選擇”。
清代的四庫館臣在回顧唐代易學的發展歷程時說:“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27]今天看來,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結論。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序》中曾提道:“其江南義疏,十有余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今既奉敕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征。”[28]可見,彼時學者以王弼易學為本,并不是機械地承襲南朝的治易傳統,而是在大一統的新時代背景下各方參照、主動選擇的結果,所以其本質上不會排斥對“漢易”的使用乃至宣揚。傳統意義被視作是純粹“義理派”的《周易正義》實為兼顧義理與象數之作。如果說,唐高宗永徽年間《周易正義》的正式刊行標志著這種新的易學風尚得到了官方最終認可的話,那么像虞世南這樣活躍于隋代至唐武德、貞觀年間的學者,他們的“易學實踐”則成為日后《周易正義》的先聲。
二、《北堂書鈔》的易學史價值
虞世南在易學領域內的理論嘗試,反映出新的易學時代即將到來。但是,虞氏在易學史上的價值并不僅限于此。他的著作《北堂書鈔》,以“類書”這個特殊的載體,直觀、全面地展現出“漢易”“玄學易”在知識階層的精神世界建構中發揮的具體作用,由此即可為了解唐代易學之所以走上義理、象數兼顧之路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內在因素。目前學界對于“類書”的研究,已經從版本流傳、體例思想、文獻價值擴展到相關的思想史領域。作為后世“收藏家率購以多金”的“四大類書”之一[29],《北堂書鈔》在目錄編排上雖有明顯的、服務于帝王的“經世致用”色彩,但博采群書的體例仍決定其有相當的思想史、學術史價值。
具體到易學問題,據筆者統計,在《北堂書鈔》中的義理派易說主要集中于王弼、韓康伯二人,共計29 條。此外,王肅之說5 條,班固、王廙、蘇彥之說各1 條。王、韓二人之說,主要出自《藝文部五·名理十八》,共有10 條,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可以說,在虞世南眼中,王、韓易學的主要貢獻在于“辨析名理”。或者說,王、韓易學是在人們論及“名理”問題時能給予最大幫助、啟示的。那么,所謂的“名理”問題,其吸引士人的地方為何呢?自然,這種“玄言”可以極大地激發士人們精神世界中的思辨熱情,就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魏晉南朝士人探求的“名理”是在兩漢黃老形名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求事物的本質、規律及其他事物的關系問題”,其特點是“從不同角度分析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比較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30]。但是,通過《北堂書鈔》這部謀篇布局有著強烈政治傾向的類書可知,“名理辨析”的終極目標并不是單純的“哲學問題”或者“精神需求”,其宗旨是要通過研習圣人經典進一步總結出治國安邦之道。虞世南將“名理”條與記載前賢之作的“著述”條一并納入《藝文部》之下,可見其認為魏晉南朝士人暢談的“名理”是有弼于政治的。
此外,尚需注意的是,王、韓二人的易說在《北堂書鈔》中的分布是相當廣泛的:既有直陳帝王之道的《帝王部》《政術部》,又有與禮樂建設密切相關的《禮儀部》《藝文部》《衣冠部》《酒食部》,更有體現知識階層對客觀自然世界認知的《天部》《歲時部》《地部》。傳統觀點曾認為:“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31]以王弼易學為代表的“玄學易”對《周易》“天道”的解釋似乎僅僅是闡發道家的“道”“無”等范疇。然而,由《北堂書鈔》看來,王、韓易學的特色與價值雖集中體現在像“名理”這樣與邏輯思辨、社會倫理、治國之道息息相關的領域,但它對客觀自然世界并非毫無關涉。這一特點并不為《北堂書鈔》所獨有,對此可以參照比較唐玄宗時期的另一部著名類書—《初學記》。據統計,《初學記》所引述的義理派易學理論中,王肅易說2 條,王弼易說7 條,韓康伯易說1 條,《周易正義》1 條,此外還有傅咸《周易詩》1 條,楊文《易卦序論》1 條。在王弼易說的7 條之中,除了2 條出自《政理部》外,剩下的則見于《天部》《地理部》《鱗介部》等直接關乎自然世界知識的部分。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論斷:誕生于魏晉時期的“玄學易”,除了能激發士人通過渺渺天道建構有益于現實政治的“圣王之道”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需求,這或許成為其在發軔之際相比“漢易”的一個優勢。
如果說《北堂書鈔》的義理派易學主要集中于王、韓兩家的話,那么象數派易學則集中在《焦氏易林》、京氏易學、《易緯》(《易緯·乾鑿度》《易緯·是類謀》《易緯·通卦驗》)。這三家易說主要出自《天部》《地部》《歲時部》:《易林》征引的15 條中,9 條出自《地部》;京氏易學征引的16 條中,10 條出自《天部》;《易緯》征引的12 條中,5 條出自《歲時部》。三家易說之外的象數派易學也展現出同樣的特點。如《歸藏》3 條,2 條出自《天部》《地部》;《周易參同契》《易筮卦洞林》《許氏易交修》所引用者都出自《地部》。
然而,與時政關系密切的《政術部》《武功部》,僅有《京氏五星占》《京房易妖占》《京房易占》及《易緯·是類謀》4 條。兩漢經學家善以陰陽災異指斥時政之弊,每逢災變,“輒傳經術,言得失”[32],這在易學領域無疑首推京房。虞世南在《政術部》《武功部》援引京房之說,應當是此種傳統的延續。但是,包括《易緯·是類謀》在內,即便算上與禮樂建設有關的諸條,即《歸藏》在《禮儀部·饗燕》中的1 條、《易林》在《車部·惣載》中的6 條、《易緯·通卦驗》在《樂部·瑟》中的1 條,象數派易學在社會政治方面也僅有12 條,只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如上所言,大量見于《天部》《地部》《歲時部》三部之中。這種明顯的、巨大的“偏向性”,在與《北堂書鈔》差不多同一時代的《藝文類聚》里有更清晰地呈現。據統計,《藝文類聚》援引易說共有12 家,全為“漢易”系統。其中,《易林》使用了7 條,《京房易飛候》使用了5 條,《易緯·通卦驗》使用了6 條。這3 家之中主要出自《天部》《歲時部》《鳥部》,與社會政治密切相關《帝王部》《禮部》《樂部》《職官部》等無一體現。知識階層面對象數易學時的“旨趣”已經呼之欲出。
概而言之,《北堂書鈔》在編纂宗旨上強調的是時政,突出的是帝王,《天部》《地部》《歲時部》雖然并不是全書的核心,卻包含那個時代人對宇宙天地、陰陽四時、世間萬物的種種知識,體現那個時代人對客觀物質世界的秩序與規律、范圍與邊界的各式信仰。這對人精神世界的建構同樣十分地重要,這正是象數派易學用力尤深的地方。比如,在《天部》《歲時部》《地部》中屢次出現的《易緯》,其闡述的宇宙演化理論及在天文、歷法、音律基礎上對四時物候所作的描述,對后世影響深遠。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筆者于此并不是在夸大《周易》及易學在彼時人們認識客觀世界時所發揮的作用。對此,可以參照《魏書》中的一則記載:“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陳奇),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后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于《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33]此處且不論陳奇與游雅的觀點哪一個更符合實情,其在探究客觀世界時所憑借的重要資源都為《周易》。且此處已明言,提出“蔥嶺以西,水皆西流”地理認知的游雅,熟稔的是漢儒的代表性人物馬融、鄭玄,結合以上內容,不應簡單地視為偶然。
綜上所述,《北堂書鈔》本質上透露出許多唐代易學史上的重要信息:“玄學易”在士人精神世界里占據的是“思辨”“人倫”“社會”等部分,“漢易”則占據“自然世界”部分,即雖然其在六十四卦爻象基礎上構建的世界圖式,很多時候并沒有經過嚴密的分析乃至科學的論證,但是它能為古代的知識分子在解讀客觀自然世界的變化與規律時提供他者欠缺的“理論依據”。很長一段時間,《隋書·經籍志》中“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之言常被用來概括六朝到隋唐間的易學風貌。但有一點值得深思,即為什么在“漢易”愈發“浸微”的唐代,為什么“玄學易”在整個帝國內已得到官方認可并推行的前提下,仍有《周易集解》這種宣揚象數易學的經典之作問世呢?拋開歷史的偶然因素,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唐代易學在其形成之初即包含大量的象數易學成分,雖然唐代學者不再像漢儒那般汲汲于象數學說的發掘與創新,但象數之說并沒有真正離開知識階層的視野,而是積累著、沉淀著,并憑借他者無法取代的獨特價值延續、發展著,終有唐一代,始終與“玄學易”相輔相成。
三、結語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以佛教的“生、住、異、滅”將清代學術的發展歷程凝練為“啟蒙”“全勝”“蛻分”“衰落”四個前后相繼的動態模式。同樣,對易學史而言,以易學著作,或者易學家為主體的片段式、靜態式書寫,雖然重要,但無法充分展現出一個紛繁復雜的發展與演變過程。本文以易學視角對虞世南的剖析,正是試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即使虞世南不是“易學專家”,即使他的易學理論并不龐大且自成系統,但他仍是一位易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人物:他的理論嘗試預示著一套兼顧象數與義理的新式易學體系,即將成為之后的主流、主旋律;他在《北堂書鈔》中對易學學說的分類使用預示著肩負認知客觀世界現象與規律的“漢易”與通過精致的名理思辨構建起全新政治哲學的“玄學易”一同成為知識階層須臾不可離的思想資源。由此,唐代易學的一些重大性問題得以窺見。當然,本文并不意味著將易學視作一個大而無當的東西,從一個全新的窗口評判唐代易學的發展狀況才是本文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