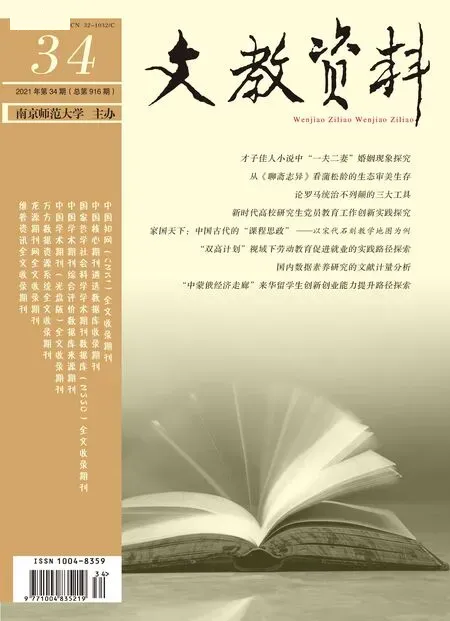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研究進展
張婧雯 周 淼 陳盛華
(南通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漢英雙語閱讀障礙是發展性閱讀障礙(下文簡稱“閱讀障礙”)的亞類型之一,指以漢語為母語、英語為二語的正常兒童所發生的、無法掌握有效閱讀能力且低于同齡兒童一到兩個年級水平的語言學習障礙。閱讀障礙首先在英語國家被提出并受到重視,在學齡兒童中占比高達10%—15%,有學者認為漢語中并不存在閱讀障礙,閱讀障礙在我國受重視的程度也遠不如西方,但我國受閱讀障礙影響的兒童數量眾多,據張承芬等(1996)統計,中國閱讀障礙發生率約為4%—8%[1],McBride-Chang 等(2013)以來自香港和北京的8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認為漢英雙語閱讀障礙大約占閱讀障礙總數的32%—40%。[2]由于這部分兒童的智力水平正常,其閱讀障礙情況極易被忽視。近年來,學界對雙語閱讀障礙的研究指出:雙語閱讀障礙普遍存在于不同雙語背景的兒童中,其腦激活模式與母語閱讀障礙類似;語音缺陷及相關腦結構異常是發生雙語閱讀障礙的主要原因。但是,目前對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特異性、語音加工之外的雙語閱讀缺陷以及早期的干預手段等還缺乏研究。
一、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研究
(一)不同母語背景的雙語學習者的雙語閱讀障礙
在行為和腦功能成像實驗的研究基礎上,我們發現雙語閱讀障礙普遍存在于不同母語背景的雙語學習者中,即雖然幼年時期掌握的母語有所區別,但是在后期學習掌握第二語言時,由于兩種語言所代表的思維模式上的差異,人們普遍存在雙語閱讀障礙,一種語言的學習會影響另一種語言的掌握,而這兩種語言之間的影響,所帶來的不一定都是正遷移或正面積極的。
研究者發現不同語言背景閱讀障礙者的腦激活模式具有一致性,即閱讀障礙者的左腦后部比正常人激活弱,Horwitz 等(1998)研究發現“正常人左角腦回的局部腦血流在任務內,跨受試者在單個單詞閱讀過程中,與紋狀體外大腦皮層和顳葉區域的局部腦血流有很強的相關性。相反,在患有持續性發展性閱讀障礙的男性中,左側角回在功能上與這些區域是分離的”[3],也就是閱讀障礙者的左腦后部較之常人,需要更多的時間進行反應和激活。Klein & Doctor 等(2003)在文字載體類似,如英語和荷蘭語中的雙語閱讀障礙研究中發現,兩種語言都存在閱讀缺陷,并采用了相似的語音發音策略[4],這種相似的發音策略會導致初學者的混亂,給語言的學習帶來困擾,從而造成閱讀上的障礙。韓娟等(2012)也通過在維吾爾語—漢語、印歐語—意大利語等雙語閱讀障礙兒童的研究中發現類似結果。[5]可見,由于文字載體之間的相似性導致的符號識別的模糊,并由此引發的閱讀障礙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雖然不同語言之間腦機制上存在差異,但不可否認,語言的學習也有其所遵循的共同規律,所以大腦對語言的加工也存在相似性。雖然漢語、英語閱讀障礙的腦機制有差異,Siok 等(2004)通過研究發現“左側額葉中的功能紊亂與漢語閱讀障礙有關”,而“左側顳頂區的激活減少是英語閱讀障礙的生物學特征”[6],即漢語閱讀障礙在大腦中表現為左側額葉,英語則在左側顳頂區。但漢英雙語閱讀障礙者的母語與二語加工激活的腦區相似,Ting 等(2017)指出“在說英語的人中右半球的損害會產生主要的空間相關閱讀障礙錯誤”“未來的研究應該進一步檢查右后區在兩種語言的初步視覺分析中的作用”[7]。雙語閱讀障礙可能普遍存在于不同雙語背景的兒童中,也就是不同母語和不同第二語言的兒童都會存在雙語閱讀障礙,雙語閱讀障礙不會只針對某兩種特定的語言存在,不同類型的語言學習都可能帶來閱讀障礙,而語言的類型差異是否會導致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特異性,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雙語閱讀障礙的語言加工缺陷
對語音加工缺陷的研究表明,漢英雙語與母語閱讀障礙兒童的腦激活模式相似,但雙語閱讀障礙的加工缺陷也會在語音層面之外發生。
以往的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由于已知的中英文書寫系統的加工需求差異,發展性閱讀障礙在中文和英文人群中具有不同的神經基礎。而胡偉(2010)研究首次發現,在語義詞匹配過程中,漢語和英語單語閱讀的大腦激活減少顯著相似。在不考慮語言及其正字法的情況下,這暗示不同語言的閱讀障礙有共同的神經基礎,通過觀察發現,兩種語言閱讀障礙的影響在左側角回、左側額中、顳后和枕顳區低于正常激活;漢語、英語閱讀障礙的對比研究顯示,漢語、英語閱讀障礙兒童左腦后部顳頂枕區的加工模式有共性。因此,漢英雙語閱讀障礙與母語閱讀障礙的腦機制相似。[8]漢語閱讀障礙者在加工二語(英語)時會表現出與母語類似的腦激活模式。Ho 等(2005)對25 名有發展性閱讀障礙的中國小學兒童和25 名學習能力薄弱的兒童進行了英語詞匯、閱讀和語音處理任務的測試。在英語測試中,閱讀障礙組的表現都明顯比對照組差,結果表明,漢語閱讀障礙兒童在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時也遇到困難,他們在漢語和英語的語音處理方面普遍薄弱。[9]Ting 等(2017)通過一位中英雙語誦讀困難患者在右后腦皮質的病變發現,雖然在右側皮質后部病變中缺乏中文閱讀障礙的證據,但從雙語的角度來看,右后皮質區域的完整性在表意文字和字母語言的正字法分析中都是至關重要的。[10]Chang 等(2013)通過研究發現:香港37 名中文閱讀能力較差的兒童中,有32%的兒童在8 歲時英文閱讀能力較差;在北京73 名中文閱讀能力差的兒童中,有40%的兒童在8 歲時英語閱讀能力較差,這表明有近40%的漢語閱讀障礙者會發生漢英雙語閱讀障礙。[11]漢英雙語閱讀障礙與漢語閱讀障礙可能有類似的神經基礎,已有的大量證據表明,發展性閱讀障礙代表了一種行為和神經生物學上的語音加工障礙。You 等(2011)通過對具有和不具有閱讀障礙的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中國兒童的正字法和語音加工的神經基礎進行研究,通過字母押韻判斷(語音任務)和字母同/異判斷(正字法任務)的神經反應,探討二語學習和母語學習是否存在共同的神經機制,分析顯示,與典型閱讀者相比,閱讀障礙兒童在正字法處理過程中,左舌/鞘膜回內和枕顳區的激活減少;在語音處理過程中,枕顳區的激活減少,這與之前的以英語為母語者的研究一致。[12]同時Meng 等(2016)研究了漢語被試英語閱讀障礙者在口語押韻判斷過程中的神經反應。結果顯示,受損閱讀者在左側額下回(LIFG)和左側梭狀回的激活減弱,LSTG(左側額上回)和左側梭狀回之間的連接減弱。這些發現表明,第二語言閱讀障礙患者讀者的語音加工受損,從而缺乏對正字法的自動提取。這些發現與英語閱讀障礙的發現相似,因此可以認為,無論英語是第一語言還是第二語言,語音加工受損都會導致顳頂和枕顳區的腦激活水平顯著降低。[13]Li 等(2018)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且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兒童為研究對象,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術探討讀寫能力的神經機制。在第一個實驗中,調查了兩種語言讀寫都存在困難的兒童(都很差,PB)和第二語言讀寫困難的兒童(英語很差,PE)。通過對這兩組兒童大腦結構與對照識字組(CL)進行比較顯示,與PB 組相比,CL 組的左側邊緣上回灰質體積顯著減少,與PE 組相比,CL 組的左側邊緣上回灰質體積中度減少。此外,與PE 組相比,PB 組的左側內側梭狀回灰質體積顯著增大,與CL 組相比,PB 組的灰質體積略增大。在第二個實驗中,探討了兩個非典型區域在兩種語言讀寫能力加工中的作用,分析顯示,左側邊緣上回僅與第二語言(英語)的讀寫能力顯著相關,而左側內側梭狀回與兩種語言的讀寫能力均不相關。這些發現表明,第二語言字母讀寫困難與左邊緣上回的結構異常有關,該區域與語音處理密切相關。[14]因此,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發生可能與大腦中語音處理的缺陷相關。
除語音缺陷外,學界還對雙語閱讀障礙者的語義加工機制進行了探討。舒華等(2000)認為語言是交流信息與思想的工具,是表音、表意的符號系統,語音加工具有普遍性;漢語的表音方式使語音加工變得復雜:漢語是聲調語系,且聲調具有區分性,而這種區分又十分細微,需要學習者具有很強的語音分析能力,這對初學者無疑是一種挑戰,但如果不能及時獲得相應技能,就可能導致語音加工困難。[15]雖然語音缺陷可能是造成母語和雙語閱讀障礙的主因,但作為一個復雜的語言系統,語言的語義和語法加工機制也對語言理解有著重大影響。Chung 等(2010)研究探討了閱讀技能與漢語(L1)和英語(L2)閱讀能力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共對84 名雙語兒童[28 名誦讀困難兒童、28 名實足年齡(CA)對照兒童和28 名閱讀水平(RL)對照兒童]進行了詞匯閱讀、快速命名、視覺正字法技能、L1 和L2 語音和形態意識測試。與對照組相比,有閱讀障礙的兒童在兩種語言上的表現都較差,在英語語音意識加工比在漢語語音意識加工更困難。同時,漢語閱讀認知技能對英語詞匯閱讀能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6]
行為學研究證實,英語閱讀障礙是由語音缺陷造成的,即未能在正字法和讀音之間形成良性聯結,但漢語閱讀障礙有可能不同。Siok 等(2004)發現漢語的閱讀困難不僅是由于正字法到語音之間的聯結程度較弱引發的,還與正字法與語義的聯結有關。漢語閱讀障礙腦區激活與英語閱讀障礙相關激活模式不同,漢語閱讀對于語音信息的依賴要小于英語,漢語閱讀障礙兒童的閱讀更依賴與語義加工相關的額葉中回。[17]因此,Chung 等(2010)研究發現兒童閱讀障礙與跨語言閱讀有關認知技能的轉移有關。盡管中英書寫系統存在差異,但影響母語閱讀的技能缺陷也會對第二語言產生影響,即第一語言為漢語的兒童在加工英語時會采用不同的語義加工策略,這些策略可由母語遷移給二語。[18]
除語音之外,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特異性可能與語法等層面的加工缺陷相關。語法層面的研究證實雙語閱讀障礙兒童的語法能力高于僅有母語閱讀障礙的兒童。Vender 等(2019)對有無閱讀障礙的單語兒童和雙語兒童的人工語法學習進行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在任務完成速度方面,雙語具有普遍的優勢,而在任務的準確性方面,閱讀障礙普遍存在劣勢;雙語閱讀障礙者比單語閱讀障礙者表現得更好。這一結果表明,雙語并不會對誦讀困難癥產生負面影響,相反,相比單語閱讀障礙相比,雙語閱讀障礙患者還會產生顯著的認知和語法加工優勢。[19]
二、研究的趨勢與不足
(一)研究領域逐漸擴大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閱讀障礙逐漸從神經科學轉向心理學、教育學和語言學等領域,從神經科學角度看,視覺功能是進行閱讀的前提;準確識別和辨認聽覺刺激是正確閱讀的必要條件,輕微腦功能失調是發生閱讀障礙的內在原因,先天性的語言能力落后則會導致閱讀障礙。因此許多研究者認為,閱讀障礙與視覺缺陷、聽覺缺陷、極輕微腦功能失調、先天性語言能力落后等生理因素有關。而心理學、教育學和語言學的興起,使研究者們開始從心理過程障礙、教育學以及語言學相關角度研究閱讀障礙,跨語言研究也成為一種研究趨勢。
(二)研究主題更加多樣
梳理近年來有關兒童閱讀障礙的研究文獻發現,現有相關閱讀障礙研究方面主要與閱讀障礙者的行為、認知和神經生理方面相關。主要研究內容涵蓋了如何鑒別閱讀障礙兒童在語言技能方面出現了障礙,閱讀障礙存在哪些亞類型,評價不同教學方法對閱讀障礙的有效性,閱讀障礙和其他語言障礙的區別,閱讀障礙兒童的詞典結構及其心理表征,詞匯識別、加工理論模型解釋及模擬閱讀障礙病理現象,閱讀障礙的視聽知覺研究,閱讀障礙是否有遺傳成分,閱讀障礙者大腦結構及其功能研究等。
(三)研究內容更加深入
研究內容從最開始對閱讀障礙發生率的探討,到閱讀障礙患者的行為和神經損傷機制,發展到不同閱讀障礙之間的對比。張承芬(1996)通過數據對閱讀障礙的發生率進行了說明,舒華和孟祥芝(2000)具體研究了閱讀障礙存在的特點和原因,認為困難表現在語音和漢字加工困難等方面。目前,對閱讀障礙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不同語言之間的對比,如Hu(2010)從中英文的語言差異中探討閱讀障礙,韓娟(2012)對兩種語言閱讀障礙發生的同時性和即時性進行了研究,Ting(2017)對右枕顳部病變所引起的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特點進行研究。
三、結語
目前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是對于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診斷和評估缺乏統一標準。目前國內外對于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診斷還沒有形成體系,缺乏統一的診斷標準和有效的評估工具,國內外學者依照自己的理解進行研究,制訂閱讀障礙測試方法與結果評判標準,這就導致研究結果可能產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對于雙語閱讀障礙診斷標準的研究要進一步加強。第二,缺乏對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特異性的研究。從大腦語言加工的整體性以及語言的系統性來看,目前對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特異性等問題還缺乏研究,漢語和英語差異較大,只基于語音層面的研究,可能不足以發現漢英雙語閱讀障礙的特異性。第三,語音層面之外的加工缺陷問題需進一步研究。索緒爾(1980)提出語言符號是音義結合體[20],McBride-Chang 指出(2013)雙語閱讀障礙兒童的語音加工缺陷可能會導致整個語言符號系統的紊亂[21],因此,除語音缺陷外,語義和語法等層面的缺陷,尚需進一步研究,這對于全面深入了解漢英雙語閱讀障礙具有重要意義。第四,提升雙語閱讀障礙兒童閱讀能力的有效手段亟待研究。最近Legault 等(2019)通過對雙語學習者腦機制的研究表明,虛擬現實(VR)等技術對語言學習效率較低的人更有效果[22],同時Vender 等(2019)提出提高閱讀障礙兒童的二語水平,其母語閱讀能力也可能會因此獲益。[23]由此可見,對雙語閱讀障礙的腦機制進行探索,不但是發現和研究兒童語言習得問題的有效途徑,而且還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然而目前應用研究遠遠落后于基礎研究,今后的研究應著眼于實際應用,以加強對雙語閱讀障礙的干預和指導、切實改善雙語閱讀障礙兒童的學習和生活狀況為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