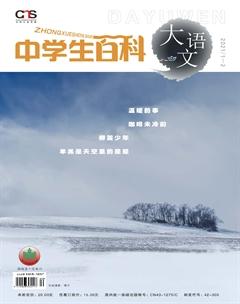牽動心靈的聲音
李璐
有一種人,他們生來不會說話。
當我們傾盡所有去展露我們的鋒芒時,他們思考的只是如何在社會上立足。
生命,真的是平等的嗎?當你用一種近于同情悲憫的眼光望向他們,他們回予你的是一個堅定的聲音——絕對。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到了附近的聾啞學前培訓中心,那里的孩子五六歲,大多先天性聾啞,剩下的小部分康復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第一次走進那里時,孩子們去吃中飯了,大廳靜悄悄的,地上不像其他幼兒園一樣堆滿了玩具,而是彩筆,墻上是一些孩子畫的畫,在陽光下映射出絢麗的色彩。
遠處,一陣風吹過,伴著一陣清脆的鈴鐺響,那聲音很整齊。嗖嗖越過,又消失在更遠的遠方。突然,一個孩子跑來,緊接著是“丁零零”的響聲,驅走了午后慵懶的睡意,雀躍在陽光里。
老師告訴我,孩子們不會發聲,平時很難注意到他們在哪,于是就在他們手上系了一串鈴鐺,聲音不會太大,但總能找到他們。
那孩子看見了我,有些羞澀,一跳藏在老師身后,露出半截用黃皮繩扎著的小辮。小辮隨著女孩的動作一上一下,和著鈴鐺清脆的響聲,可愛極了。
下午,我陪孩子們在后花園玩耍。孩子們不會說話,也沒法發出聲音,整個花園便只有蟬鳴、澆花的水聲和鈴鐺搖動的聲音。午后的蟬很是聒噪,群聚于樹梢發出“吱吱”的聲響,伴著熱烈的陽光,一下低沉,一下高亢,以生命之詩來吟誦未完的秋天,生命的無常在蟬的哀鳴中漸漸鮮亮。
我坐下來,索性閉上眼,假裝自己沒有視覺、嗅覺、觸覺,唯有聽覺,虔誠地追尋那一串串鈴鐺的蹤跡。
我就這樣虔誠地去尋找,拔開風的吟唱、蟬的嘶鳴,聽那鈴聲一會兒遠,一會兒近,一會隨著風散開,一會兒聚攏,發出“叮叮當當”的交錯聲,最后又歸于寂靜。這令我想起了海邊的浪花,美好而熱烈,于潮起潮落間詮釋著大海的遼闊,讓我想起了西藏系鈴而前往高原的信徒,走三步跪一步,涼風高陽,腳步從未停止,信仰從未干涸。
驀地,思緒被陣陣撲鼻的花香打斷。那位辮子扎著黃皮繩的女孩側著臉向我遞來一朵小花。我不清楚它的品種,只記得它的香味很清新。女孩的靦腆,孩子們的笑,即使沒有話語,但陽光足以見證,他們教會了我那么多。
那個下午,鈴鐺的聲音從未斷過,清脆地,熱烈地,活潑地,堅強地,吟誦地,前行著,終于在蟬的最后一陣鳴叫中伴著夕陽隱去,陽光熱烈,風很輕柔。
生命該以一種怎樣的姿態真實而盡力地度過,是我們唯一值得思考的問題。
人都一樣,從不曾有人卑微,從不曾有人生來不幸,孩子們以鈴之聲告訴我,他們不會因寂靜失去對生活的追求,只要路還在,腳步就不會停。
有一種人,生來就不會說話。
點評
本文作者將真摯的情感與純熟的技巧融為一體,成就了一篇令人感動的好文章。開頭以“有一種人,他們生來不會說話”設下懸念,又以“一個堅定的聲音——絕對”奏響了一個強音,然而最精彩的是作者對鈴聲的描寫。作者將鈴聲與蟬聲并寫,以富有頑強生命力的蟬鳴來渲染鈴聲,又以“大海”“信徒”等聯想來強化美好而熱烈之感。最后聾啞小女孩與鈴聲在精神氣質上高度統一,寫聲即寫人,鈴聲成了孩子們對生活執著追求的象征,這讓最后的那一句“有一種人,生來就不會說話”擲地有聲,也呼應了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