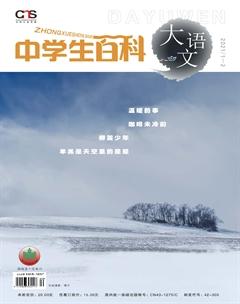美者近之,德者友之
胡嶺
文同,又名文與可,北宋詩人,畫家。其在藝術上所公認的最大成就便是畫竹,這在其表弟蘇軾《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一文中有詳細的記述。其實他在詩文的創作上,同樣成果斐然,只是人們多論其所畫之竹,而忽略了他在文學上的成就。蘇軾就曾經評價他說: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
今天,我們來欣賞他的一首七律《北園梨花》:
寒食北園春已深,梨花滿枝雪圍遍。
清香每向風外得,秀艷應難月中見。
苦嫌桃李共妖冶,多謝松篁相蔥蒨。
黃鸝紫燕莫過從,時有一聲拖白練。
該詩寫于陵州,即現在的四川仁壽縣,北園為他的居處。詩歌開篇先點明時間、地點,仿佛信口說來,毫無作詩的架勢,再一頓,寫出“春已深”三字,漸漸拓開意境。“春深”,意為春意濃郁,其間再加一個“已”字進行強調,讓人感覺雖是居家之處,卻別有一番風景。而這風景之中,尤為引人注目的便是梨花,“梨花滿枝雪圍遍”一句承前而來,“滿”字寫其數量之多,有簇擁洋溢之感,“雪”字則著眼于顏色,以比喻的手法突顯其白,給人以鮮艷亮麗的印象,一“滿”一“雪”,相互作用,感覺是對岑參“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反寫:在基于數量之多的前提下,岑詩以梨花寫雪,而文同則以雪寫梨花,路徑不一致,但同樣形成了本體喻體交相輝映、彼此同一的效果,所彰顯的,則是詩人們在剎那間混同雪花與梨花的訝異與欣喜。緊隨之后的“圍遍”,把視角從梨樹枝頭移向整個北園,從一枝一枝的梨花,寫到一樹一樹的梨花,它們緊密、繁茂,環繞在作者的周圍,充盈在北園之中,使得一園之景,似乎有了漫山遍野的盛大,可謂虛虛實實,但也恰到好處地寫出了春深之時的梨花的特點。
第二聯,作者緊扣“清香”與“秀艷”展開。前面所寫的視覺形象,極為飽滿,再做渲染,便會有重復累贅之嫌。于是,作者跳開一筆,寫其“香”,“香”的特質為“清”,清者,一則純正澄澈,一則清新淡雅,兩者合二為一,往往需要雅士細品靜賞,才能得其真味。句中的“每”字,則表明作者對于梨花之香的傾心品賞,絕非此時此地的品賞,而是一種經常的習慣性的行為。春風所到之處,便是花香散布之處,春風無處不在,北園的梨花之香自然也是無處不在,于是清晨可賞、暮夜可賞,墻內可賞、墻外可賞,忙時可賞、閑時可賞。作者每每品賞梨花清香,不僅表現梨花之香的動人,更是道出了作者的生活狀態和審美品位,可以說是花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如果這一句是以此刻的時間點向后推,寫過往與平時,那么下一句則是將時間點向前推,寫將來的某一個月夜。一個“應”字,有揣測之意,說明這并非作者的所見之景。顏色可看,清香可聞,這還是停留在感官之上,是具體的,而作者的遐思卻早已飛向另一個時空,去領略梨花的另一種神韻——“秀艷”。“秀”,意為美麗而不俗氣,“艷”,則有色彩鮮艷的意思。在梨花之白鮮艷明亮的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將其上升到“美”的高度來加以表現,為此特地為其創造了一個月夜的場景:梨花純白美麗,與同樣純白美麗的月光融為一體,隱約朦朧,難以分辨。文同多有寫月的詩句,如“獨向中庭待明月,一身清露瀉金波”“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一“待”一“候”,足以證明月在他心中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而他在此詩中,又將地上的梨花與天上的月光相提并論,可見梨花之美,是不拘于具體形貌、超脫凡塵的美,是隱約朦朧之中給人以精神享受的美。
第三聯,重新回到園內。園中桃李妖冶,即妖媚而不莊重。古人寫到梨花,常會想到桃花李花,如“粉淡香清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華”(陸游《梨花》),“桃花人面各相紅,不及天然玉作容”(黃庭堅《次韻梨花》),“桃花徒照地,終被笑妖紅”(錢起《梨花》)等。其中,陸詩的“未容”,黃詩的“不及”,錢詩的“終被笑”,或態度鮮明,或對比鮮明,或形象鮮明,各有千秋,而文同用“苦嫌”與“共”兩詞,將這三種意蘊糅合在一起,仿佛讓人看到梨花對妖媚的桃李心生厭惡、避之不及的場景,顯示了梨花潔身自好、清雅自守的美好情操。園中還有松篁,也就是松樹和竹子,它們蔥蘢青翠,讓人心生喜愛。當然,在作者筆下,它們的“蔥蒨”,并不是自顧自的“蔥蒨”,一個“相”字表明,它們在為梨花蔥蘢青翠,它們在和梨花唱和呼應,表面上是綠與白相映襯的色彩之美,深層次卻是梨之純粹、松之堅貞、竹之高節的共同展示。當松篁奉之以綠,梨花亦報之以謝,彼此友好互動中,不覺梨花的純粹中,亦有了堅貞與高節。文同寫梨花,往往引入與之相關的人或物,如“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和梨花》)中用江淹和甄宓之典,寫梨花的姿態與色彩,再如“曉來帶雨四廂下,恰似蓬萊見太真”,則從《長恨歌》中“梨花一枝春帶雨”生發而來,將梨花喻為楊玉環,表現梨花的凄美。但整體上而言,本詩將梨花放入北園這個世俗化的小生態中,通過寫梨花與桃李、松篁之間的關系,營造情境,挖掘梨花的精神品質,其信息量更大,組織形式更為緊湊,思想內涵也更為豐厚。
第四聯,作者進一步豐富北園這個小生態。前一句“黃鸝紫燕莫過從”中“過從”一詞,意為“來訪、來往”。那梨花為什么不和“黃鸝紫燕”來往呢?我們要了解一下“黃鸝紫燕”到底是什么樣的鳥。黃鸝體黃色,自眼部至頭后部黑色,嘴淡紅色,叫的聲音很好聽,常被飼養作籠禽;紫燕,也稱越燕,體形小而多聲,頷下紫色,營巢于門楣之上,分布于江南。可見,這兩種鳥類皆為習慣于依從和攀附的世俗之物,梨花自然將其拒之門外。下一句,有人將“白練”理解為梨花散發出的光輝,其實這是錯誤的。明朝黃一正所著的《事物紺珠》云:“練鵲,尾長而色白者,又一名拖白練。”張華亦云:“帶鳥,練鵲之類是也。今俗呼為拖白練。”對于拖白練,詩文中也多有所見,如宋代王質“拖白練,拖白練,蒼翠陰中玉一片”(《 山友辭·拖白練》)一句,將其喻為蒼翠之中的一片玉,可見色彩之純美,形體之優美。而文同更是在《湖上眾禽盡以俗呼為題·拖白練》一詩中,將其當作知音:“盤石坐深林,不欲人求見。隔岸誰品弦,數聲拖白練。”處深林,避人世,臨水奏曲,拖白練隔岸品賞,不見其形,只聞其聲,有高山流水、知音之賞的妙趣。《北園梨花》一詩,則以“拖白練”結尾,既借其色彩之白,映襯梨花之白,形成視覺的美感,又通過“時有一聲”,在寧靜的氛圍中營造出生機與活力,暗示梨花的生命狀態和精神狀態,更是與前句形成對比,俗與雅,棄與揚,庸俗與高尚,得以生動地顯現,有意境之美,又有意蘊之深,讓無限情懷熔鑄于畫面里,信手結篇。
《北園梨花》一詩,跳脫騰挪,充分借助了與梨花相似之物,寫梨花的顏色神韻,為表,又擇北園或生活中所見的動植物,與梨花形成關聯,側重寫其精神品質,為里,前后表里統一,看似寫梨花,實則寫人,立體豐滿,讓人稱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