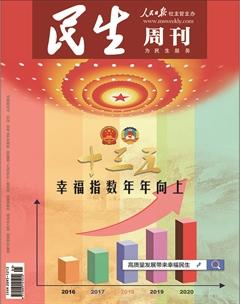全國人大代表王瑞霞:文化真正飛入尋常百姓家
王迪

“博物館是一個城市的靈魂,每到一個地方,我總會先去當地的博物館看看,通過它展示的文物,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談起與文物打交道的30年,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原館長王瑞霞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說,“歷史和文化賦予城市鮮活的生命,使它不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青州市是山東省轄縣級市,1986年由原益都縣撤縣設市,為古“九州”之一,今天的青州市是古青州的核心區,歷史文化遺存極為豐富,2013年青州市被國務院評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作為青州歷史文化展示的主要場所,青州博物館收藏文物之豐富、品類之珍貴,在中國同級博物館中名列前茅。2008年,在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定級評估中,青州博物館成為83家一級博物館中,唯一一家縣級綜合性博物館。
“走進博物館,便是走進青州悠久的歷史,走進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王瑞霞說。
不盲從? 不迎合
“走上文博這條路,對我而言似乎早已注定。”談起鐘愛的文博事業,王瑞霞頗有感觸。
學生時期的王瑞霞,尤其偏愛歷史學科,看到課本里的文物圖片就想追個究竟。“記得上高中時,一家國家級報紙舉辦了一場全國文物名勝知識大賽,為了答題,我甚至逃課去查資料。”每當回憶起那段時光,王瑞霞總是激情滿懷。
高考時,王瑞霞毅然報考了兩所名校的考古系,名落孫山的她,最后被中南民族學院(2002年更名為中南民族大學)歷史系錄取。令她沒想到的是,畢業后,她幸運地被分配到青州博物館工作。至此,王瑞霞終于與夢寐以求的文物打起了交道。
“剛入職時,正趕上博物館清查倉庫,我負責藏品登記。”于是,當時青州博物館所有藏品都經她的手登記了一遍。看到一件件館藏器物精美的造型、流暢的紋飾,王瑞霞禁不住感嘆,古人是用怎樣的心思才能制作出這些傳世杰作。“真的很想去探究它們的奧秘。”回憶起第一次接觸到藏品的感受,王瑞霞稱“除了敬畏,就只剩吃驚了”。
轉眼到了1996年,轟動世界的青州龍興寺遺址窖藏發掘。從發掘到整理、再到修復保護,王瑞霞有幸參與了整個過程,結合自己掌握的書本知識,加上現場專家學者的悉心指導,王瑞霞慢慢對佛教造像有了初步認識。
“在大學三年級時,我無意中買了一本《佛教哲學》,來回翻看幾遍,卻一直看不懂。工作之后看到資料室有《佛學大辭典》,于是借來從頭翻閱,還做了不少筆記。沒想到半年之后就幸運地遇到了這次考古大發現。”王瑞霞說。
而恰在此時,王瑞霞人生迎來一個轉折—去鄉鎮掛職鍛煉。“社會上對我們這類人有個通俗叫法‘無知少女,若從事行政職務類工作,可能會更有發展空間。”可是,對好不容易實現了兒時夢想的王瑞霞來說,文物是她心里難以割舍的痛。
于是,在掛職結束前,王瑞霞向組織部門提出回到博物館工作,而這一干,就是30年。
2002年,國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學舉辦佛教考古研究生進修班,作為山東省唯一一名學員,王瑞霞參加了此次培訓。據悉,這期培訓班被戲稱為“黃埔三期”,雖然學員不多,但絕大多數一直活躍在佛教考古一線。
2019年,當了19年的業務副館長后,王瑞霞被任命為青州博物館館長。
談起從業30年的感悟經驗,王瑞霞說:“對很多基層博物館來說,需要加強研究,找準定位,歸納自己藏品的特色,積極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不盲從,不迎合,只有這樣才能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子。”
博物館不再“高冷”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特別是來自基層一名從事文物工作的代表,王瑞霞深刻感受到,在過去的5年里,我國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
5年時間里,通過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網絡體系基本建立。廣電網絡進萬家工程,使廣電網絡進入到最偏遠的山區;文化大院、農家書屋建設,極大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鄉村博物館、村史陳列室建設,讓人們切切實實感受到了身邊的文化。
“當農民朋友看到農具也可以放在陳列室里展覽時,我相信對他們靈魂的觸動,一定比去參觀大城市的博物館更直接、更深遠。”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王瑞霞看來,這些變化帶給群眾更多的是對文物保護意識的增強,以及對家鄉認知與情感的加深。
5年時間里,各級政府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大大增加。為了讓更多人走進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國家對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繼續推行免費開放,縣級文化館、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扎實推進。
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為保證這一惠民政策落地,各級政府為群眾“買單”。值得一提的是,免費開放補助政策在“十三五”期間惠及非國有博物館。在各級財政緊縮開支情況下,這一惠民舉措無疑是國家對文化重視的有力反映。
“尤其是非國有博物館的設立,在文博領域是一個重大舉措。它的出現以及規范、有序地發展,補充了國有博物館服務能力的不足,也讓更多收藏在民間、有價值的藏品得以面世,直接推動了歷史文化的研究和繁榮發展。”王瑞霞說。
“十三五”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確立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制度,這意味著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取得重要突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日益完善,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國民素質整體提高,城鄉文化實現了大繁榮、大發展。
“晉級難”終被打破
當前,我國文物事業的發展進入重要歷史機遇期,文物數量大幅度增長,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全國共調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76.7萬處;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之后,全國國有可移動文物共計10815萬件/套。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核定公布后,我國國保單位總量達到5058處,全國博物館達5354家。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項,與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
王瑞霞此前調研發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但在人才隊伍建設、文化活動經費保障等“軟件”方面的配套投入仍嫌不足。基層文化干部的社會地位、收入待遇相對偏低,加上個人成長空間有限,從而降低從業人員的職業存在感。
“就博物館而言,全國縣級博物館多數只有十幾個編制,有些甚至只有幾個。很多博物館幾年下來,工作人員沒增加幾個,工作量卻不知增加了多少倍,面對公眾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不少基層一線文博工作者只能疲于應對。”王瑞霞坦言。
近年來,國家對公共文化人才的培養和使用越來越重視,尤其“十三五”時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規定。例如,對一些非遺傳承人實行生活補貼,為他們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提供更好的環境;再比如,長期困擾基層專業技術人員評職稱難,特別是基層不設正高,即使設正高,到退休也停留在正高四級等問題,王瑞霞在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議案,當年,人社部專門針對文博部門出臺了有關職稱設置的指導意見。“晉級難”這一難題終于被打破。
國家對文博事業的重視,無疑給無數奮戰在文博事業一線的“王瑞霞們”打了一針強心劑。“政策的陸續出臺,讓更多文博工作者安心扎根基層,長期服務基層,為基層文博事業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實現自身價值。”王瑞霞說。
就在前不久,王瑞霞剛剛卸任館長職務,目前是青州博物館研究員。回顧與文物結緣的30年,王瑞霞感慨,“我是幸運的,幸運地從事了自己喜歡的工作,幸運地遇到了龍興寺遺址佛教造像的出土,幸運地參加了北大培訓班,幸運地見證了我國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
對此,王瑞霞常常感嘆,自己何德何能,遇到了這么多幸運的事。“唯有誠實做人,踏實做事,以回報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