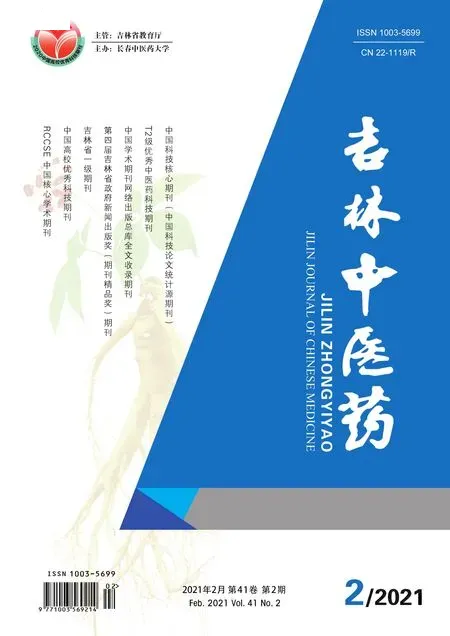出血性中風中醫證候要素分布規律研究
張琳婷,張根明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 100700)
出血性中風是臨床常見的腦血管病,具有起病急、變化快[1]。中醫辨證論治在出血性中風的治療中起著重要作用。研究出血性中風證候要素分布特點及演變規律,可以進一步認識出血性中風的病因病機,探求證候的本質,對于提高辨證論治水平及指導臨床治療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研究病例來源于“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臨床研究基地業務建設科研專項——出血性中風證候要素診斷量表編制研究”,2016 年6 月-2019 年1 月于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太原市中醫院、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門診及住院收治的腦出血患者494 例。其中男性298 例,女性196 例;年齡最大93 歲,最小25 歲,平均年齡(60.46±12.87)歲。其中合并吸煙者207 例,合并飲酒者213 例,高血壓病393例,冠心病65例,糖尿病108例,高脂血癥72例。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采用《中國腦出血診治指南(2014)》[2]腦出血診斷標準:1)急性起病;2)局灶神經功能缺損癥狀(少數為全面神經功能缺損),常伴有頭痛、嘔吐、血壓升高及不同程度意識障礙;3)頭顱CT 或MRI 顯示出血灶;4)排除非血管性腦部病因。
1.2.2 中醫診斷標準 采用1995 年中國中醫學會內科學會腦病專業委員會提出的《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1]。1)主癥:偏癱、神識昏蒙、言語蹇澀或不語、偏身感覺異常、口舌歪斜;2)次癥:頭痛、眩暈、瞳神變化、飲水發嗆、目偏不瞬、共濟失調;3)急性起病,發病前多有誘因,常有先兆癥狀;4)發病年齡多在40 歲以上。具備2 個主癥以上,或1 個主癥2 個次癥,結合起病、誘因、先兆癥狀、年齡即可確診;不具備上述條件,結合影像學檢查結果亦可確診。
1.2.3 證候診斷標準 參照《中風病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根據專家意見,將“陰虛陽亢”拆分為“陰虛”和“陽亢”,從而形成風、火、痰、血瘀、氣虛、陰虛、陽亢7 個基本證候要素;整理2000 年之后有關出血性中風的證候學相關研究,整理其中提到的證候要素出現頻率,進行排序,將出現頻率大于10%以上的證候要素作為研究備選證候要素,增加濕、氣滯、陽虛3 個證候要素,最終組成10 個出血性中風最常見的證候要素。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腦出血診斷標準的患者;2)發病在90 d 以內;3)年齡>18 歲;4)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排除標準:1)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外傷引起的腦出血患者;2)梗塞后出血患者;3)合并其他器官的嚴重疾病;4)精神障礙或嚴重癡呆。
1.4 研究方法 將患者一般信息(性別、年齡、發病時間等)、出血性中風臨床常見的四診信息(包括癥狀、舌、脈)、證候要素信息等編制成統一的調查表。選擇有臨床經驗的中醫神經內科醫師,按統一要求填寫調查表格,記錄患者四診信息,同時由固定的三位臨床醫師背對背做出證候要素是否存在的判斷,每位患者允許同時存在多個證候要素。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EpiData 3.1數據庫錄入數據,采用SPSS 20.0 進行統計分析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以頻數(%)表示,采用χ2檢驗,2 組比較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 組比較以P<0.167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證候要素分布
2.1.1 單證候要素 494 例腦出血患者中,共有證候要素1615 例次,見表1。

表1 單證候要素分布 例(%)
2.1.2 雙證候要素組合 見表2。

表2 雙證候要素組合(前十) 例(%)
2.1.3 三證候要素組合 見表3。

表3 三證候要素組合(前十) 例(%)
2.2 證候要素分布與腦出血天數 見表4。
2.3 證候要素分布與性別 見表5。
2.4 證候要素分布與吸煙、飲酒 見表6。

表4 證候要素分布與腦出血天數 例(%)

表5 證候要素分布與性別 例(%)

表6 證候要素分布與吸煙 例(%)
2.5 證候要素分布與飲酒 見表7。
3 討論
出血性中風是指自發性腦實質出血,位居腦血管病第二位,僅次于缺血性中風。自《內經》開始就有關于中風的論述,但歷代中醫典籍均未區分出血性中風和缺血性中風,直至近代張錫純才將之分為腦充血證和腦貧血證。出血性中風證候特點與缺血性中風并不完全相同,既往中風的證候分布及演變的研究多未對兩者進行區分[3-6]或是僅研究缺血性中風[7-14],對于出血性中風的證候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試圖彌補這方面研究的不足,探求出血性中風的證候分布及演變特點,以更好地指導臨床辨證治療出血性中風。

表7 證候要素分布與飲酒 例(%)
本研究表明,單個證候要素最常見為痰,其次為血瘀、風、火,氣滯出現最少;兩個證候要素組合最多的為痰瘀,其次為痰熱、風痰;三個證候要素組合最多的為風、痰、瘀,其次為火、痰、瘀。痰、瘀、風、火是出血性中風最為突出的證候要素。在出血性中風的第0~1 天、第2~14 天、第14~90 天3 個時期痰、瘀都位居前兩位。這一證候分布和演變規律提示痰瘀在出血性中風疾病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貫穿于中風病的始終,這與楊利等[15]的研究基本一致。
出血性中風雖起病急驟,但發病之前已有痰瘀漸積而成。《丹溪心法·中風》有云“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出血性中風常見于中老年人,多年老體虛,臟腑功能衰退,脾胃虛弱,脾失健運,則水濕不化聚而為痰;或過食膏粱厚味,脾失健運,氣不化津,反聚濕生痰。年老體虛,臟腑功能衰退,氣血失和,或氣虛無力行血,血行不暢,則生瘀血。或勞逸失度,過勞氣衰,過逸氣滯,氣衰氣滯皆致津血不行,留而為瘀。《血證論》有云“離經之血,雖清血、鮮血,亦是瘀血”。津血同源,《靈樞·癰疽篇》有云“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瘀亦可致痰水形成。出血性中風絡破血溢[16],瘀停脈外,脈道不通,致使血脈內外津液不能滲出或還于脈中,循環受阻,津聚為水,水聚成痰。離經之血停于腦竅,久而不去可轉化為痰水,即唐容川《血證論》所言“血積既久,亦能化為痰水”。現代研究亦表明痰瘀在中風病的進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痰瘀既是中風產生的病理基礎,亦是中風的病理產物。宋劍南[17]研究認為痰濁是機體是物質代謝過程失控生成并過量積累的各種病理性產物,如膽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等,瘀則與血液黏度、血管內皮通透性及內皮舒張因子等變化密切相關,推測脂質過氧化作用可能是中醫“痰瘀相關”的中心環節,LDL-C 的過氧化物LPO 可能是物質基礎,內皮細胞損傷是由痰致瘀的主要病理特征,脂質代謝率亂及引起脂質代謝紊亂的內外因素是痰瘀共同為病的病因所在。痰瘀與高脂血癥、動脈粥樣硬化密切相關,而高脂血癥、動脈粥樣硬化是中風病的重要危險因素。張令霖等[18]研究認為中風病痰瘀的生物學機制主要歸納為脂質代謝紊亂、炎癥反應、血液流變學改變、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微循環障礙、氧自由基、細胞間黏附分子等方面。
本研究表明吸煙、飲酒患者更易出現火證和痰證。吸煙、飲酒為腦血管病的常見危險因素。清代顧松園《顧氏醫鏡》云:“煙為辛熱之魁,酒為濕熱之最。”煙草辛溫微熱,主升屬陽,易助陽耗陰;酒性濕熱,偏嗜飲酒,易傷脾胃,助濕生痰;痰熱內盛,進而生風,風陽夾痰熱而橫竄經絡,導致中風的發生。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更易出現火證、氣虛證,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男女生理基礎有所差別,中醫體質亦不相同,導致出血性中風的證候分布、演變不同;另一方面,男性患者吸煙、飲酒的比例更高,也會對中醫證候產生影響。
由于客觀因素制約,本研究病例以急性期為主,恢復期和后遺癥期較少,研究結果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倚,病情進展至恢復期及后遺癥期虛證(如氣虛、陽虛等)所占比重未見明顯升高,與傳統中醫認識的中風后期以正氣虛損為主有所差異;研究病例限于北京、吉林長春、山西太原三個地區,研究結果可能受地域影響。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正常接受中西醫結合的治療,可能對證候要素的演變產生一定的影響。今后需擴大樣本量,涵蓋更為廣泛的地域,克服本研究的局限與不足,獲得更為可靠的臨床資料,以更好地反應出血性中風的證候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