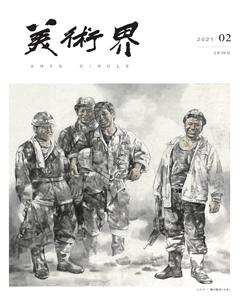從德拉克洛瓦看法國浪漫主義人物造型“丑”的特征
梁恒浩
【摘要】德拉克洛瓦是法國浪漫主義繪畫的領袖,是19世紀法國浪漫派畫家最重要的代表。本文從德拉克洛瓦的作品出發,研究法國浪漫主義人物造型“丑”的藝術特征,并歸結德拉克洛瓦“丑”的人物造型來源為一種漫畫形式感。在適當分析法國諷刺漫畫與德拉克洛瓦作品的聯系過程中,例證漫畫形式感是造成德拉克洛瓦浪漫主義人物造型“丑”的根源。
【關鍵詞】浪漫主義;德拉克洛瓦;漫畫;人物造型;丑
法國19世紀上半葉,漫畫人物造型的審美早已有所定論,當時的批評家波德萊爾(Baudelaire)曾言:“這些圖樣可以被表現得美,也可以被表現得丑。表現得丑,就成為漫畫,表現得美,則成了古典雕像。”①當時法國人認為漫畫形式的人物造型是丑的,它是相對于“古典”藝術而言,即相對于“美”的藝術而言。“美”與“丑”在藝術作品表現中常常需要相互比較,相輔相成。法國浪漫主義繪畫人物造型中的“丑”,并不是生活中真正意義上的丑,它作為藝術審美特征同樣是美學的研究范疇。法國浪漫主義繪畫在人物造型“丑”的贊美與表達中,對近現代中西方藝術美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德拉克洛瓦十分喜歡法國漫畫,其在1838年繪制扇面形式作品《漫畫迷》就體現浪漫派畫家對漫畫形式感的偏好。早期德拉克洛瓦在1821年畫了一張意大利劇院題材的人物造型插圖(圖1)就很有漫畫的形式感,畫家當時匿名將它發表在法國《Le Miroir》報紙上,畫面上描繪邁開雙腿的人物是同時代意大利歌劇作曲家羅西尼(Rossini),羅西尼被德拉克洛瓦描繪成一名中產階級的打扮,褲腰袋裝滿了法國公眾對他三件歌劇作品的得分,以此諷刺羅西尼的歌劇在法國上映迎合新古典主義人士審美而得到熱捧和好評。這張匿名作品公開發表后讓法國人耳目一新,浪漫派畫家用《意大利歌劇》人物造型反映古典主義美學在法國劇場的表演,通過怪誕的、戲謔的、漫畫式的人物造型來表達對古典主義美學地抗議,初具浪漫主義色彩。
而羅西尼頭頂上的三個小人物則是羅西尼的三件歌劇作品中的主角,從左到右分別為:摩洛哥衣著打扮的奧賽羅(Othello)、中間的是羅西娜(Rosina)、右邊的是費加羅(Fiaro)。畫面中的人物造型十分具有諷刺意味,其中羅西尼左手舉著的費加羅被描繪成尖銳、巨大的鼻子,頭身比例夸張化,實則是采用了漫畫形式感中夸張諷刺的手法,這一手法在法國諷刺漫畫家杜米埃(HonoréDaumier)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對此我們可以參考杜米埃發表的諷刺漫畫,如這一張諷刺當時某位歌唱者的漫畫《M.G表演的歡樂歌曲》(圖2),其人物造型特點與德拉克洛瓦描繪《意大利歌劇》的手法幾乎是一致的。
浪漫派畫家在諷刺社會丑聞的人物造型中,故意把人物畫丑,而這樣“丑”的特征和當時法國19世紀上半葉黑暗的資產階級政權相關,浪漫派藝術家密切關注到人內心的真善美。大多數法國浪漫派人士并不像古典主義畫家只喜愛在藝術作品中表現人物的美貌,雖然他們崇拜詩人拜倫英俊的長相,喜歡浪漫小說中俊美的男女主人公——或許因為美的外表而沉迷故事人物,這些確實反映出浪漫派畫家對外表的浪漫主義氣質有一定的追求。但是,他們并不討厭長相十分丑的人,而是討厭內心十分丑的人。在他們的文學與藝術作品中,法國浪漫派藝術家幾乎一致地表現出人的內心比美貌更為重要的觀點。其一,如果要運用諷刺漫畫的形式感,則必然造成人物造型的夸張變形和丑化的藝術效果,以突出諷刺的目的;其二,漫畫形式感本身就具備較為自由地表現手法,相比古典技法的嚴格約束,漫畫的輕松與詼諧的特點也得到了浪漫派畫家的贊美。
比如德拉克洛瓦在1826年畫的《拉美莫爾的新娘》(圖3)出自司各特(Scott)的小說,畫面所描繪的故事的主角露琪亞與埃德加作為一對幸福的戀人,卻在故事的轉折中露琪亞不得不嫁給巴克洛,而結婚的那一天露琪亞得知有關埃德加的真相,就是他自殺身亡的場景。雖然德拉克洛瓦把故事主角丑化,但我們有理由認為畫家并無以上諷刺漫畫的目的。畫面中,拉美莫爾的新娘被描繪成十分“丑”的模樣,看似是浪漫派畫家通過“丑”的外表來贊美露琪亞內心對愛情的堅守,實則是贊美了司各特的小說《拉美莫爾的新娘》悲劇與傷感的愛情故事,同時也表達了德拉克洛瓦對女主角愛情悲劇的同情。
另外,浪漫主義人物造型長相丑陋也有依據可循。比如這張露琪亞人物造型的形式感不像畫家1827年畫的《薩達納帕勒斯之死》或《但丁之舟》受到魯本斯等人影響。《拉美莫爾的新娘》人物造型的表現既不魯本斯式,也不是米開朗基羅式。西方在古典造型藝術繼承發展漫長的過程中,出現了影響力極大的藝術家,不僅這些著名西方畫家在繪畫人物造型上被世界熟識,而且有強烈的并屬于他個人的造型語言特點。目前國內外在研究人物造型中為便于區分畫家與畫家之間學習與效仿的關系,我們一般把文藝復興時期以結構解剖的“肌肉美”人物造型稱之為“米開朗基羅式”或“米氏”,體型流暢的“秀美”人物造型稱之為“拉斐爾式”,巴洛克時期“肥美”的人物造型稱之為“魯本斯式”等。《拉美莫爾的新娘》實則采用的是法國漫畫形式,戲謔、簡約、平面,這都是漫畫人物造型的特點。畫家曾說“看到了兩冊英國的《笨拙》畫報。到巴黎時,一定得買一份,它上面有些漫畫畫得確實是不壞。”②除此之外,畫家繼續表達出對漫畫的看法:“有一次畫漫畫,我也有過和這同樣的經驗,我畫出的輪廓幾乎像是兒童畫,沒有運用一點立體塑型的方法。”③可見法國漫畫對德拉克洛瓦畫中的人物造型手法有著直接影響。
對此當時法國漫畫是什么樣的人物造型?法國漫畫普遍表現出繪畫感與線條的抒寫性,不強調光影和體積感,而且人物的五官不是客觀寫實的,有夸張的效果。關于夸張的人物造型手法,德拉克洛瓦認為“就像米開朗基羅、蒲熱和柯雷喬這些人所慣用的夸張或者不準確的表現手法,在古人是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所有,古人與之無緣”④。德拉克洛瓦認為文藝復興之前的古典主義人物造型不具備夸張效果,文藝復興之前古典繪畫也就無法與夸張漫畫形式相聯系,同時德拉克洛瓦把漫畫中的夸張手法也稱作“不準確的表現手法”,這就證明浪漫派畫家所描繪“不準確”的人物造型,多數是以漫畫中的夸張手法故意而為之。在德拉克洛瓦《拉美莫爾新娘》中的人物面部特征中,畫家采用與漫畫一致的表現手法,強調故事情節發展與自我的主觀感受,從而忽略人物造型原本的模樣。主角露琪亞的頭部、五官,甚至身體的表現都是“不準確”的。這一特色在白璧德(Irving Babbitt)看來,“只有當一件東西是奇異的、出乎意料的、強烈的、夸張的、極端的、獨特的時候,它才是浪漫的”⑤。顯然,德拉克洛瓦充分運用了漫畫人物的形式特點這一媒介。
如何理解法國浪漫主義人物造型中的“丑”,首先就得先理解法國浪漫派畫家對漫畫手法的認識。德拉克洛瓦說:“特別是對于遠處的人物,就應當像我們在漫畫中所采用的平涂畫法:也就是說,只用暗影去表現出形狀,而不表明光線。”⑥從中可見,漫畫中的平涂、摒棄光影的立體感是浪漫派畫家所倡導的。即德拉克洛瓦對于“丑”的人物塑造歸于法國漫畫的形式感,這種形式感帶有顯著的“丑”的特征,是漫畫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特點。
“美總是不可避免地由兩個要素構成”⑦,其一是代表永恒、普遍而通俗的美感;其二是時代的、激情的、變化的。這是波德萊爾對美的理解,他在代表作《惡之花》中寫道:“有匹野獸,更丑、更悍、更是臟兮兮的!”⑧似乎指向德拉克洛瓦——畫家不僅有“浪漫主義的雄獅”之稱,而且畫過大量的野獸習作。德拉克洛瓦在《美的多樣性》開頭就引用了拉封丹(La Fontaine)《烏利斯的旅伴》中的詩句:“熊叫著回答烏利斯:‘嘿!就為這么一件事嗎(我不美)?相貌和我有什么關系?熊就是熊相,就要這么個傻樣,為的是證明,比美更重要的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外貌”⑨。從中就證明法國浪漫派藝術家對審美有自己執著地追求,浪漫派畫家的美學觀也因此在18、19世紀聯合哲學家的討論中有了較為科學的體系。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德拉克洛瓦作品中的人物造型“丑”的特征和法國漫畫的形式有直接聯系。因此法國浪漫主義繪畫人物的“丑”不是憑空創造出一種新的繪畫形式,而是在法國經常出現漫畫形式插圖的書籍、報紙等閱讀媒介上,挖掘漫畫形式感的人物造型特點,找到漫畫形式特點中的戲謔、平面、簡約、失去光影與體積的繪畫方法,并重視線條的勾勒與抒寫,這與西方傳統繪畫、古典主義繪畫的造型方法就截然不同。因此德拉克洛瓦的人物造型手法不僅僅是發泄情感地涂抹和對細節刻畫沒有表現出關注,而是糅合了當時法國漫畫的形式感,并且對浪漫主義繪畫造型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且,漫畫形式不僅是插畫用途,它在法國當時更多被用來諷刺政治丑聞、社會丑聞,和法國浪漫主義人物造型的產生目的相關聯。不論如何,研究法國浪漫主義人物造型不能脫離漫畫,因為這是造成19世紀上半葉法國浪漫主義人物造型“丑”的主要原因。
注釋:
①[法]夏爾·波德萊:《現代生活的畫家》,胡曉凱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4,第2頁。②[法]德拉克洛瓦:《德拉克洛瓦日記》,李嘉熙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第297頁。
③同上,第174頁。
④同上,第496頁。
⑤[美]歐文·白璧德:《盧梭與浪漫主義》,孫誼學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頁。
⑥[法]德拉克洛瓦:《德拉克洛瓦日記》,李嘉熙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第173頁。
⑦[法]夏爾·波德萊:《現代生活的畫家》,胡曉凱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4,第3頁。
⑧[法]夏爾·波德萊:《惡之花》,孤振豐譯,三聯書店,2019,第40頁。
⑨[法]德拉克洛瓦:《德拉克洛瓦論美術和美術家》,平野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