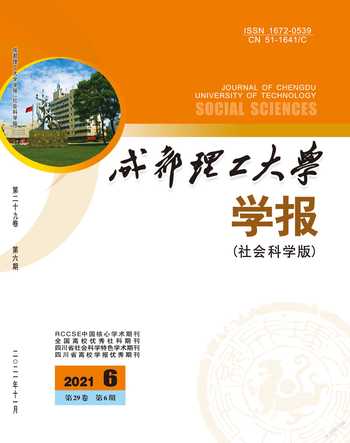平臺中立視角下優待自營業務的法律規制
吳楷文 栗明
摘 要:為了實現縱向一體化的目標,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有天然動機運用“私權力”和數據優勢優待自營業務并為其提供競爭優勢。同時,優待行為也給平臺內經營者、平臺內市場的競爭機制和消費者帶來現實損害。因此有必要引入平臺中立理論要求平臺經營者恪守中立原則,并且網絡中立理論及我國競爭法的立法目標也為平臺中立義務提供了正當性。為了實現實然與應然的平衡,必須對平臺經營者完全中立義務有所克減,進而實現其部分中立義務。
關鍵詞:平臺中立;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自營業務;優待行為
中圖分類號: D922.29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21)06-0015-08
一、問題的提出
在平臺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電子商務平臺的商業模式也愈發多樣化。有些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下稱“平臺經營者”)不再局限于提供作為“中間人”的平臺業務,而是選擇進入平臺內市場,通過自營業務擴展盈利渠道并與平臺內經營者形成競爭。在我國,京東、當當網和蘇寧易購等大型電子商務平臺均為自營業務的實踐者,而且上述平臺內均存在自營業務和平臺內經營業務。
不過,自營業務在繁榮市場的同時也存在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的風險。這是因為平臺業務與自營業務同為平臺經營者的業務構成,為了獲得更多利潤,平臺經營者勢必會優待自營業務,讓其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競爭時占據優勢。此時,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極易導致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失衡,這也引起了歐美反壟斷部門的關注。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維斯塔格在聲明中認定亞馬遜違反了歐盟反壟斷規則,理由是亞馬遜將第三方賣家數據反映在其算法中,再通過算法優化其自營業務的價格與管理[1]。此外,在美國眾議院2020年10月發布的報告中,亞馬遜被指控通過控制關鍵資源、訪問競爭賣家的數據等方式使自己的第一方商品(自營業務)獲得競爭優勢[2]。
相較于歐美,我國反壟斷執法部門未曾關注過平臺經營者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自營業務的處理也僅限于確定民事責任,與競爭秩序無關。受2017年“京東自營案”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立法的影響,學界的討論集中于自營業務的法律地位及民事責任的問題。此外,《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七條作為現行法中唯一直接涉及自營業務的法律規范,也僅從正面規定了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應當顯著區分及平臺經營者應當對自營業務承擔民事責任。
隨著對于平臺經濟反競爭威脅認識的不斷加深,我國開始扎緊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籬笆,將科學有效監管作為平臺經濟領域開展反壟斷的一項基本原則,而非任由平臺企業“野蠻生長”。在宏觀層面,202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作為次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直指平臺企業的反壟斷問題[3]。在微觀層面,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下稱“《平臺指南》”)的公布同樣為規制平臺經營者的自我優待行為提供了契機和參考。為此,筆者希望在明確優待自營業務行為產生的反競爭問題根源及規制必要性的基礎上,運用平臺中立理論為該行為的法律規制提供有益思考。
二、縱向一體化與競爭優勢:優待自營業務反競爭問題的根源
(一)自營業務的外延識別
根據學者的定義,電子商務平臺的自營業務是指平臺經營者在自己經營的電子商務平臺上開展自己經營的業務[4]。正確理解自營業務概念的關鍵是明晰定義中的兩個“自己經營”,其中第一個“自己經營”是前提,第二個則是表現形式。首先,自營業務必須是平臺經營者在“自己經營”的電子商務平臺內從事的業務,換句話說,平臺經營者在其他平臺內從事經營活動時只能被視為平臺內經營者,最典型的就是蘇寧易購的天貓旗艦店。其次,自營業務的表現形式為“自己經營”,也就是平臺經營者自己直接向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這使得自營業務區別于僅提供中介服務的平臺業務。
平臺經營者本不參與平臺內的交易,但是在從事自營業務時,他不應仍被視為提供平臺服務的第三方。平臺經營者通過自營業務直接向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在法律關系上與消費者構成買賣合同或服務合同關系,在法律地位上也與平臺內經營者無本質差別。在責任承擔方面,根據《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平臺經營者應當對標記為自營的業務承擔商品銷售者或者服務提供者的民事責任。
此外,還需將平臺實踐中出現的“商家自營”與本文所述的自營業務加以區分。商家自營或品牌自營店是指商家在電子商務平臺內自行經營,而非通過代理渠道經營,類似于“直營”[5]。在商家自營的場景下,經營主體并非平臺經營者,而是產品或服務的原始商家。與平臺自營類似,商家自營同樣可以基于自身商業信譽給消費者帶來更多信賴保證,但其在性質上仍為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
(二)自營業務的定位:縱向一體化
《電子商務法》第九條圈定了平臺經營者的基本業務范圍,即為買賣雙方的獨立交易提供網絡經營場所、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而不包括自營業務。根據波斯納的定義,縱向一體化就是企業把本來可以承包出去的經濟職能在內部執行[6]。因此平臺經營者在提供平臺服務之外把原本可以承包給平臺內經營者的經濟職能由自己通過自營業務執行,其實就是一種縱向一體化。
由于平臺企業與傳統線性企業在經營策略、發展動力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在電子商務平臺的語境下,平臺經營者通過自營業務實施縱向一體化的理由也具有特殊性。在平臺成長初期,自營業務的主要任務是解決“雞蛋相生”的問題,即平臺內經營者不足而無法吸引消費者的問題。借助平臺的信譽和背書,平臺經營者可以憑借優質的自營業務吸引消費者,再通過消費者數量的增加尋求更多平臺內經營者入駐,以求在網絡效應的作用下實現快速發展。
平臺發展成熟后,平臺經營者可以通過自營業務獲取平臺內市場的利益,而且其基礎平臺業務也為自營業務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這是因為平臺經營者不僅擁有自營業務成長所需的商業資源,更是整個平臺架構的擁有者和管理者。縱向一體化與優待行為本身就是一體兩面,或者說,縱向一體化的目標本身就包含了優待縱向業務以節約交易成本。自營業務本就是平臺整體業務的一部分,平臺經營者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勢必會優待自營業務,讓自營業務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并成為平臺業務日趨飽和時新的增長點。
(三)自營業務競爭優勢的來源
1.平臺經營者的“私權力”
基于平臺服務合同和交易規則,平臺經營者一方面負有為平臺內經營者提供優質平臺服務的義務,另一方面則享有管理平臺內經營者的權利。而且,為了保證平臺內經營活動的有序進行、減少負網絡外部性對平臺內市場的不利影響,平臺經營者必須建構一系列機制以實現對平臺內經營者的有效管理。不過,平臺經營者同樣可以假借管理之名為自營業務提供不公平競爭的優勢。
在平臺成長初期面對平臺經營者實施的不合理管理行為時,平臺內經營者可以依據服務協議毫無顧慮地退出平臺。隨著平臺的不斷擴張,或許平臺內經營者仍可以一走了之,這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礙,但是退出對他來說意味著放棄一個龐大的市場。此時,平臺內經營者就需要在權衡利弊后再做出選擇。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平臺經營者與平臺內經營者仍為名義上的平等主體,但事實上平臺經營者卻不同于傳統市場經營者,他扮演著市場規制者的角色,具有履行管理平臺的“私權力”[7]。
憑借“私權力”帶來的事實上的支配力,平臺經營者可以單方面影響平臺內經營者的經營活動和商業行為,甚至可以決定平臺內經營者的去留。為了使自營業務獲得更多流量和關注度,平臺經營者可以通過算法直接讓其獲得首頁推薦的機會或更高的搜索排名。此外,平臺經營者還可以干擾平臺內經營者的正常經營活動,甚至可以違反平臺規則為名直接封停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
2.平臺的整體數據優勢
在當今社會,數據已經同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成了一種新型生產要素。不過,單個或零星的數據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通過大數據手段對原始數據進行大量搜集、整理和運用,才能發揮其商業價值。在數字經濟時代,不管是對于平臺經營者抑或是平臺內經營者來說,更多數據意味著更大的競爭優勢。因此平臺經營者需要借助自營業務等方式拓寬數據收集渠道,與此同時,自營業務更是平臺整體數據收集的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自營業務是原始數據的收集者。電子商務平臺的基礎架構地位意味著平臺經營者可以在自己收集數據的同時獲取平臺內經營者的部分數據,但這并不等于他的數據需求已經飽和。因為與直面消費者的平臺內經營相比,平臺經營者在原始數據收集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劣勢。因此,平臺經營者通過自營業務與消費者直接發生交易不失為一個穩定的數據補充來源,這不僅能夠幫助他更好地做出決策,也為自營業務的數據優勢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自營業務更是平臺整體數據的使用者與受益者。雖然平臺內經營者在原始數據收集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但從總量上來說,他仍然無法與平臺經營者相提并論。作為平臺業務的縱向延伸,自營業務可以享有海量的平臺數據資源,并利用這些資源進行自我優化與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平臺經營者還可以通過深度分析平臺內經營者的交易數據甚至非公開數據的方式優化自營業務,讓其在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競爭中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三、優待自營業務的規制必要性
(一)縱向一體化的傳統理論與電子商務平臺的特殊性
縱向一體化屬于企業為了減少交易成本做出的正常商業選擇,本身不具有可罰性。但是如果一個實施縱向一體化的企業自己就是壟斷者,那么該行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卻值得反壟斷法及其理論的關注,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杠桿理論。杠桿理論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司法實踐中,該理論認為,企業通過縱向一體化可以憑借杠桿力量將自己在一個市場上的壟斷力傳導至另一個市場,從而在相鄰市場同樣也獲得壟斷力。甚至在有的學者看來,縱向一體化與企業原本的橫向壟斷力相結合,可以比在單一市場壟斷更嚴重地削弱競爭[8]。
隨著芝加哥學派的興起,杠桿理論被逐漸拋棄。芝加哥學派將價格理論作為反壟斷法的分析核心,他們認為企業從事縱向一體化只不過是為了利潤最大化將交易成本內化為企業的組織成本,而非想要在另一環節獲得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在該學派看來,企業沒有必要將壟斷力傳導至另一環節,因為在銷售鏈的某一環節擁有壟斷地位的企業,一般可以將整個鏈條上的全部壟斷利潤占為己有[9]。相較于更關注競爭過程與市場結構的杠桿理論,芝加哥學派將效率視為反托拉斯違法的唯一標準,而且縱向一體化在他們看來通常是有效率的、符合消費者福利的。正是在這種學說的影響下,美國法院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步放棄杠桿理論,并放寬了對縱向一體化的審查。
芝加哥學派認為縱向一體化通常是有效率且促進競爭的,但是電子商務平臺卻不同于傳統線性企業,它是一個典型的雙邊市場,且以提供平臺服務而非銷售商品為盈利來源。此外,在平臺產業中并不存在一個完整、清晰的銷售鏈條,而且平臺經營者擁有并掌管著平臺的基礎架構及平臺內的諸多生產要素,這也使得優待行為的反競爭風險更難評估。因此,若要規制平臺經營者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就必須首先明確其規制必要性。
(二)優待自營業務的現實損害
對于平臺經營者來說,自營業務是其整體業務的一部分,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平臺經營者有天然動機運用自己的“私權力”和數據優勢實施自我優待。然而,平臺經營者在優待自營業務并為其帶來競爭優勢的同時卻給平臺內經營者、平臺內市場的競爭機制和消費者帶來了嚴重的現實損害,下面分述之。
1.損害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
在市場經濟中,有競爭就有損害,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也就意味著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的競爭劣勢。平臺經營者的優待行為在給自營業務提供競爭優勢的同時,更會損害平臺內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利益。借助平臺的“私權力”,自營業務可以毫不費力地獲得更多流量與首頁推薦的機會,并在消費者搜索商品時位于前列,與此同時,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若想獲得同等機會則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此外,平臺“私權力”不僅可以為自營業務帶來競爭優勢,還可以降低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的競爭力。比如,平臺經營者可以通過搜索降權、流量限制等手段限制平臺內經營者的正常經營活動,抑或是以違反平臺管理規定之名直接暫停或封停對自營業務產生競爭威脅的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讓其從根本上無法與自營業務開展正常競爭。
基于平臺的整體數據優勢,自營業務同樣也可以獲得極大的競爭優勢,尤其在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內經營者的非公開數據優化自營業務的情況下。這些非公開數據不僅可以為自營業務提供經營思路或彌補經營短板,平臺經營者甚至還可以利用這些數據仿制平臺內經營者的產品并最終將原產品趕出市場。然而,此種行為會造成單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并侵犯平臺內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這些非公開數據能夠被認定為商業秘密,那么平臺經營者的此種行為同時有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風險。
2.加劇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失衡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公平是市場經濟的靈魂[10]。競爭可以提升市場活力、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但前提是存在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在平臺內市場的競爭中,自營業務具有平臺內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然而,該競爭優勢的取得并不一定源于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及質量,而可能是平臺經營者基于自身“私權力”及數據優勢實施的優待行為。不管是在流量分配還是數據使用上的差距,都很難使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與自營業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也就是說,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極易導致平臺內市場競爭的失衡。
不僅如此,競爭機制亦無法在平臺內市場中充分發揮作用。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有賴于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不過在電子商務平臺的語境下,平臺經營者作為市場規制者卻可以使用手中的“私權力”人為干預市場競爭。不同于以維護市場競爭活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為己任的政府干預,平臺經營者對平臺內市場競爭的干預有天然的逐利性、偏向性和優待自營業務的動機。在利益的驅使下,該干預行為的目標并不是矯正平臺內的市場失靈和競爭失范、讓市場回到有效競爭的完滿狀態而是為自營業務提供更多競爭優勢。這種情況下,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只會進一步失衡。
3.間接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使得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無法與其公平競爭,進而導致市場機制的失靈,這一切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雖然自營業務在短期內看似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但隨著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失衡,消費者根本無法從中受益。由于存在單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平臺內經營者沒有動機通過降低價格或產品優化進行調整,因為平臺經營者可以通過算法和信息優勢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做出反應。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對自營業務產生競爭威脅的平臺內經營者會被逐出平臺。上述事實不僅限制了消費者自由選擇的權利,也意味著他們需要付出更多的消費成本。
更為重要的是,消費者哪怕可以自由決策也會存在信息不充分及認知局限的問題。根據調查報告顯示,美國80%以上的用戶在使用搜索引擎平臺時不會瀏覽第三頁以后的內容[11]。這一結論對于電子商務平臺同樣適用,為了節約交易成本和搜尋成本,尤其在購買非貴重商品的情況下,消費者只會對比和選擇搜索靠前的商品。而且消費者的決策行為是高度情景化的,他們通常只會關注那些顯著信息[12]。對于消費者來說,基于對平臺算法公平性的信任,他們也更愿意相信排名靠前或者首頁推薦的產品更受歡迎。然而,自營業務搜索排名和流量上的優勢并非完全來自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質量更優或價格更低,而是摻雜了平臺經營者的人為干預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基于信息劣勢和認知局限更容易被誤導,做出不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四、優待自營業務的法律規制:平臺經營者的部分中立義務
(一)平臺中立義務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從法律關系上來看,作為中介方的平臺經營者并不參與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間的交易,而是超脫于買賣雙方的交易關系之外。對于平臺經營者來說,中立意味著不偏不倚、不傾向于平臺內市場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平臺經營者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可以納入非中立的范疇。正如上文所述,平臺經營者的自我優待行為會強化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并對平臺內市場的競爭造成現實損害。不管是損害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加劇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失衡還是間接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都源于平臺經營者不能保持中立、對自營業務和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一視同仁。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引入平臺中立理論,要求平臺經營者恪守中立原則,這也是對維護平臺內市場公平競爭迫切需求的回應。
平臺中立理論并非空穴來風,它是由網絡中立理論發展而來。美籍華裔教授吳修銘(Tim Wu)是網絡中立理論的首倡者。他認為,網絡中立性是普通法上公共承運概念在21世紀的新版本,網絡經營者應當極為公允地通過網絡設施為公眾承擔起運送所有互聯網信息的義務[13]。網絡中立的核心義務在于禁止不當歧視,它原本僅規制網絡運營商(ISP),要求網絡運營商為大眾提供普遍的網絡服務。因為只有讓所有用戶都能夠無差別地接入網絡,才能夠促進互聯網及其相關產業的繁榮。
在平臺經濟時代,為了應對各類平臺實施的非中立行為,不少學者希望將網絡中立或公共承運人理論擴展至平臺領域,由此提出了平臺中立理論。將網絡中立發展為平臺中立,最大的問題在于確定平臺的“公共載體”屬性。在持該學說的學者看來,網絡平臺(PSP)具有的壟斷權力、涉及公共利益并符合“純粹的傳輸”要求,因此它符合公共承運人的重要屬性[14]。既然是公共承運人,平臺經營者就應當保持中立,為自營業務和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提供無差別的平臺服務。此外,在我國不管是競爭法還是作為電子商務基本法的《電子商務法》,都以促進公平競爭為立法目標。在我國競爭法體系中,反壟斷法側重于保障競爭機會和競爭條件的公平,反不正當競爭法則更注重保障競爭手段的公平性[15]。不僅如此,電子商務法也強調要引導、監督本行業經營者公平參與競爭。其實中立和公平在語義上本就接近,平臺中立義務也就意味著平臺經營者應當公平對待自營業務和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競爭法及電子商務法的立法目標同樣為平臺經營者的中立義務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二)應然與實然的平衡:完全中立義務的克減
平臺中立義務意味著平臺經營者應當為所有用戶提供無差別的平臺服務,該義務可以矯正平臺內市場的競爭失衡,實現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的良性競爭。但完全的平臺中立只是一個理想的應然狀態,而將平臺中立理論引入自我優待行為的法律規制中還必須考慮到產業發展及立法的實然狀態。首先,平臺中立不僅在積極方面要求平臺經營者不歧視用戶,與此相對應,在消極方面其也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買賣雙方的活動[14]。申言之,平臺中立的消極方面就是指平臺經營者只需為買賣雙方的交易提供好平臺服務,而無需行使任何管理行為并對用戶的違法行為負責。但是為了平臺的良性發展并減少負網絡效應的不利影響,平臺經營者不可能消極地完全保持中立,而是應當具有公共性并承擔起治理平臺的重任。其實,平臺的公共性一方面要求平臺經營者不應濫用內部管理職權從事非中立的積極行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其平臺中立的消極屬性。
其次,平臺經營者有天然優待自營業務的動機,因此只要自營業務存在,平臺經營者就有可能實施非中立的優待行為。但是在《電子商務法》已經認可自營業務、競價排名等非中立行為的立法背景下,強制要求平臺經營者放棄自營業務、完全保持中立已不現實。更為重要的是,從經濟層面上來說,平臺經營者只有在更有效率時才會通過自營業務的方式進行縱向一體化,而且如果不允許平臺經營者將平臺整體資源用于自營業務的發展更會扼殺其創新商業模式、開拓盈利渠道的積極性。
雖然電子商務產業的實然狀態導致完全的平臺中立不能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中立義務無法在電子商務平臺的法律規制中發揮作用,平臺經營者亦可以隨意地優待自營業務。而且,作為平臺內市場的規制者,如果沒有中立義務的束縛,平臺經營者極易濫用手中的“私權力”和生產要素排除、限制競爭,最終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因此,為了實現實然狀態與應然狀態的平衡、維護平臺內市場的公平競爭,筆者認為平臺經營者仍應當承擔部分中立義務,即在滿足自身基本商業需求的情況下不得實施非中立行為。
(三)部分中立義務的具體要求
1.顯著區分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
部分中立義務的第一個要求為顯著區分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顯著區分義務來源于《電子商務法》第三十七條,是《電子商務法》就自營業務對平臺經營者做出的唯一義務性規定。根據該條的規定,平臺經營者應以顯著方式區分標記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不得誤導消費者。
雖然第三十七條的初衷在于保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但該規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平臺內經營者的競爭壓力。因為在顯著區分與標記的要求下,自營業務與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在某種意義上被分割。換句話說,雖然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與自營業務仍在同一平臺內市場中競爭,但在顯著區分要求的保護下,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被部分稀釋,而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也可以避免直接面對自營業務的沖擊。
2.提升平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部分中立義務的第二個要求為提升平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在代碼和算法的幫助下,平臺經營者可以單方面決定平臺內經營者的搜索排名、流量大小甚至去留。雖然在網絡空間中,“代碼即法律”,但是法律是公開的,而代碼的具體內容卻不為常人所知。為了破解“算法黑箱”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可能存在的“惡意”,保障平臺內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歐盟于2019年6月通過了《歐盟商業平臺條例》(《P2B條例》)[16]。該條例第7條明確規定,平臺經營者擁有自營業務的,應當在合同條款中明確說明自營業務與平臺經營者的業務間可能存在的差別待遇。此外,根據條例的規定,平臺經營者不僅在中止、終止和限制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時負有提前通知的義務,而且必須在合同條款中明確列出決定搜索排名的主要參數及各參數的選用理由。
歐盟《P2B條例》旨在提升平臺運行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讓平臺經營者不再能夠毫無顧忌地單方面損害平臺內經營者的利益。作為一個普遍性問題,上述規則對我國治理自營業務產生的諸多亂象同樣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因此,筆者認為平臺經營者應當將那些可能影響到平臺內經營者及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事項予以公開,尤其是搜索排名、流量分配等關乎平臺內經營者最根本利益的事項。此外,當同時擁有自營業務時,平臺經營者應當明確告知與之競爭的平臺內經營者自營業務使用了多少平臺資源、是否存在差別待遇及差別待遇的具體內容。唯有如此,才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護平臺內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實現平臺內市場的公平競爭和競爭機制的有效運作。
3.不得利用平臺內經營者的非公開數據
部分中立義務的第三個要求為不得利用平臺內經營者的非公開數據。數據在平臺經濟時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說擁有了數據就擁有了競爭優勢。在平臺整體數據的幫助下,自營業務可以獲得平臺內經營者的業務無法比擬的數據資源。多樣化的數據來源意味平臺經營者能夠更好地優化自營業務,并使自營業務在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更為重要的是,平臺經營者作為平臺基礎架構的提供者,還可以基于技術優勢獲取平臺內經營者的非公開數據,并將這些數據用于自營業務的優化中。雖然數據的法律屬性仍有爭議,但在現行法規范中,將部分數據擴張解釋為商業秘密可以實現對它的良好保護[17]。與基于平臺地位獲取的公開數據不同,這些非公開數據屬于特定平臺內經營者獨有,因此平臺經營者利用非公開數據的行為還有可能符合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侵害商業秘密行為的要件。而且,平臺經營者利用平臺架構和技術優勢取得這些數據后,再通過自營業務與原數據所有權人競爭,會造成單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并加劇平臺內競爭的失衡。因此,如果說平臺內的相互扶持仍可被認為是規模經濟下的正常商業行為,那么這種利用競爭對手的非公開數據并獲得競爭優勢的行為則應當被嚴厲禁止。
五、余論
由于縱向一體化的目標本身就包含了自我優待以節約交易成本,作為平臺經營者縱向一體化的方式,自營業務天生擁有平臺內經營者業務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在平臺經營者的優待下,自營業務的競爭優勢極易對平臺內市場的競爭造成現實損害。為了解決這些現實損害,本文僅從事前預防的角度希望能夠賦予平臺經營者部分中立義務,并從三個方面闡釋了部分中立義務的具體要求,但沒有觸及損害發生后應當如何通過競爭法尤其是反壟斷法規制該優待行為。
由于平臺經濟的特殊性,反壟斷法在規制平臺經營者優待自營業務的行為時會存在一定適用困境。盡管《平臺指南》已嘗試為其中的諸多難題提供解決方案,但其仍不完備,并需要在特定語境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能否跳過相關市場的界定、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濫用優勢地位的關系以及差別待遇的對象能否從交易相對人擴張到平臺內經營者等。總之,在數字經濟對傳統反壟斷理論不斷沖擊及我國《反壟斷法》修改的背景下,如何在理論上達成共識,形成一個體系化的競爭法規制方案并為實踐提供指引是未來亟須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康愷.反壟斷調查“第二季”:歐盟再撕亞馬遜 或進一步加強立法[EB/OL].(2020-11-12)[2020-11-24].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11-12/doc-iiznezxs1363905.shtml.
[2]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EB/OL].(2020-10-06)[2020-11-23].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N].人民日報,2020-12-19(1).
[4]楊立新.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自營業務的民事責任[J].求是學刊,2019,46(1):98-107.
[5]余佳楠.平臺在自營業務中的法律地位——以信賴保護為中心[J].法學,2020,(10):31-46.
[6]理查德·波斯納.反托拉斯法[M].孫秋寧.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03:263-267.
[7]劉權.網絡平臺的公共性及其實現——以電商平臺的法律規制為視角[J].法學研究,2020,42(2):42-56.
[8]Friedrich Kessler,Richard H. Stern. Competition, Contract,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J]. Yale Law Journal,1959,69(1):16.
[9]赫伯特·霍溫坎普.聯邦反托拉斯政策:競爭法律與實踐[M].許光耀,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19.
[10]孫晉,李勝利.競爭法原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3.
[11]壽步.搜索引擎競價排名商業模式的規制[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6(2):67-73,2,163.
[12]Russell Korobkin. Bounded Rationality, Standard Form Contracts, and Unconscionability[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3,70:1225-1226.
[13][美]吳修銘.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變遷[M].顧佳.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297-298.
[14]高薇.互聯網時代的公共承運人規制[J].政法論壇,2016,34(4):83-95.
[15]朱理,曾友林.電子商務法與競爭法的銜接:體系邏輯與執法展望[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9,(2):104-112.
[16]Regulation (EU) 2019/115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EB/OL].(2019-06-20)[2020-12-0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9R1150.
[17]盧揚遜.數據財產權益的私法保護[J].甘肅社會科學,2020,(6):132-138.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Self-operated
Busin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Neutrality
WU Kaiwen,LI Ming
(Law schoo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0, China)
Abstract:As a way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have a natural incentive to use “the private power” and data advantages to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self-operated business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t the same tim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lso has brought real damages to the operator on E-commerce platform,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s of platform market and the consum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platform neutrality theory to require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to abide by the obligation of neutrality, and network neutrality theory and the legislative goals of our country’s competition law also provide legitimacy for the obligation of platform neutra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reality and necess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complete neutral oblig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and fulfill their partial neutral obligation.
Key words:? platform neutrality;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self-operated businesse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編輯:鄒蕊
326050033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