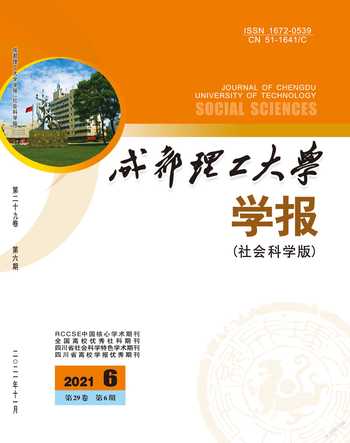方以智的理一分殊詮釋學路徑探析
凌紳燊
摘 要:在宋明理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理一分殊,在方以智思想中有著完整的運用。方以智將《中庸》《易傳》《禮運》結合起來進行論述,以《中庸》之首三句為綱目,對“道”“性”“教”中所蘊含的思維方法、詮釋架構等進行了逐層剖析。在對“道”的分析中主要從太極之普遍性,一與二的關系著手,在對“性”解析時緊扣性命、公性獨性而發,在關于“教”的闡述中對“以立教為權”之政府、立教之六經進行了深刻剖析,將理一分殊思想原則的普適性、靈活性展現出來,從而為正學、傳道指明方向。
關鍵詞:理一分殊;道;性;教;方以智
中圖分類號: B248.93???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2-0539(2021)06-0108-07
方以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現代學人多認為其成就可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相提并論。近年,隨著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出版,學界對方以智的研究傾注了更多的熱情,主要在易學思想、三教關系、性論、會通中西等方面成果豐富,然方以智思想中較有代表的理一分殊之特征,學界研究較少,本文便從此處著手以期對方以智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一、理一分殊溯源
理一分殊是中國思想史上對道體進行探索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和思維方式。《易傳》講“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1]304,又講“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289,可謂是理一分殊思想的重要依證。然此命題的提出是在宋代。關于理一分殊,程頤說道:“《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圣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2]以此來對理一分殊的思維方式與墨氏二本無分的異趣進行了說明。朱熹對其的觀點較為認同,并說道: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圣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3] 410
其下又說道:
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于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3] 410
太極是所以然者,是萬事萬物產生之依據,“太極生兩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雖然不同,然追其原始,受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卻是相同,即所謂理一。天道流行于個體,使萬物各得其宜,便出現了種種不同,也即是所謂萬殊。理一而萬殊,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亦不至于墨氏兼愛無父之弊。萬殊而理一,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亦“不牿于為我之私”。可見掌握理一分殊之精髓對于避免“兼愛”“為我”有重要之意義。朱熹所就學之李侗曾對朱熹說:“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4]可以看出,李侗將理一分殊作為區分儒學與異端的標志。
理一分殊思想對方以智的影響非常之大,其對理一分殊的運用主要集中在“道”“性”“教”三個方面,此三方面是與其對《中庸》的重視分不開的,其認為“《中庸》以三句約萬理矣”[5]15,此三句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6]。依此方以智將理一分殊運用得活靈活現,以下對此逐一釋之。
二、理一分殊在“道”中之運用
《易傳》中講“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 268-269,又講“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即是道,兩儀即是陰陽。方以智在對道的闡述上主要從太極的普遍性與化生的角度來進行,由此將太極與陰陽的關系清晰地呈現出來,而這其中理一分殊思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太極之普遍性
方以智在其著作中多有提到“太極”,當然在其諸多哲學概念中有“公因”“公心”“至善”“所以”等,乍一看似乎和“太極”無異,但究其實際便會發現此諸概念為針對“各一理”之理而發,而“太極”則是針對“共一理”之理而發,此諸概念可謂是方以智揭示“太極”之理的不同表達,可見他們與“太極”之間不能簡單等同。從易學本身來看太極,太極無聲無臭,不可用有無言之,也不能隨意用圖像來表示,但是對易學的解讀又不得不借助簡潔明了的圖像來輔助語言詮釋。周敦頤之后的學者從對所傳之《太極圖》進行的解讀來看,太極可以以“圜(圓)象”來進行表示,但是不能就此便將太極本身視為“圜(圓)象”。方以智認為“萬有萬無,莫非太極”[7] 120,其又有“兩間皆氣也,而所以為氣者在其中,即萬物共一太極,而物物各一太極也”[8] 1210之說,“萬物共一太極”“物物各一太極”可見在方以智那里太極是普遍存在的。“太極”是兩間之所以然,他決定著鴻蒙開辟以及古今萬事萬物的運動變化,是萬事萬物之所以存在的內在根據。太極無不冒,若要再追究下去則有不得已而命之者,則其“原自歷然”,實則太極即是“所以”,正如“先統后后亦先,體統用用即體矣。以故新其號曰太極,愚醒之曰太無,而實之曰所以”[9] 94一樣,其借助“所以”來揭示太極的本質。太極永恒存在,永不改變其作為萬事萬物之所以然的本質屬性。
太極以一切法、一切物為護身符,故太極為都符。太極最善逃,而人不能逃,此太極之所以毒也。彼謗太極、駕太極之上以自逃者,蚤(早)已為太極所藏,而彼不知也。彼烏知呼“太極”者何?呼“天地”者何?呼“易”者何?呼“物”者何?呼“心”者何?同在此中,隨呼即是,不呼亦是。[9]289
太極寓于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為表現形式,太極又為萬物之體,為“都符”即總符,人不能以一事一物來限量太極,正如不可以一事一物來限量圣人一般。“太極最善逃”,即是太極不局限于自身又不得不通過萬物來表現,太極藏于天地萬物之中,雖然不可見,“彼謗太極、駕太極之上以自逃者,蚤(早)已為太極所藏,而彼不知也”,但是人又處處在其規范、籠罩下。“彼烏知呼‘太極’者何?呼‘天地’者何?呼‘易’者何?呼‘物’者何?呼‘心’者何?同在此中,隨呼即是,不呼亦是。”此“太極”“天地”“易”“物”“心”諸稱呼,看似不同,然則所指實一。又:
太極也,精一也,時中也,混成也,環中也,真如也,圓相也,皆一心也,皆一宗也,因時設施異耳。各有方言,各記成書,各有稱謂。此尊此之稱謂,彼尊彼之稱謂,各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則何不信天地本無此稱謂,而可以自我稱謂之耶?何不信天地本無法,而可以自我憑空一畫畫出耶? [9]30
“太極也,精一也,時中也,混成也,環中也,真如也,圓相也,皆一心也,皆一宗也,因時設施異耳”,此種種稱呼雖都是對宇宙本體的稱謂,然究其實際,所指皆一,因時而異。各有其方言,“各記成書”,又各有稱謂,此尊此,彼尊彼,“各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追究天地之始,雖有物而無名,物實存,名隨人類社會發展而有,然不同之地,不同之時其名亦有所異,然究其實際則為一,不通稱謂則亂矣。
可知,從“所以”上來講,太極具有理一的特點,從“因時設施”上來講,其又具有分殊性,正如前所說“萬物共一太極”“物物各一太極”,太極普遍存在,同時亦體現了理一分殊之原則。
(二)一與二
“太極”是作為萬事萬物之本體的絕對性存在的,其實現是靠自身的衍演來展現的,方以智將此稱為“衍古太極”,“太極老翁嘗以無所得之圍謀必不免之范,若曰不可見者,人何以見?應以見載不見。于是乎作費藏隱之器,授之天地,而自碎其身,以為之用”[7]135,認為太極若要顯現其自身“不可見”的本性,便要“自碎其身”來發用其體,此又表現為逐層遞進然同時又是步步回歸的過程。
方以智將“大一”比作太極,將《禮運》中“大一”與“天地”比作太極與兩儀:“智曰:《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為天地,即太極兩儀也。……故自一至萬謂之大兩,而太極者大一也。大兩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為用。”[8] 9“大一”必然要分為天地兩端,對于一切陰陽和合之物來講,莫大于天地,對于“太極”的邏輯演變法則實際上也是事物的演變法則,正所謂“萬物共一太極,而物物各一太極也”,所以太極的“一而二”模式也適用于世間一切物,也即是說任何事物莫不在進行“一而二”的演變模式。太極不斷地一分為二,也說明了這正是表現太極為“大一”的必需條件,這也顯示了太極的“合-分”的意蘊。
太極雖在不斷進行“合-分”的模式,然其“分”后所形成的兩端亦有側重:
衍古太極者,始皆陽而無陰,陽之所不足處,則為陰,蓋主陽也。圣人曰:初不得謂之二,又不得謂之一;一陰而一陽,一陰即一陽……當陰含陽之時,亦重陽也;當陽沖陰而包之之時,亦重陽也。自此對待相交而生生不已,皆陽統陰,猶天統地、夫統妻、君統臣也。[9]100
對于太極衍演來講,“始皆陽而無陰,陽之所不足處,則為陰”,為“主陽”。圣人立教對于初始“不得謂之二”,又“不得謂之一”,“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10]4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10]4實現本能即陰,而所以成即陽,說太極要不落陰陽,不離陰陽,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謂“重陽”者,說明在太極分為陰陽兩端之后,太極之兩端亦有主次,所以有主次,“圣教惟在善用其當有者”[8]3耳。方以智在立說的過程中對于此可以說非常重視,也使得其思想特征由此而顯。其認為:“大要明體則暗用,明用則暗體,雙明即雙暗,遂有三表、三遮。”[7]20凸顯體則會使用不顯,凸顯用則會使體不顯,體用都凸顯便會體用都不顯。對于世間之說教亦如此,往往強調一方面會使另一方面不顯,強調另一方面會使這一方面不顯,兩方面都強調會使兩方面都不顯。“故《易》無體,因謂之無體之體耳。總之,即用是體,而逼人親見至體之方便,原不可少。”[7]27《易》無體,“即用是體”,“逼人親見至體之方便”。其認為:“人泥于二,不能見一。故掩畫后之對待,以從畫前之絕待,借設蜃樓,奪人俗見耳。一用于二,即二是一,寧舍畫后而有畫前之洸洋可執哉?”[7]目錄2人不能膠泥于二,這樣會使一不能見。一用于二,通過二便可探究一,即二是一,舍棄畫后想要去探究畫前是不足取的。又:“掩對待之二,所以巧于逼見至體之一也。究竟絕待在對待中,即用是體,豈有離二之一乎?所謂絕者,因世俗之相待而進一層耳”[7]8。對于“即用是體,而逼人親見至體之方便”,此處認為,之所以“掩對待之二”,是為了“逼見至體之一”。其又用比世俗之相待更進一層的絕待來表達,絕待在對待中,至體之一就在對待之二中,即用是體,通過用來探究體,用不離體,一不離二,不是去二外另尋求個一。對于一,其說道:“大一曰:我以天地卦爻為我,久舍身以充周之世,有談道而言行不合吾天地卦爻之凡者,顧乃高榜于天地卦爻之外,妄曰知我,我豈受之?”[7]26自太極生兩儀而下,太極便寓于“天地卦爻”,談論道不與“吾天地卦爻之凡”相合,而去“天地卦爻”之外進行探究,依此為觀,能說知太極,能說知一嗎?可見一便在二中,即用是體。“故曰:因二為真一,執一為遁一,貞一則二神,離二則一死。”[7]189-190此句話可以說將一與二的關系描寫得恰到好處,從這也可以看出理一分殊思想的運用。不止于此,其另有詳細之論述:
曰:圣人以天視,視虛空皆象數,象數即虛空。信如斯耶,斯可語矣。……孔子善巧,而名字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運》善巧,而理數之曰:“禮本于大一,分而為天地。”天地之數,止有一二而畢矣。……冒天下之道者,大二即大一而已矣。[7]29-30
其中認為,虛空皆象數,象數即虛空。從萬物之名字來講,又對理數進行說明,將理一分殊融入其中。認為天地之數,一二可以盡之。無論是“《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還是“禮本于大一,分而為天地”,抑或是其他種種都符合一與二的邏輯關系。按照這種邏輯關系,天地未分前、天地已分后;人之未分前、人之已生后;未畫前、已畫后,都難逃出此邏輯關系所表現的法則,大二即大一可冒天下之道。此處之大一在邏輯關系上即是理一,大二即是分殊。將《禮運》之大一與《易傳》之太極思想合論,可見自太極而下,在化生的過程中大兩即大一,而大兩是大一的不同表現形態,“不妨分之以為用”。到此可以明顯地看到與“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10]5所表達的思想可謂是高度契合。在此種邏輯中太極即是理一,陰陽即是分殊。理一并不妨礙其用之分殊;其用之分殊,并不妨礙其生成之理一。另:
“一生二,二生三”,非老子之教父乎?印度之伊帝目胸表一卍五葉,或綱六相,或立三玄三要,或立五位君臣,或指首羅而掃之。雖非實法,然何所逃于大一之分天地、天地之為大一乎?彼炫專門,重在遮二顯一,迸遮一而使自得之耳。[7]31
即便是老子之立說,印度之伊帝目諸說,雖然非實法,依然逃脫不出“大一之分天地、天地之為大一”,可見理一分殊思想之運用普遍存在。方以智立說具有明顯地將理一分殊思想運用于其體系內的特征:通過對一與二關系的論述,將理一分殊思想運用得活靈活現,使理一分殊的普遍性得以呈現。
方以智在對“道”進行分析時,主要從太極之普遍性,一與二的關系上著手,然無論太極之普遍性,抑或一與二的關系問題,其中都明顯存在著理一分殊的思想原則。
三、理一分殊在“性”中之運用
方以智本《中庸》之“天命之謂性”來論說性之名與實:“有情無情,莫不由焉,名之曰道。由與由者,求其主而不得,名之曰天命。以名其生機之流注焉,名之曰性,以名其功能之蘊藏焉。”[7]204-205道之浩蕩何處而非命?性之名因天道流注于個體而始有。方以智說:“言性所自,而曰‘天命之謂性’,究何謂耶?”曰:“孟子注之矣:‘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一絲尚疑,請自剝復而研極之。”[5]18-19其稱孟子注之“天命之謂性”,實際上是方以智自己引用孟子言注之。其如此這般,可以說是為了對天命之性之不可測不可知的神性進行揭示,圣人之德行由性體所出、天命所至,若能對此有知,子孝臣忠等皆為性之必然,此可以算識得天、性為一之率性境界。又:“虛無不塞,實無不充者,氣也,而神貫之。神用無體,風之濟虛也,孰為之耶?故邈其生成無體之體曰性,此不可睹聞者也。”[7]26-27其認為性無定體,倘若使其有定體便會有定相,則會落于物。早在《莊子》中就有:“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11] 對于天道或者性來講,如果落為可見之物,又怎么足以成為價值之源、萬物之本呢?方以智常用“中”來揭示“性”:
中也者,非動非靜,常動常靜,不可思議之極致也。首云天命之謂性,未發故屬天,不屬人。其曰性者中也,不妨隨時發為率性之道,修道之教。末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者中也,而不妨隨時發為三德、五道、九經。此中三教至理,無不貫徹。[12] 55
所謂“中”,“非動非靜,常動常靜,不可思議之極致也”。方以智將《論語》《中庸》《周易》綜合起來論性,通過“中”來揭示“性”之神性。雖謂“此中三教至理”,并非定論,但可以看出其烹炮三教之端倪。又:
且論性而必索之于未形未氣之先,則必失之于已形已氣之后,是偏認寂寞者為性也。……學人于此達其生生之本,則三界萬法,實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貫,有無可以不二矣。[12]47-48
論性若是“必索之于未形未氣之先”,便會“失之于已形已氣之后”,是為有所偏于性之寂。聶雙江、羅念庵等人主張求未發之寂體,正所謂“推極于先,性體始見耳”之實指。佛氏以寂靜言法性,正似此處之“是偏認寂寞者為性也”之所指,則其不達生生之本。
其論性亦與命相連:“氣聚則生、氣散而死者,命根也;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性體也。……如波蕩水,全水在波;如水成波,全波是水。此性命之不可二者也”[7]206。命根“氣聚則生、氣散而死”,性體“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此處便顯示出性命之“不可一”。性命又“不可二”,正如“如波蕩水,全水在波;如水成波,全波是水”一般。又:
性者,天之命也。圣人,性之不惑者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昭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誠而不息則虛,虛則明,明則照天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12]21
性為天之命,圣人為性之不惑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百姓與圣人性不殊,然之所以有區分則在于圣人為“性之不惑者”,而百姓情之所昏甚而至于終身不自睹。圣人知人性皆善,可以循此不間斷而至于圣,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如何盡性命之道呢?“誠而不息則虛,虛則明,明則照天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而這其中可以看出“誠而不息”之重要性,“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于穆不已”,可見盡性命之道亦要遵循生生之德。
基于此,方以智從公性、獨性兩層來論性。“公性則無始之性,獨性則水火草木與人物各得之性也。”[9]167其所說之“無始”即是“先天”之另一種說法,公性是先天存在,后天寓于物中,不隨物之消亡而消亡的性。其之所以被稱為公性是因為“所以為獨性者,無始以前之公性也”[9]168,公性是獨性皆具的依據。何謂獨性?“獨性則水火草木與人物各得之性也”。又:
物各一理,而共一理也,謂之天理。氣分陰陽,則二其性;分五行,則五其性。人物靈蠢各殊,是曰獨性,而公性則一也。公性在獨性中,遂緣習性。故學以剝復而用之,明辯而晦養之。[5]3-4
戴蒙曰:太一片(爿)而為陰陽,陰陽各一其性;分而為五行,五行各一其性;殽而為萬物,萬物各一其性。……此無所不學則無所不能者,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是人之性也,是獨性也。所以為獨性者,無始以前之公性也。[9]167-168
獨性是人物、物物相別的特殊屬性。“質論人之獨性,原是無所不學則無所不能之性,而公性即和其中”[9]180,倘若就人而言,獨性可謂是人先天所稟賦之認識能力。但是人與自然界的動植物畢竟有所不同,“公性在獨性中,遂緣習性。故學以剝復而用之,明辯而晦養之”,獨性要受到后天環境的影響,由此而產生的獨性之改變稱為習性。后天的學習對于先天獨性的保持和發揮是非常重要的。公性與獨性的關系和公因與反因的關系一致,“公性在獨性中”,公性寓于獨性,又“所以為獨性者,無始以前之公性也”,公性是獨性皆具的依據,又是獨性之統。“公性則一”也可以看出公性亦具有“絕待”性。公性具有理一的特點,獨性具有分殊的特征。
可以看出,方以智論性命、公性獨性皆不出理一分殊之模式,正如“此性命之不可一者也”“此性命之不可二者也”與“人物靈蠢各殊,是曰獨性,而公性則一也”之所述,可見理一分殊思想在方以智論性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四、理一分殊在“教”中之運用
方以智賦予了“政府”特殊的含義,“天之政府,必以立教為權”[7]109。“以立教為權”之“政府”在一個國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明末清初社會動蕩之際,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其有著深層次的根源。方以智主張用“宰理”對政治生活進行重新規范。他認為天道是禮樂制度、政治思想、施政綱領等的合理性來源,應當譴責不顧民眾切身需求的行為與做法,強調發揮“宰理”的積極作用,“問宰理,曰:‘仁義。’問物理,曰:‘陰陽剛柔。’問至理,曰:‘所以為宰,所以為物者也。’”[13] 所謂“宰理”,在其處可以說是“仁義”,發揮“宰理”的積極作用,也即是發揮仁義的積極作用。其下又加以說法,所謂“物理”,“陰陽剛柔”也。《周易·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1]326可見,所謂“宰理”“物理”也是對天道、地道、人道之獨特提煉。不止于此,其認為還有“至理”,所謂“至理”即“所以為宰,所以為物者”,正如“太極”是所以然者,是萬事萬物所以存在之依據。由此亦可以看出,其所謂“宰理”之背后亦有太極之作用存在,太極之理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亦無處不在。宰理關乎人道之興衰,而其中“政府”占有顯著位置,“舍政府之尊,又安有至尊之尊耶”[5]3,可見政府所處位置至關重要。對于傳統的君臣關系來講,屢屢產生自上而下之壓制和自下而上之篡權,君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可謂歷史發展的線條之一,君主與官僚集團之間之不合也是此起彼伏的發生,人民群眾對所謂的“肉食者”之間的權力斗爭表現出十分冷漠的態度。“先民有言:‘詢于芻蕘。’”[14]古賢者有言,有疑事應當與薪采者謀之,為了助力儒家“詢于芻蕘”政治理想的實現,方以智突出政府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也是方以智對“政府”處理“君”“民”關系的考察。方以智提出,“人知圣人以仁義為政而已矣,曾知政府既立,下以治萬古之民,而上即以治萬古之君乎。”[7]120由此可知,方以智認為政府在社會治理方面有著雙重的作用,既規范民眾行為又防止君主專制對群體生活造成的危害。政府是公共的,不是一家一姓的暴力機器,從理論層面上來講,對由君主專制向政府管理進行過渡具有重要的意義。“或即流而表源,或稱先以化后,權在政府宰民,并以宰君,主仆一家,森森即是渾渾,果會通乎?何礙偏舉。”[5]13君為主,民為仆,設立政府是為了使君民一家,實現仁義的政治理想。方以智正是想通過對政府角色的塑造來對當時所面臨的現狀進行調節,由此便可看出其意義之所在。
又:
編氓于里正,邑令于郡守,監司于開府,以次上屬,而內屬東西臺三省,省各有長,而屬于宰輔,君乃儼然統之,此無對之尊也。然當知凝命布政咸若率俾者,為直無對之尊也。非惟君相操此權也,郡邑里正皆有凝命布政之君道焉。[7]114
由此可以看出,對于各級政府方以智也有所構思,其所構思的出發點是為了使社會和諧、國家安寧,各級之間“以次上屬”。對于凝命布政權力的行使,不但君相,郡邑里正都有對此行使的能動性,可見此一方面可使國家政權一統,另一方面亦可發揮地方之靈活性。正如“萬物共一太極”“物物各一太極”之思路一般,可以說方以智對“以立教為權”之政府的構建是跟其對“道”的闡發一致的,其中貫穿著理一分殊的思想。在凝命布政之道上,體現了理一,在各級政府實際操作運行中則又有分殊之性。
不但“以立教為權”之政府,即便對于立教之典籍亦如此,方以智對此說道:
若正襟儒者鄙唾《六經》,《六經》一賤,則守臆藐視之,無忌憚者群起矣。今日久舞狻猊狎侮之戲,痛厭六瑟。六瑟之堂,若不注“信述好學”之真我,專襲“《六經》注我”之抗說,乃瓜坑砥柱也。有真知《六經》之注我者,知天地之注《六經》乎?我即《六經》,然后可云“《六經》注我”。既知《六經》即我,仍何妨于我注《六經》乎?天地注曰:無聲無臭,表于倫物,煙煙煴煴,醇于經史。[7] 137-138
在如此長的經學歷史中,有兩大詮釋傳統值得我們多加關注。即漢儒之“我注六經”和宋儒之“六經注我”已然形成,且二者之間對立尖銳,從恪守家法的角度來講,堅持此對立,是立學之根基。關于“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方以智認識到片面的恪守某種“陣營”都是不足取的,倘若真能做到“六經注我”,則“我即《六經》”,即便是“我注六經”也無妨。從中也可以看出方以智所認為的,正確解經勢必要突破此對立,超越漢、宋儒之解經傳統,使得己之生命精神與六經所蘊涵之生命精神融貫為一,如此解經才能避免漢儒、宋儒解經之片面性。可見,此中亦體現了理一分殊思想原則,倘若體認到六經中所蘊含的天地之理,以及由此而闡發之理,所謂“我注六經”或者“六經注我”只不過是分殊而已,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無論對于“以立教為權”之政府,還是立教之六經,其中所蘊含的大道不可不體認,只有體認了其中之內涵,也即理一,對于其所操作運行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分殊就好理解了。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在方以智的思想體系中,以《易》為樞紐,通過《易》將其他諸說統攝其中,處處顯示著易學色彩。方以智在對易學進行闡發的時候以“一以貫之”作為方法,在理論建構之中通過“無極”“有極”來凸顯“太極”,并對太極衍演的形式進行了探究,而這種種都體現著理一分殊的運用。其對理一分殊的運用可以說是以中庸之首三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為綱目來進行的,通過對“道”“性”“教”進行剖析將理一分殊思想運用得活靈活現。不但如此,在論述過程中其還將《易傳》中太極思想、《禮運》中大一思想與之合論,在思維方法、理論架構等方面將理一分殊思想原則完整地體現出來,通過此為正學、傳道指明了方向。
參考文獻:
[1]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M].《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宋〕程顥,〔宋〕程頤.程書分類[M].[朝]宋時烈,編;[韓]徐大源,點校.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845.
[3]〔宋〕張載.張載集[M].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
[4]〔明〕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7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452-1453.
[5]〔清〕方以智.性故注釋[M].張昭煒,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
[6]〔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17.
[7]〔明〕方以智.易余(外一種)[M].張昭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8]〔明〕方孔炤,〔明〕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M].鄭萬耕,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
[9]〔清〕方以智.東西均注釋[M].龐樸,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10]〔宋〕周敦頤.周敦頤集[M].陳克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0.
[11]〔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全四冊)[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634.
[12]〔明〕方以智.藥地炮莊 [M]. 2版(修訂本).張永義、邢益海,校點.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
[13]〔明〕方以智,編.青原志略[M].張永義,校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86.
[14]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上、中、下)[M].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146.
An Analysis of Fang Yizhi’s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One Unified Principle and Different Embodiments
LING Shenshen1,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2.Marxist Institute,Jiangx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Xinyu Jiangxi 338000, China)
Abstract:“One Unified Principle and Different Embodi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hich has a complete application in Fang Yizhi’s thoughts. Fang Yizhi discusse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Yi Zhuan and Li Yun together. Taking the first three sentence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the outline, Fang Yizhi analyzes the thinking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contained in “Tao”, “Nature” and “Education” layer by layer.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ao”, mainly from the universality of Tai Ch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two in hand, discussing the nature from nature to life to the universality of character and particularity of character. In the exposition of “Education”, the public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ix Classics of Education are deeply analyzed, showing the universality and flexibility of “One Unified Principle and Different Embodiments” ideological principle, so as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right learning and preaching.
Key words:? One Unified Principle and Different Embodiments; Tao; Nature; Education; Fang Yizhi
編輯:鄒蕊
36655003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