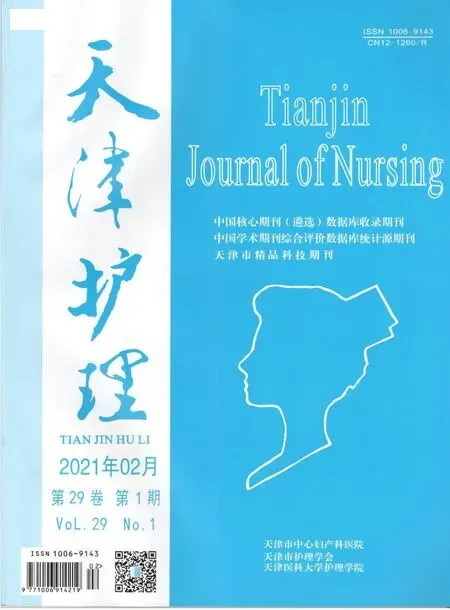“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構建*
趙燕 魏鑫洪 張夢 白雪 邸騰森 左鑫 宋子賀 陳梓瑜 胡潔
(1.河北醫科大學,河北 石家莊050031;2.青島大學附屬醫院)
目前,我國老齡化日趨嚴峻,慢性病發病率逐漸攀升,居民護理服務需求日益增大,而我國護理資源分布不均、護理人員緊缺,導致社區護理服務需求不能滿足,看病難、看病貴成了人們為之卻步的“攔路虎”[1]。因此,如何合理地分配護理資源,使醫療資源公平化,成為護理管理者亟待解決的問題[2]。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互聯網+”背景下的上門護理服務也應運而生。2015年5月,廣東省衛生計生委發布《廣東省持續改善護理服務重點工作方案》,鼓勵探索護士多點執業[3]。2019年1月,國家衛健委發布《“互聯網+護理服務”試點工作方案》,確定在北京、天津等6個地區進行“互聯網+護理服務”試點工作。但這些大多為原則性規定,缺乏實際操作性,諸如服務項目的相關分類標準、操作類型以及服務模式等,方案均未予以明確。本研究旨在構建“互聯網+”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為社區上門護士的進一步規范提供可行的培訓方案,為解決醫療護理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提供參考和借鑒。
1 研究方法
1.1 成立研究小組 研究小組成員共6名,其中研究生導師1名、研究生2名、本科生3名。主要任務是編制專家函詢表,遴選專家,并對專家的意見和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和討論。
1.2 初步擬定培訓方案
1.2.1 文獻回顧 檢索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萬方數據庫、維普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PubMed、Medline、Elsevier、CINAHL、Cochrane圖書館,檢索時限為2009年1月至2019年8月。檢索以自由詞和主題詞相結合的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上門護士”、“共享護士”、“網約護士”、“德爾菲專家咨詢”、“互聯網+”、“護士多點執業”;英文檢索詞包括“door-todoor nurses”、“shared nurses”、“online nurses”、“delphi expert consultation”、“internet+”、“standardized training”。按照篩選流程,對符合條件文章反復閱讀,刪去對本研究價值小、交叉等文獻[4-5],共檢索出724篇文獻,納入59篇文獻。
1.2.2 初步擬定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 文獻查閱的基礎上,經過小組討論,初步擬定了“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框架,包括護士執業資格及資質、護士核心能力及素質、上門服務禮儀、健康評估、基礎護理服務、專科護理服務、相關健康教育服務、護理職業安全培訓7個一級條目,52個二級條目。并就初步形成的培訓方案內容進行討論,最終確定函詢問卷內容。
1.3 編制函詢問卷 函詢問卷包含3部分:①致專家信,簡要介紹研究的背景、意義、方法及填表注意事項;②專家一般情況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職稱、學歷、職業領域等;③專家函詢表,包含了初步擬定的培訓方案指標條目,指標的重要程度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進行評價,依次分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5個等級并分別賦予5、4、3、2、1分。專家對問題的熟悉程度分5度:很熟悉、較熟悉、一般、不太熟悉、不熟悉,分別計1.00分、0.80分、0.60分、0.40分、0.20分[6];對問題的判斷依據分為實踐經驗、理論分析、參考國內外資料、直觀選擇,分別將其分為大中小的程度進行賦值,理論分析(0.30、0.20、0.10),經驗判斷(0.50、0.40、0.30),參考相關資料(0.10、0.08、0.05),主觀感受(0.10、0.07、0.05)。專家對相關條目的認可情況進行量化賦值,從重要度、相關度、可行度三個層面對各級指標進行分別賦值,分別計3、2、1分。另外,在問卷中留出足夠空間供專家對問卷內容發表修改意見。
1.4 遴選函詢專家 采取目的抽樣法選取從事臨床護理工作、護理教育以及社區護理工作的專家12名。專家納入標準:①本科以上學歷、中級以上技術職稱;②10年以上護理/醫療專業工作經驗,參加護士培訓工作或在護士培訓方面較權威;③自愿參加,有較高熱情,能提出較全面的建議和意見;④課題研究期間能持續參加兩輪專家函詢。
1.5 實施專家函詢 采用電子郵件的方式發放函詢問卷,函詢前與專家進行溝通。根據前一輪函詢結果的一致性確定是否進行下一輪函詢。本研究共進行2輪函詢,2輪間隔3~4周。第1輪函詢結束后以重要性賦值均數>3.5分,變異系數(CV)<0.25為標準,并結合專家意見對條目進行綜合篩選。由此形成第2輪函詢問卷,以同樣的方式發放給函詢專家。根據2輪專家的函詢意見對培訓方案進行修改,結合專家對各項指標提出的具體意見,經研究小組論證后對指標進行篩選[7-9],選擇率在80%以上的選項予以保留(選擇率=選擇此選項的專家人數/回復問卷的專家人數)。最終形成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內容。
1.6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所有數據錄入和統計均經雙人核對。分別計算各項指標的重要性賦值均數、滿分選擇率、變異系數(CV),同時計算專家權威系數、積極系數、肯德爾和諧系數(W)并進行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函詢專家基本信息 共邀請12名專家參與函詢,其中從事臨床護理工作4名(36.4%)、護理管理工作4名(36.4%)、護理教育工作2名(13.6%)、社區護理工作2名(13.6%),均具有一定的護理培訓經驗。實際有11名專家完整參與了2輪專家函詢(1名專家在第1輪函詢時脫失),11名函詢專家平均年齡(49.5±10.5)歲;工作年限(29.3±10.3)年;學歷:碩士7名(63.6%),本科4名(35.4%);職稱:主任護師6名(54.5%),副主任護師5名(45.5%)。
2.2 函詢結果的可靠性
2.2.1 專家積極系數 兩輪專家函詢各發放函詢表12份、11份,均回收11份,有效11份,回收率各為91.67%、100.00%,有效率均為100%。表明專家對本研究的關注度和積極性較高。
2.2.2 專家權威系數 專家權威系數用(Cr)表示,權威系數由專家對問題的熟悉程度(Cs)和專家的判斷依據(Ca)決定,具體計算公式為Cr=(Cs+Ca)/2[10]。結果顯示,專家判斷依據平均得分為0.85(0.81~0.87),專家熟練程度平均得分0.91(0.78~1.00),權威系數平均0.88(0.79~0.93),均>0.7。說明專家權威程度高,所得結果可靠。
2.2.3 專家意見協調程度 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用變異系數和肯德爾和諧系數表示,變異系數代表專家對每個指標重要性判斷的變異程度,采用Kendall’s W檢驗計算肯德爾和諧系數。變異系數越小,專家協調程度越高。Kendall’s W和諧系數越大,說明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越好[11]。結果顯示,第1輪函詢條目總的綜合指數變異系數為0.12,滿分選擇率為0.64;第2輪函詢條目重要性變異系數為0.09,滿分選擇率為0.77。2輪專家函詢的Kendall’s W和諧系數分別為0.231、0.377,經χ2檢驗后,P<0.00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明專家意見協調程度相對一致,結果可取。
2.3 “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確定 本研究初步擬定的“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包括7個一級指標、52個二級指標。
在第1輪專家咨詢過程中,2名專家在“護士執業資格和資質”中提出增加二級指標“護師以上資格”,據國家衛健委要求及目前推行的網約護士類APP顯示,社區上門護士對護士本身要求較高,“護師以上資格”是一個很重要且需要達標的方面,課題組經查詢文獻并討論后,采納該意見。2名專家提出社區上門護士的護理服務項目應涵蓋基礎護理服務項目和專科護理服務項目,建議增加一級指標“專科護理服務項目”,經查詢相關文獻,“輸液港維護”、“PICC置管”、“五項中醫常用護理項目(耳穴壓豆、穴位按摩、刮痧、艾灸、拔罐)”等均屬于專科護理操作,故將其均移入“專科護理服務項目”中。基礎服務項目中的“母嬰護理”應包含孕產婦以及新生兒在內的相關護理操作內容,涉及操作種類較多,建議分開敘述涉及到的操作,課題組討論后采納該意見。
3名專家建議將“健康評估”中二級指標“健康狀況”修改為“評估身體狀況”,其中1名專家提出,“健康評估”項目應包含分類為問診、體格檢查、心理社會評估、實驗室檢查、心電圖、影像學結果判讀等項目,而該二級指標“健康狀況”實際想表達的意思是評估患者的身體狀況,故課題組討論并采納該意見。另外對于涵蓋內容不準確的條目,課題組經討論后做了相應改動,如“健康狀況”中增加“自理能力”和“飲食方式”、“心理素質”改為“評估心理狀況”、“基礎護理服務項目”中將“壓力性損傷護理”改為“壓力性損傷預防及護理”、“輔助排痰指導”改為“輔助排痰及治療”、刪去“插管管道護理”、“鼻飼指導”改為“鼻飼置管護理”、“導尿”改為“留置尿管及護理”、“灌腸”改為“灌腸護理”;將“安全知識培訓”改為“護士執業安全培訓”,“入戶安全知識”“相關護理風險告知”合并改為“護理人員入戶工作風險評估及預警措施”,增加二級指標“護理操作相關風險”。最終共刪改二級指標13項,新增一級指標1項,二級指標6項。修訂后進行第2次專家函詢。第2輪專家普遍反映修改后的指標較滿意,最終確定8個一級指標和57個二級指標的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表1)。

表1 “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指標函詢結果

續表
3 討論
3.1 德爾菲法用于構建“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德爾菲法又稱專家函詢法,是綜合各領域專家的知識和經驗,通過數輪問卷函詢專家意見并反饋,對某一主題或事項達成統一意見的方法。具有避免面對面討論時產生的害怕權威、隨聲附和或固執己見等情況的顯著優勢,使參加者更容易接受結論,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權威性以及客觀性。本研究12名函詢專家來自臨床、教育、管理、社區領域,均參與過護理相關知識培訓,且所有專家權威系數均>0.7。有研究表明,在德爾菲專家函詢中,專家的Cr大于0.70即表明有較好的可信度[12],故此次專家權威系數較高,函詢專家具有代表性。一般在德爾菲函詢中,回收率達到50%是可以用于分析和報告的基本比例,70%以上為非常好的比例。而本次問卷回收有效率較高,一輪為91.67%,二輪為100%,說明專家參與的積極性較高[13]。變異系數越小,專家協調程度越高。Kendall’s W和諧系數越大,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越好。2輪函詢的Kendall’s W和諧系數分別為0.231、0.377,經χ2檢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說明專家協調程度較好,意見較為一致,進一步說明本研究中運用德爾菲法得到的函詢結果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14]。
3.2 構建“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全面性。本研究構建“互聯網+”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旨在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加全面的護理以及為“上門護士”等平臺提供有效參考和借鑒意義。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中,“護理執業安全培訓”重要性賦值均數排在首位,滿分頻率最高,變異系數也最小,說明專家對于護理執業安全培訓所列指標意見較一致,其次為基礎護理服務項目;專家指出操作環境決定操作內容,如對于操作技術過于專業的操作項目,如“靜脈輸液”和“PICC置管護理”等專項護理服務措施,建議盡量不在家中進行操作。此外,關于“上門護士”的基本條件和護士本身的醫療風險保障,修正后的2輪函詢表中提供了更為全面的指標框架。調查中,大多數專家對培訓的相關指標表示贊同,可見本研究項目的全面性。
3.3 構建“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重要性。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2.41億人,其中近1.5億患有慢性疾病,需定期進行健康管理,約有20%~30%的患者在出院后仍需護理,可見社區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對上門護理服務有著強烈的需求。而隨著《“互聯網+護理服務”試點工作方案》[15]等一系列政策的出臺以及“金牌護士”等APP的相繼問世,足以凸顯社區上門護士這一角色的社會需求。有針對性的培訓方案能夠有效解決護理人員服務水平參差不齊,提高護理人員自身的專業素質,進而為患者提供更優質的護理服務。“互聯網+護理服務”人員培訓方案既有利于衛生健康行業和互聯網的相互融合,進一步推動醫療資源的有效利用;又可以通過互聯網與醫療資源的有效整合,充分開發醫療資源,為患者和社區居民提供便利的同時,實現醫護人員的自身價值。因此,建立“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尤為重要。
3.4 構建“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可行性。研究結果顯示,2輪專家函詢的滿分選擇率分別為為0.64和0.77,Kendall’s W和諧系數分別為0.231、0.377,表明專家意見相對一致,對于本研究“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相關條目實施較為認可,進而也說明本項目具有可行性。上門服務對于護士來說,發揮自己專業能力的同時,也可獲得更多收入。互聯網背景下廣大社區居民對于上門護理服務的需求,以及目前“上門護士”共享平臺的多樣化,進一步說明了本研究方案實施的可行性。
4 小結
本研究通過兩輪德爾菲專家函詢構建了“互聯網+”背景下社區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研究擬定的基于“互聯網+”上門護士培訓方案的科學性和實用性較好,為社區上門護士的培訓提供了參考。專家對培訓方案的各級條目函詢意見趨于一致,專家積極性和權威性高,結果科學可靠。但是本研究也有不足之處,例如個別指標操作有待細化,信效度有待在更大人群范圍內驗證,個別指標有待更為詳細、具體、可行的制度來護航[15]。這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進而較好的滿足社區居民對“上門護士”的服務需求,同時也為今后“上門護士”平臺的全面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