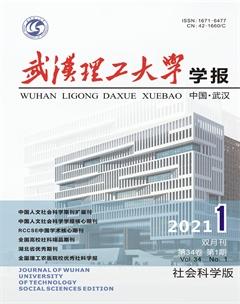“中國古典哲學走出去”之思考
摘 要: 作為“愛智”之哲學,屬于“共命慧”,從普遍性而言,它應當屬于整個人類,中國哲學亦然。要讓中國哲學走出去,為世人所接受,首先要作好基礎工作,即要把中國古典哲學的智慧完整地呈現出來,要把中國哲學的精華和特質彰顯出來,同時還要做好讓中國古典智慧走出去的相關準備工作并把握住時代所賜予的歷史機遇。
關鍵詞: 中國哲學;中國智慧;中國哲學特質
中圖分類號: B21; G125 文獻標識碼: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1.01.015
關于“中國哲學如何走出去”的話題(或曰“哲學話語權”問題),近兩年,學術界談的較多。以筆者淺見,中國(古典)哲學走出去,首先是態度問題。就是要承認并尊重中國文化,中國古典哲學同古希臘、古印度的哲學同樣偉大,同樣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承認并尊重古典哲學,才可能去鉆研它、研究它。其次,要有學術擔當和學術愿力。就近三百年而言,哲學的中心一直在西方,由英國而法國,由法國而至德國。正如葉秀山先生所總結的那樣:“十九世紀是德國的‘天下’,列維納斯說,二十世紀哲學無過于海德格爾;及至二十世紀后半期,法國人做著德國人過去做的工作。”[1]284-285今天,時光已轉進21世紀,“哲學中心”能否若季羨林先生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樣轉向中國?筆者以為,即便有此可能,亦非自發的,它需要中國的哲學工作者付出艱辛的努力。其三,且不言中國能否成為哲學的中心,即便從學術傳承與交流的角度而言,我們最切實的要務乃是做好基礎工作,須把自己的哲學智慧完整地呈現出來,把中國古典哲學的精華呈現出來。在此基礎上把握好“走出去”的幾個技術問題或“走出去”的細節問題,再漸次地讓中國哲學智慧推廣出去。
關于前兩個層面,較容易理解且學界討論亦多,故本文擬在第三個層面上進行展開探討。
一、將中國古典哲學智慧完整地呈現出來
探討“中國哲學如何走出去”的問題之前,首先要把中國哲學講好,倘若壓根不能講好中國哲學,那么“走出去”的問題就可能淪為空談——此實則涉及到“中國哲學如何講的問題”。
“中國哲學如何講”的問題,換言之,即謂“如何把中國古典哲學呈現出來”的問題。從學術發展之路徑而言,中國哲學的呈現方式大抵分為三種;一為“照著講”,即按照文獻資料的順序,不走樣地再敘述;二是“接著講”,即順著古哲的思路,把哲學引向深入,講出古人“應有”但卻未曾講出的東西,馮友蘭先生即持此主張;三是綜合地講,即把中國哲學放在世界智慧的背景下,將其同人類的其它智慧相融通、綜合,以彰顯其特色,張岱年先生所主張的“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創新說”大致如此。
三種講法,實質上體現了三種思維模式,“照著講”體現了靜態思維,其特征為哲學智慧的再現;“接著講”體現縱向思維,為哲學智慧的延伸;“綜合講”表現為綜合辯證的思維模式,其特征表現為不同哲學智慧的融合。就哲學自身的發展規律而言,我們自然應該注重“接著講”與“綜合地講”。事實上,自“五四”以降,學術界也一直在后兩種講法上下功夫,且講出了新意,譬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牟宗三、張岱年等大學者皆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就當下人們對古典哲學普遍存在的隔膜現象而言,“照著講”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筆者這里倡導的中國哲學“照著講”,絕非照本宣科、機械地敘述,而有其特定的內涵,即通過對古典哲學的再理解、再把握的基礎上,把中國古典哲學智慧完整地呈現出來。
首先,“照著講”是要把哲學問題講準。這里的講準,要求講述者將中國哲學能以客觀的姿態,盡可能準確地將其哲學智慧原型呈現出來。這勢必要求講述者既要熟悉文獻,亦要通透義理。中國哲學,其智慧博大精深,其問題同樣也錯綜復雜,不同學派間存在著“斬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因此真正把哲學講“準”并不容易。譬如,作為文本的《老子》同孔子的時間的早晚問題(馮友蘭認為孔子早于《老子》,理由是“無”針對“有”而來,首先要“有”,然后才有與之對反的命題出現),儒、道依何劃分?法家、道家、儒家有如何關聯?名家緣何衰落?墨家同道家的關系如何?問題可謂多多!此外,“照著講”勢必涉及到學理的問題,儒家之道同道家之道的通性何在?莊子之自由同郭象之自由有何區別?佛家之“空”同道家之“無”的分際何在?漢儒與宋儒的分殊如何?如此問題,舉不勝舉。欲厘清此種問題,既涉及到文獻的問題(辨別文獻的真偽頗需功力),亦關涉到講述者的態度問題;倘若講述者對某派哲學抱有成見,或缺乏相當的功力,怕是很難講準。
其次,“照著講”須把哲學問題講透。講透需建基于講準的基礎之上。將問題講準,目的在于讓人有一個客觀準確的了解;而講透則是問題本身的深化,它既涉及到問題產生的背景、發展的趨勢等較為宏觀的視野,更牽涉到問題的細節——因為“透”總是關聯著細節,問題不能追問至細節,就難以講透,就難以領會中國哲學的妙處。一般而言,對于中國哲學稍有研究者,大抵都能“大而化之”地給出所謂“春秋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之宏觀概括,然而若具體到細節,譬如先秦的“仁”、“誠”、“道”、“幾”、“自然”等概念的含義為何?魏晉時期的“空無之辯”、“自然與自由之辯”(“獨化”與“無待”的差異)、“才情之辯”等內涵如何?宋代的“理、氣之辯”“理、欲之辯”“心、理之辯”“情、理之辯”是否厘清?……諸如此類細節問題,絕不在少處。無疑,若缺乏扎實的文獻功夫和對細節的探究與體察,是難以呈現古典哲學的精彩之處的。
再次,照著講,須把哲學問題講通。講透要求重視和把握細節的妙處,講通則強調整體上的融會貫通。中國古典哲學門派眾多,但主干大致可歸結為儒、釋、道三類哲學。因此講中國哲學,必須對此“三家”有一個融通的理解和把握,此乃從事中國哲學的學者應具備的基本素養。毋庸諱言,由于學科的精細化,使得一些學者疆域自治,彼此不能貫通——治儒者不懂佛學,治道(家)者對儒學不通透,治佛者對儒、道不熟悉。更有甚者,即便從事某一類哲學者亦未必真正貫通。譬如,從事兩漢儒學的研究者竟然對宋明理學不甚熟悉,甚至相當隔膜。遺憾的是,學界這種狀況并非個案。此種態勢下,即便“照著講”都困難,又何談“接著講”?須知,“接著講”須建基于融通的基礎之上,譬如馮友蘭先生之所以能接著宋明理學講,熊十力、牟宗三之所以能接著陸王心學講,皆在于他們對儒釋道有著融通的把握和嫻熟的理解。對于儒、釋、道之通,牟宗三先生曾有妙論,他認為,一個真正的通儒必然能真切地體會到道家和佛學的精髓,同樣對道家、佛學有真正研究的人也必然懂得儒家,因為三者在境界上是通的。非但儒釋道是通的,每一學派亦應該是通的;然而,后學卻學派林立,此固然與其學養不足有關,亦與其缺乏博大胸懷有關。
把哲學講通并不是簡單的事。倘若不能貫通三家智慧,那么所講的哲學是不圓融的,至少不能把中國的智慧完滿地呈現出來。客觀地講,當下既精通儒釋道又透悟西學的大學者不是太多——甚至真正能貫通儒釋道這三家學問的大學者亦不多見,這尤須當今中國哲學同仁的共同努力。
最后,要把哲學問題講活。所謂講活,并非外在的活,而是中國哲學的特點決定了必須講活。就活之特點看,中國哲學表現有三:其一,中國哲學根底上是關于生命的學問,是活潑潑的學問;其二,中國哲學的表現形式是生動活潑、不拘一格的,或格言、或寓言、或詩歌、散文乃至小說,概而言之,“文史哲”渾然一體,具有鮮活流動之質感;其三,中國哲學不是死的知識,而是具有強烈現場感的“生活的智慧”和真實的生命體悟。鑒于此三個特點,講述中國哲學須扣緊生命這個根本指向,即便涉及到的哲學概念亦須向生命上收攝;要以靈動的方式講述中國哲學,以鮮活的故事來講哲學,讓“載道的文獻”靈活起來;要將古老的智慧同現實生活鏈接起來,讓“現場感的智慧”充盈當下并試圖化為方法論,來提升我們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上述標準衡之,“照著講”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簡單,它同樣需要心血、心智的付出。對不少從事中國哲學的學者而言,“照著講”仍是一門基礎性的功課,也是當下努力的方向。道理很簡單,只要做好“照著講”,才可能更好地“接著講”乃至“綜合創造地講”;同時,也只有在全面系統地把握中國哲學的基礎之上,才可以真正知曉中國哲學特質與精華之所在,才可以把精華之處顯揚出去。
二、把中國古典哲學的精華呈現出來
從事中國古典哲學研究,不僅僅意味著把中國哲學作為一個整全系統對待之,亦不僅僅停留在講通、講透、講活,還必須練就一副火眼金睛,要能從浩瀚的哲學文獻中攫取中國哲學的“特別處”與“閃亮點”,要能在長期的思考與體悟中凸顯中國哲學之特質①。一句話,從事中國古典哲學的研究者須將中國古典哲學的精華較為完整地呈現出來。此亦是讓“中國哲學走出去”的學術層面的核心工作之一。
筆者認為,探討“中國哲學之特質”或曰“中國古典哲學的精華”,大略可從以下五個方面著眼。
其一,要將“生命哲學”的意蘊凸顯出來。
與西方哲學相比較,中國哲學根底上是生命的哲學,誠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華民族之靈魂乃為首先握住‘生命’者。因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注意到如何調護生命、安頓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講說道理,其基本義皆在內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則在修德安民。”[2]當然,這并非說西方哲學不重視生命,但就主旨而言,西人的精彩在于思辨之知識,而中國哲學則重視生命,其精彩處亦在于生命;與印度哲學相比較,印度哲學同樣重視生命,但他們更重視“來世的生命”,中國哲學對生命的重視是“全方位”(此言中國哲學尤重生命本體之研究)的,但主要針對現世之生命。這種“現世之生命”,并非僅僅重視物質之存在,更是重視人格(修身、修德)之養成。人格乃是精神的生命,是人之為人的根據。華夏民族的一切優良傳統皆建基于此,無論儒家經典《易經》所凸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取意識還是道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的以“無為”為特質的謙讓文化;無論墨家站在平民立場所踐行的“尚同、節葬、非攻”的兼愛主張還是法家帶有策略性的“法、術、勢”具體制度之設計,根底上在于成就生命,安排生命,實現生命,以及最終完成生命,實現生命的價值。中國古典哲學也涉及思辨的內容,但總體觀之,不占主流,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言,中國古典哲學“也重視思辨,但只占次要的地位。中國的思辨是為實踐而思辨的,西方的哲學是為思辨而思辨的。”[3]也許今天看來,中國古典哲學難免存在偏頗之處,但是其對“聚焦現實之生命”的特質是顯然易見的,此乃其生命力之所在。尤其是儒家,更具有生命的擔當感和強烈的族類意識,譬如,孔子“文不在茲”之文化承載,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與“舍生取義”的道義擔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生命承擔與族類意識,無不透顯出其對生命的尊重與呵護,此乃元氣淋漓的生命哲學之宏大氣象。華夏民族五千年的學術史、文明史,乃是圍繞生命之證成而展開,今天我們探討的諸如以人為本、仁愛、勤勞、謙讓、節儉等諸多傳統美德(核心價值)皆從生命哲學這一總根源中流淌出來,尤其值得我們傳承和發展。
其二,要將人之“內在道德的主體優位”顯揚出來。
中國哲學的核心在生命,生命的價值在于道德。關于倫理道德哲學,西方亦不缺乏,然其最大不同點在于,中國的道德根底上是內在的、自律的,而西人的道德就主流言則是外在之他律(康德哲學同樣推崇內在道德,強調道德自律,此為國人所熟知),依靠上帝之監督,或以外在“規制”(懲罰)來獲得。中國哲學強調道德內在,人本質上就是天道的承載者,是道德的主宰者。此如《中庸》所謂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意識就是道德意識。道德由天命下貫,并凝存于心中。良知被喚醒,便是仁心發動,與天地宇宙打成一片,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其意。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大程子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陸九淵謂“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及至王陽明,更是開出“致良知”之妙理。鑒于“仁義內在”的道德主體優位之考量,歷代圣哲之要務就在于喚醒人之內在之德性,以使得人能“以德配天”,挺立于天地間。古哲(從孔孟至程朱、陸王,皆然)如此,今哲亦然:馮友蘭先生所勾勒的人之“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之說,意在激勵人們要完成崇高的人格;方東美先生提出的由“三階九層”的“人格超生論”②亦反映了現代大哲對“人性善”的期許;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皆將“挺立道德主體人格”置于要位,皆在于凸顯道德之價值。無疑,此與西人匍匐于上帝之下的卑微之狀截然不同。
中國古典哲學之所以探討道德,還在于:以中國圣哲視野觀之,道德是內在的,是“求之在我”(孟子),是“吾欲仁,斯仁至矣”(孔子),是簡易之極的。而知識則不然,因為知識是“外在”的,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是孟子所謂“求之由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盡心上》)。這種取向與西人截然不同。中國古典哲學承認道德內在,承認道德“操之在我”,但并不因此就“放任自流”,因為要完成這個“簡易”之德,是需要誠意、慎獨等一系列的修煉,需要猛下工夫,缺乏工夫的道德言說為中國古哲所不恥。
順便提及,中國古典哲學對道德內在的視野及“道德優位”的認可,尤其凸顯了人格平等的理念,“人人皆可成堯舜”,“途之人可以成為禹”,即為人之德性平等、人格平等的最好注腳,這一點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可謂彌足珍貴。
其三,要把“真善美合一”的境界哲學之特質豁顯開來。
中國古典哲學追求道德,追求至善,但這個善不是孤立的,而是同美、真(誠)相互貫通的。西方哲學求真,求美,亦求善。然而,其真善美之追求與東方顯然不同,要點有二:其一,西人的真善美更多的表現為理論的訴求與知識的開拓,與實踐未必合拍,故而其關于真的理論盡管縝密、可信,但關于真的行為則未必“果真如此”,此誠如王國維先生總結的那樣,“可信者不可愛”;其二,西人關于真善美的探討就整體而言乃是割裂的,因三者分屬不同的研究領域,大哲康德極力將三者“粘結”起來,雖付出巨大心血,但限于西人思維二分、知行二分,結果亦難盡人意。時至今日,以西方學術觀之,真者自真、美者自美、善者自善(此言即便在研究領域層面,三者亦是割裂的)。
中國哲學則不然,其真善美在理論體系上圓融一體,相互貫通。孔子所言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可謂將真善美視為有機的整體;孟子在《盡心·章句下》中有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之之謂神。”此在理論上進一步闡明了真善美的有機性、圓融性——追求仁(可欲之物,此做“仁”解)就是善,把這種“善”切實地充實于自身就是信(真),把這種“充實于自身的德性”發揚下去就是美——當真善美完美地結合于一體定能引領社會風氣,這就是圣人的境地了。關于“充實”之義,牟宗三先生曾論之:“所充實的是什么呢?那必是‘天道性命相貫通的這個立體的骨干’。”[4]中國哲學之真善美在行為上表現為“知行合一”。知仁曰真,行仁曰善,而依據仁所呈現的過程就是美,三者是統一的。固然,古典哲學之道、仁、義未有嚴格的定義,在邏輯上未必可信;但是君子卻能根據本心(良知)實踐出來,此乃是其最可愛處,最感人處!關于中國哲學家的知行合一,以研究邏輯學名世的金岳霖先生曾評價道:“(對中國哲學家來說,)哲學從來不單是一個信條體系,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以說是他的自傳。我們說的并不是哲學家的才具——他可以是二流的哲學家,也可以具備他那種哲學的品質——那是說不準的;我們說的是哲學家與他的哲學合一。”[5]這個評價是中肯的,中國古典哲學家即便其學識二流,然卻體現著“知行合一”的誠之品格,體現著真善美的有機統一。
其四,要將中國古典哲學的“和”之包容品性宣揚出來。
“真善美”之所以能完美地融為一體,其根蒂在于中國古典哲學“和”之特色。雖然中國在秦漢以來形成大一統的歷史傳統,但大一統下的政治觀并不排斥古哲“和而不同”的包容哲學觀。中國古典哲學自誕生起,就傳承“和”的包容觀念。包容只是籠統的說法,細講來,中國哲學中包容(和)的含義是非常豐富的:《乾·彖傳》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及《中庸》所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從自然萬物并存、共處的角度來探討“和”之價值;《國語》言“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則從事物發展、存在的角度探討“和”的意義;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則從為人處世的角度對“和”進行探討;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是從生成論的角度談“和”;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則是從“人心向背”之戰爭維度探討“和”;……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提煉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6]的“交往原則”,可謂是中國哲學古典之“和”在當代的詩意表達。
總之,“和”是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關鍵詞之一,“和”的包容品質,內在地要求人們與天合、與地和、與人和,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此哲學理念下,包容性顯示出開放性的特點,異域的學術思想(尤其以佛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代表)方可在華夏大地落地生根。中華民族在學術思想史上也因此呈現出博大氣象與豁朗之局面,春秋時期的諸子興起、魏晉時期的儒道爭雄、宋明時期的儒釋道三足鼎立,乃至今天哲學界仍然“中西馬”鼎足而立且有會通、交流之勢,皆是以“和”為底色,并因此大大繁榮了思想學術。
同時,這種獨具“包容”品質的“和哲學”(亦有學者如張立文先生稱之為“和合學”)也切實地影響到執政黨的執政方針,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新中國的諸多大政方針皆打上了包容哲學的烙印,建國初所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國際交往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一國兩制”的勾勒與實踐,當今我們對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局勢的把握,皆是“和”之包容特質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今天,“互聯網”拉近了國際間的距離,然而國際關系日益復雜、人際矛盾愈發彰顯,人與自然的關系益發緊張……,因此,如何將中國古典哲學的包容品質彰顯出來,如何將中國的“和”哲學大力地宣揚并運用到實踐中就顯得尤為必要了。
其五,要將系統、整體的圓融思維模式呈現出來。
中國古典哲學的主要思維模型乃是“系統、整體”的有機思維,這種思維的特點在于,它把任何個體都置于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宇宙格局之中,個體的行為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關系網絡中的一個結點,它通過“非線性”的方式在時空中沉積、發酵,直至產生宏大的影響。此思維原型當來自于有天人之學之稱的《周易》,《周易》首先通過“觀物取象”的直觀思維,將事物按陰陽的方式分類;繼而以“八象”(即八卦)的方式將宇宙囊括其中,其中卦卦之間、爻爻之間、卦爻之間皆有著錯綜復雜(即錯卦、反卦)之聯系,而每一卦、每一爻皆又對應著不同的時空。由此,天地人、時空、自然萬物乃凝結為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整體。此種思維一經流淌而出,便一發而不可收,影響中華民族數千年。以其對中國形上哲學的影響而言,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孟子》)乃至由此工夫而達到的“與天地參”的天人合一之哲學理境,道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與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莊子·齊物論》)及“道通為一”的哲學觀,佛教中國化之典型代表如天臺宗之“一念三千”、華嚴宗之“四無礙”(即理無礙、事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十玄門”之義理等等,無不突顯了整體、系統的哲學思維,尤其是華嚴宗與天臺宗,更是將這種有機思維推至極為圓融的境地。以其對具體的有形文化影響而言,以“家天下”而延伸出來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念,以調和陰陽、把人體視為小宇宙的中醫文化,講究整體布局、氣韻流動的藝術文化,綜合陰陽、五行、八卦等理論為指導的“負陰而抱陽”的建筑(風水)文化,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五味雜陳(調和)”的飲食文化,甚至帶有術數性質的擇日、占卜、星相等民俗抑或神秘文化,其根底莫不是“整體思維”在實踐中的妙用。
無疑,承載這種整體思維的工具——漢字,更是具備此特性。漢語的用法非常靈活,除非你懂得整體的意思,否則靠單純的語法分析是很難湊效的。物理學家F·卡普拉這樣描述:“中國人的思維并不采用抽象的邏輯思維,而是發展一種與西方相去甚遠的語言。許多中國的詞語既可以作名詞、形容詞,也可以作動詞。因此它們的序列主要不是取決于語法規則,而是句子的感情內容。”[7]80何止是理解句意如此,理解中國古典哲學亦然。如果不能透悟“整體有機思維”模式,是很難真正理解中國文化的——無論是我們“和”文化的包容品質還是“真善美”合一的哲學理境,無論是對生命價值的倚重還是道德內在的優位定位,其中始終貫穿著系統、整體的獨特思維模式。
相對于理性的邏輯思維而言,這種有機思維模式充滿混沌性、直觀性乃至神秘性。然而,它的價值是無法否認的,即便在科學認知領域也是如此。正如F·卡普拉指出的那樣:“我把科學和神秘主義堪稱是人類精神的互補體現,一種是理性的能力,一種是直覺的能力。它們是不同的,又是互補的。不能通過一個來理解另一個,也無法從一個推出另一個。兩者都是需要的。”[7]243他還從物理學的角度對中西兩種思維進行比較,認為“人類文明能否存在下去也許就取決于我們能否進行這種(思維的)變革,它最終取決于我們采納東方神秘主義某些陰的態度的能力,要有體驗統一自然和協調生活的藝術”[7]245。正是基于古典思維所具有的過去與未來的雙重考量,從事中國古典哲學的學者一定要把這種系統、整體的東方獨特思維模式呈現出來。
當然,正如光與影子的關系那樣,光愈強,影愈暗,哲學文化亦然。古典哲學的優長從反面看也是其缺陷:譬如重視生命忽視了知識的開拓;重視德性忽視了法制的建設;重視“統一”忽略了差異;重視“和合”而忽視了對立、差異;重視了混沌思維忽視了分析思維。然而,我們必須知曉一個事實,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東西,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完美。中國古典哲學雖然存在諸多弊端,然而卻能讓中華民族傳承五千余年而不衰,這難道不是奇跡?!難道不值得我們繼承、拓展與弘揚?!
三、處理好“走出去”的幾個技術問題
講好中國古典哲學,彰顯古典哲學的精華,是“中國古典哲學走出去”的基礎工作——當然是奠基性的工作;中國哲學欲走向世界,還需做好幾個“技術性”的工作——此技術工作當然奠基于前兩步的基礎之上,筆者姑且稱之為幾個關鍵的“技術問題”——它既包括學術表達體系的構建、語言的翻譯及問題的切入點等關乎學術的“技術問題”,也包括善于把握人類共性的問題、善于把握機遇等關乎視角、敏銳性等“技術(巧)的問題”。
首先,要構建好中國哲學智慧的“表達體系”,此乃關乎中國古典哲學能否走出去的“學術前提”。
中國古典哲學注重生命的體悟,不注重語言的言說——雖然在中國古典哲學崇尚有機、系統思維,但在表達(敘述)層面較零散。相反,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多是連貫的、以專著的形式出現,按徐復觀先生的說法,西方哲學家思想的結構表現為其著作的結構,“他們著作的展開,即是他們思想的展開,這便使讀者易于把握”[3]70;中國哲學家則很少能意識到以有組織的文章結構來表達他們的思想結構,他們的思想零星地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之中,甚至信札之中;同時,在同一篇文章或一段語錄中,又常關涉到許多觀念,許多問題。因此,要把中國哲學“說”好,就要在整理上下功夫,不但要認真對待每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而且還要認真對待整個哲學史。關于這一點,第一部分已涉及到。除此之外,今天的學者還需在“體系表達”上下功夫,正如第二部分所述,中國哲學至少有五大特色,我們要把五大特色貫通一體,使之成為融貫的體系。這個更像“寫家譜”一樣,非常基礎但又頗費功夫,且十分必要。這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需要有志者艱苦的付出;同時,這也是一項創造性的工作,替古哲把“散亂的珍珠”串成適于現代人接受的體系同樣是一種創造:理清其中錯綜復雜的關系、融通各種學派間的矛盾與困惑,既需要嚴謹的邏輯方法也需要極高的文字修養。惟其如此,我們的哲學智慧才能易于接受,且不說為外人接受,即使對國人,也同樣如此。
其次,要把我們的哲學精華翻譯好(轉化好),此乃思想交流的關鍵。
中國有著豐厚、深邃的哲學智慧,自為國人稱道,然卻不為外人所知。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諸多歷史的原因,亦有文化自身的原因。譬如,漢字難學,漢語難學,古漢學尤其難學,由古漢語所傳達的哲學思想則是難上加難!據哲學家熊偉先生講,德國大哲海德格爾對漢語之難,竟然帶有敬畏的態度,“在關于康德的《先驗辨證論》的一個專題討論班上,當一次發問無人回答時,海氏說,‘這并不難,又不是中文’,可見海德格爾當時似把中文視為不可企及的事”[8]115。且不說當下的大多數國人對古漢語存在隔膜,即使是專業人士亦未必能完全理解漢語的古義。此種態勢下,若讓古典哲學走向世界,確有難度。因此,這就需要一流的翻譯,能用典雅的外文表達出古典哲學的神韻,這尤其需要懂外文的哲學大家,或懂哲學的語言大家,若二者缺一,恐怕皆難以表達出古典哲學的神韻。眾所周知,古典如《周易》《論語》《老子》,雖在數百年前就被翻譯為英文、德文等諸多語言,然而當時的翻譯多停留在字面的對譯,難以表達出中國古典哲學之智慧。這一點,我們可以學習佛教的做法。佛教之所以能傳入中國,與鳩摩羅什等大師的翻譯分不開,為了翻譯佛經,他學習中文數十年,以至于能用文言文寫作出一流的文章。上世紀,馮友蘭、方東美二先生皆以典雅的英文分別著述《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在國際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為中國哲學贏得了一席之地。惜乎當下我們尚缺乏這樣的大家,如何培養復合型人才,如何讓一流的哲學人才同一流的翻譯人才進行無縫對接、融洽合作(當然能將二者融于“個體”更好)亦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復次,要精通至少要熟悉西方哲學思想的精華與套路,以便尋找學術會通與思想交流的關節點,并借此提升中國哲學的品質。
《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進行學術交流或文化傳播,固然需要“說出自己的”,同時還要“知曉別人的”,否則,將會陷入自說自話的“獨角戲”之境地或陷入隔靴撓癢的尷尬之中。我們自信有古典哲學智慧,同時還要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智慧,這樣方能通過比較,更好地知曉中國古典哲學的優長與不足。同時,也只有通曉異域哲學之智慧,一則我們可以找到溝通與傳播的契機和關節點;二則可借此進一步提升中國古典哲學的智慧。哲學智慧的提升需要碰撞與刺激,更需要交流與融合。葉秀山先生在研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提出這樣的看法:“從某種意義來說,西方哲學的希望在于‘非西方’,希望在‘東方’,在‘東西方之融合’。”[1]279事實上,哲學界的有識之士已經展開了這個融合的工作:關于西方人以中國哲學來提升其哲學層次的,如果說在黑格爾時代,還較罕見,那么在20世紀則逐步展開。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爾,雖然其晚年發出“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世界”的說法,然而晚年的海德格爾對中國哲學充滿興趣,其高足比默爾教授在1991年于北大講學時講到,“海德格爾專心致力于弄清中國世界,皆因其看法是,沒有中國語言的知識,沒有對中國世界的明見,就不可能有真實洞察的通道”[8]128。至于漢學界的名家如費正清、愛蓮心、史華澤、耿寧等,已默默耕耘數十年,早已取得較豐厚的成果。中國人以西方哲學的理論來提升中國哲學品質的更是舉不勝數,其中尤以“現代新儒家”這個群體為典型。以牟宗三先生為例,其為融合康德與儒家哲學所提出的“智的直觀”“一心開二門”“良知的自我坎陷”“圓善論”等理論,可謂在融合會通的基礎上將儒學乃至康德哲學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讓中國哲學走向世界,讓哲學說“中國話”,本意并非要“中國文化主宰世界”,而在于取得學術交流的發言權,平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因為在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宰制下,一些學者甚至都不敢承認自己的哲學,他們的研究無非是跟著西人后面亦步亦趨。此固然取得了對話與交流的機會,然而“亦步亦趨”的姿態本身,已決定了他們所研究的哲學無非是拾人牙慧而已。今天,我們讓哲學說“中國話”,須在對等的基礎上,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心態下,敞開胸懷,合理吸收,平等交流,以達到融合貫通、紹述并提升中國哲學的品質之目的。
再次,要把握機會,在國際合作與國際文化交流中展示中國古典哲學的智慧。
當下國際間的交往愈來愈頻繁,我們要抓住每一個機會,宣揚我們的文化理念、哲學理念,展示東方古老的智慧。就政府層面而言,國家領導人的出訪即帶來傳播文化的契機,譬如,國家元首外訪時的講話③所秉持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理念,即彰顯出東方古老智慧的當代價值,至于講話中所引用的老子、孔子及其他古代經典文句,亦不在少數。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區區數百字訪談中,國家領導人便引用了韓非子、《詩經》、《老子》及唐代詩人李涉等經典著作,此從一側面向世界展現出古典哲學的智慧、厚重與博大。至于國際間的學術(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學人文學科的交流,有幸與會的學者則更應該抓住機遇,本著平等交流、共同提高的原則積極宣揚自己文化的特色。近百年來,伴隨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利及八國聯軍的入侵,國人曾一度失去了自信,認為“一切都是外來的好”,這導致了如下兩種心態:就積極意義上,我們能以開放的心態積極學習外來的優秀文化;就消極意義而言,則失去了民族自信、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正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經過近60年的建設,尤其是4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華民族在世界舞臺上有了自己應有的地位。在實現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的今天,中國人須昂起高貴的頭顱,不卑不亢地宣揚東方的智慧。須知,正如西方的科學屬于全人類一樣,東方的智慧雖為華夏民族所培育,然而它同樣是“共命慧”,屬于整個世界、屬于全人類。我們有義務來宣揚一種中正、圓融的智慧,使之為國際間存在的諸多問題提供可能性的思路和方案。
最后,抓住機遇,在人類所面臨的共同難題中展現中國古典的哲學智慧。
在具體的事務性活動中傳播古典哲學的智慧是非常有效的,因為這種事務性的活動具有“零距離”、“接觸時間長”等特點,譬如,隨著我國大型企業集團(如高鐵、天然氣管道等)日益走出國門,尤其隨著“一帶一路”策略的實施,我們可以在這個“新絲綢之路”中弘揚東方文化,讓更多國家的人民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分享東方古老的哲學智慧。當然,這需要高層管理人員具有一定的古典哲學修養。
當下,日益成為名副其實的“命運共同體”的人類面臨諸多共性的問題,如瘟疫問題、能源問題、氣候問題、生態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自然災害問題,等等。諸種問題的解決當然涉及到科學的謀劃與技術的參與,然而僅有科學和技術是不夠的,它需要有一個大系統、大地球觀的考量,要有大局觀和整體意識,要有系統思維和人文思想的參與,而這一點單靠西方的智慧是難以奏效的,它同時需要“中國智慧”的參與。事實上,在國與國關系的重大問題上,中國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的成員一直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也一直貢獻著古老的東方智慧。今后,我們更要發揮自己獨特的有機思維優勢、博大而包容的胸懷及尊重生命、尊重主權的“和”文化思維,在具體事務的解決中把東方獨特的經典文化與智慧貢獻于世人。
注釋:
① 一般而言,“特質”未必一定是精彩的,但對中國哲學而言,則大致如此。因為言其特質,乃至在中西比較的視野而言,沒有比較,何有特質?另者,中國哲學的特質恰恰凸顯了中國古典哲學的精彩,至少主體如此。
② 九種人分別為:自然人、活動人、理性人;藝術人、道德人、宗教人;高貴人、神性人、不可思議的神明境界人。其中,依次每三種為一層級,共三階,筆者稱之為“三階九層”。
③ 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的《弘揚絲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講稿中,引用了范曄、魏源及馮友蘭的經典文句;在《攜手合作,共同發展》的講話中,則引用了東晉葛洪《抱樸子》中的文句。
[參考文獻]
[1] 葉秀山.學與思的輪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2] 牟宗三.歷史哲學[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14.
[3] 徐復觀.徐復觀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601.
[4]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5.
[5] 傅永聚,韓鐘文.儒學與西方哲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3:150.
[6] 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自覺[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62.
[7] F·卡普拉.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8] 熊偉.在的澄明:熊偉文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責任編輯 文 格)
Abstract:As a philosophy of “loving wisdom”, it belongs to the human-being, so doe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n order to let Chinese philosophy go to the world and be accepted by the world, we must first do the basic work, that is, to study the wisdom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completely, then highlight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do the preparatory work.
Key words: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wisdom; Chinese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