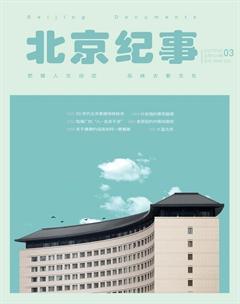茨維塔耶娃:俄羅斯白銀時代里程碑

白銀時代俄國再度出現“天才成群誕生”的壯觀景象,這是俄國的“文藝復興”,更是一個文學的時代,詩歌的時代。象征派的勃洛克和勃留索夫,阿克梅派的阿赫馬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未來派的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爾納克等相繼崛起,各領風騷。而唯一一位從未加入任何詩歌流派,卻又成為白銀時代最杰出詩歌代表的詩人,就是茨維塔耶娃,被布羅茨基稱為“20世紀的第一詩人”(布羅茨基、沃爾科夫:《布羅茨基談話錄》,馬海甸、劉文飛、陳方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47頁)。她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詩風就像一面鮮艷的旗幟,孤獨地飄揚在詩歌巔峰之上。
不合時宜的真誠和焦慮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МаринаЦветаева,1892--1941)的父親伊萬·茨維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學藝術學教授,是莫斯科美術博物館(今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的創建人;她的母親瑪麗婭·梅因具有波蘭、德國和捷克血統,曾隨著名鋼琴家魯賓施坦學習鋼琴演奏。由于身患肺結核病的母親需出國治療,童年的瑪麗娜和妹妹曾隨母親到過德、法、意等國的寄宿學校就讀,這使瑪麗娜·茨維塔耶娃自幼便熟練掌握了德語和法語。剛滿18歲的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詩集《黃昏紀念冊》(Вечернийальбом),詩集得到勃留索夫、古米廖夫、沃羅申等當時著名詩人的肯定,茨維塔耶娃從此走上詩壇。
可迎接茨維塔耶娃的卻是嚴酷的厄運:丈夫卷入蘇聯情報機構的暗殺行動被逮捕槍斃,女兒也坐牢15年,兒子犧牲在衛國戰場上,她自己在申請洗碗工遭拒后于租住的木屋中自縊。
在茨維塔耶娃自由、孤傲的個性中,積淀著這樣兩個基本的性格因素,即真誠和不安。她將“生活與存在”,當成她的詩歌創作中主要的思索對象,她思索苦難以及對于苦難的態度,思索詩人以及詩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思索愛以及愛的本質和意義。或是由于內心激情的涌動和生存狀態的刺激,或是關于個人命運和文化命運的擔憂,她的詩始終貫穿著一種不安的情緒主線。這種焦慮感的真誠表露,構成了她詩歌的主要風格特征之一。茨維塔耶娃的詩像是一種“獨白的詩”,是一個深刻體驗過多種生活的天才演員。茨維塔耶娃的詩中充滿隱喻,而且,她的一首詩、甚至是一部長詩,往往就是建立在一個大隱喻之上的,自身就是一個拉長的隱喻、組合的隱喻。
散文、戲劇和音樂的集合
茨維塔耶娃詩歌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他文學和藝術體裁的因素在她詩歌中的滲透。茨維塔耶娃的詩不論長短,都寫得十分酣暢,雖隨意卻不顯零亂,雖自然卻不失精致,帶有一種明顯的“散文風格”。布羅茨基在評論茨維塔耶娃的散文時曾說:“散文不過是她的詩歌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劉文飛譯,第137—138 頁)詩與散文的界限在她的創作中被淡化了,模糊化了。作為其結果,她的詩與散文均雙雙獲益。其次,是戲劇因素在茨維塔耶娃詩歌中的顯著作用。茨維塔耶娃的詩很有畫面感,而這些畫面又時常是流動的,就像是不斷變幻的戲劇舞臺。茨維塔耶娃同時是一位杰出的劇作家,在1918—1920 年間,她一度與瓦赫坦戈夫劇院等莫斯科的劇院關系密切,創作出一系列浪漫主義劇作;“詩劇”也一直是她心儀的文學體裁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詩作無論長短,往往都有著緊張的沖突、劇烈的突轉和激烈的對白,似乎稍加擴充,就會變成一部舞臺劇本。

《終結之詩》無疑就是男女主人公的一出對手戲,詩中不時出現兩位主人公的直接引語,就像劇本中的臺詞,而且,“這種對話酷似網球比賽,詞句像來回飛舞著的網球”。[ 斯洛寧(斯洛尼姆):《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浦立民、劉峰譯,毛信人校,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75 頁] 長詩中還多次出現被置于括號內的舞臺提示,如“(鷹一樣環顧四周)”“(斷頭臺和廣場)”等。廣義地說,《終結之詩》整部長詩就是兩位主人公的舞臺對白。此外,長詩中的舞臺“背景音”也此起彼伏,如汽笛、雷霆、笑聲、交談、手指的鼓點、耳朵的轟鳴、廠房聲音洪亮、紅色過道的嘩啦聲、空心的喧囂、鋸子穿透睡夢、腳掌的嘆息、接縫的崩裂、妓女的笑聲,等等。這些聲響與主人公簡短的對話形成呼應,也是長詩舞臺效果的重要來源之一,這使我們聯想到茨維塔耶娃說過的一句名言:“帕斯捷爾納克在詩中是看見,我在詩中是聽見。”(М.Цветае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семи томах, т. 6, с. 366.)最后,茨維塔耶娃的詩作又是高度音樂性的,曾自稱她繼承了母親對“音樂和詩”的愛好,這種“愛好”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她的篇幅較長的詩,多具有交響樂般的結構,具有呈示、發展和再現等不同階段;她的短詩則如歌曲,具有前文提及的濃烈的“歌唱性”。在俄語詩人中,茨維塔耶娃是最受作曲家青睞的詩人之一,肖斯塔科維奇等著名音樂家曾將她的許多詩作譜成歌曲,這并非偶然。
以詩歌背負“終結”的十字架
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創作在當年就引起了眾多女性讀者的共鳴和崇尚,在她以及阿赫馬托娃等女性詩人出現之后,一代又一代俄羅斯女性仿效她倆,拿起筆來寫詩。從此之后,女性聲音便成了俄國文學、尤其是俄語詩歌中一個水量豐沛的潮流,一種碩果累累的傳統。
茨維塔耶娃極具現代感的詩歌創作,構成了俄語詩歌發展進程中的一個路標。眾多大詩人在長詩寫作范式方面這種“不約而同”的嘗試,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索,而且,長詩體裁自身的這一變化也是與世界范圍內現代派詩歌的生成密切相關的。理解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茨維塔耶娃的《終結之詩》在世界詩歌發展史中顯明的“路標轉換”意味,而在整個俄語詩歌的發展過程中,茨維塔耶娃和她那個時代的許多大詩人一樣,也是從古典向現代轉向過程中的“里程碑”。
《終結之詩》也建立在一個巨大的隱喻之上。這部長詩共14章——這可不是一個偶然的數目,而是茨維塔耶娃有意為之的設計。這個初看上去并不具宗教含義的數字,實際上包含這一意義:它恰好是與十字架之路、即天主教傳統中苦路的14 個階段相呼應的。”( Т.Венцлова: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на пиру,Baltos Lankos, Vilnius, 1997, c.220)也就是說,茨維塔耶娃在詩中把她道別愛情的過程比作耶穌背負十字架的苦路。茨維塔耶娃曾這樣定義愛情:“愛情,就是受難。”(М.Цветаев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семи томах, Элис Лак, 1994, т. 6, с.609)也就是說,在她的意識中,愛情往往不是幸福、索取和生存,而是傷害、給予和毀滅。在俄語原文中,《終結之詩》這一標題中的“終結”(Конец)一詞是以大寫字母開頭的,這是在暗示我們,“終結”本身就是長詩中另一個隱在的主人公,它作為一個碩大的象征,構成“愛情苦路”這一整體隱喻的核心。這對戀人分手途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朝向“終結”的迫近,同時也是對“終結”的消解;“終結”既指愛情的終結,世俗生活的終結,甚至世界的終結,但“終結的終結”也意味著新的開端,亦即靈魂的凈化、愛的復活,乃至存在的無垠。
茨維塔耶娃的一生構成了20世紀俄國詩人悲劇命運的一個象征……她似乎在用她真實的生活際遇,圖解她自己給出的一個關于詩人和詩歌創作的定義:詩人就是猶太人,就是永遠被逐的人;寫詩就是殉道,就是一種受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