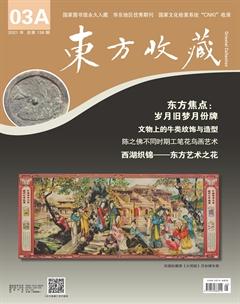古人的“存錢罐”與“保險柜”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屬鑄幣的國家。文獻記載以及考古發現的古代錢幣儲藏器具多種多樣,漢代陶撲滿和綠釉陶錢柜就是目前所見的遺留下來且為數不多的古代錢幣儲存器具。
1.撲滿
我國古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流通的貨幣是“天圓地方”的圓形方孔錢,人們為了方便存儲,便用陶作一個瓦罐,在瓦罐上開一個能放進銅錢的長方形孔,平常將散銅錢投入其中,需用錢或罐裝滿之后,摔破罐子將錢取出。這種我國古代人民日常儲蓄錢的陶器就叫做撲滿,通俗的講就是存錢罐。以撲滿儲錢流傳久遠,直到今天不少兒童還用它存錢。如今的存錢罐以豐富的造型、多彩的顏色深受小朋友的喜愛,對兒童養成良好理財習慣大有裨益。
關于“撲滿”一詞的由來,據《西京雜記》記載:“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這里面有一個撲滿背后的故事,漢武帝時的丞相公孫弘,年少時家中貧寒,曾放過豬,當過獄吏,但他刻苦向學,孜孜不倦,近70歲時入九卿之列,74歲升為丞相。早年在他被推舉為賢良方正時,因家境貧寒,沒有像樣的衣著赴京,他的同鄉鄒長倩便脫下自己的衣裳和鞋子送給他。還送給他生芻(青草)一束,意為雖極其貧賤,但不能失君子之度,勿以貧賤而自卑;贈青絲一襚,意為任何事物都是積少成多,勿以惡小而為之,讓他多做好事,以建立功業;贈撲滿一個,讓他知道一味聚斂錢財,最終只能像撲滿一樣得到破敗的結局。公孫弘謹記朋友三件禮物的用意,在為官期間,保持勤儉的本色,多余的錢財用來招納賢才。他奮發努力,最終立功揚名,成為一代名相。
撲滿因其特殊的形制和用途,經常出現在歷代文人墨客的筆下,其特殊的寓意為人所借鑒,成為節儉、清廉的象征。唐末高僧詩人齊己在《撲滿子》一詩中寫道:“只愛滿我腹,爭如滿害身。到頭須撲破,卻散與他人。”唐代名相姚崇曾寫過《撲滿賦》用于批判金錢,批判貪婪以及自滿的惡習,告誡自己的后代做人和為官之道。他寫道:“謙以自守,虛而能受。”以撲滿的特點來傳達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宋代詩人范成大在《催租行》中有這樣的詩句:“床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慳囊即為撲滿,這樣的詩句讓人充分體會到底層人民的困苦。宋代陸游以撲滿設喻:“錢能禍撲滿,酒不負鴟夷。”說明過度斂財必招災禍。明代語錄集《菜根譚》中以“欹器以滿覆,撲滿以空全”來比喻做人的道理。詩句中撲滿的形象既增添濃郁的生活氣息,又被引申出新的含義。不僅如此,直到現代社會,我國還曾經在儲蓄存折上使用“撲滿”樣式的儲徽,圖案中的“撲滿”上有很清晰的投幣口。
目前考古所見的撲滿中最早為漢代,但據文獻記載撲滿在秦始皇時期已存在。根據出土竹簡《云夢秦簡·關市》中記,商販在市場上經營所收的錢必須經人監督投入特制的“錢缿”中,集市結束后將所收錢幣倒出,官吏進行統計收稅。這里的錢缿是為管理市場而設的,只做盛錢用,但它已經具有儲錢器的形式了,是撲滿的雛形。
西漢至魏晉時期,撲滿被人們作為存錢罐來使用,并逐漸發展成熟。這一時期的撲滿既有文獻記載,又有考古實物可見。洛陽燒溝漢墓出土一饅頭形撲滿,高13.5、腹徑14厘米,泥質灰陶,弧頂,下部內收,平底;頂部有一橫條形窄長孔,器身還有一不規則的破口,外壁和底部均有明顯的輪制痕跡,撲滿內蓄有20枚五銖錢。在廣州漢墓還發現過陶撲滿,高11.6、底徑14.8厘米,形狀像扁圓的罐,束頸,溜肩,大腹渾圓,平底;且有雙耳,腹上方有一長方形豎孔,出土時器內也貯有五銖錢20枚。
依據這兩個撲滿出土時器內貯藏有五銖錢的情況來推斷,撲滿在當時定是作為儲錢器使用的。器物頂部的長條形孔為投幣孔,器身不規則的破口應為取錢時鑿的,因不想將撲滿徹底打碎,所以鑿個小洞,這樣即使取出錢幣,器身仍較完整,還可以再用。從考古出土的撲滿來看,這樣的做法屢見不鮮。
下面是三門峽市博物館館藏的兩個漢代陶撲滿,其中一件器身也有不規則破洞。
漢代陶撲滿(圖1),高16、底徑7.9厘米,重570克。泥質灰陶,呈球狀,上部圓鼓,下腹急劇內收,平底;外壁和底部均有明顯的輪制痕跡,頂部開一橫條形窄長口。腹部殘,已修復。
漢代陶撲滿(圖2),高16.3、底徑7.1厘米,重590克。這一件器型稍高,泥質灰陶,似蘑菇形,上部微鼓,腹較深,平底;外壁和底部均有明顯的輪制痕跡,頂部開一橫條形窄長口,下腹部有一圓孔,底部有一不規則破口。完整。
撲滿到漢代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這兩件陶撲滿都是上部圓鼓,下腹內收,平底;造型簡樸且不帶任何裝飾,外壁較粗糙,制作工藝較差,具有漢代陶撲滿的普遍特征。因為其陶質的形制和“滿則撲之”的用法,大多數撲滿已被人為破壞,目前所見的較完整的實物寥寥無幾。同時,因其本身不曾為人所知,得不到重視,故而其埋藏狀況被人忽視,對撲滿的各項研究也就十分困難。僅少數撲滿中稀稀拉拉的古幣聲響,在向我們訴說著它曾經的故事。
2.錢柜
柜,古作匱或櫃,是一種貯藏物品的家具,通常為長方體狀,有蓋或門。《舊唐書·王叔文傳》中有關于柜的形狀的記載,“室中為無門大柜,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藏金寶。”史書中有柜可藏金錢的記載,《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死時“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唐代時有一種經營貴重物品與錢幣存放和借貸的機構,稱為柜坊,“柜坊”這一名稱就是由盛錢的箱柜演變而來的。
由此可見,錢柜也是古代一種重要的錢幣儲藏器具,下面來看一看三門峽市博物館館藏的一件漢代綠釉陶錢柜。
漢代綠釉陶錢柜(圖3),1993年出土于三門峽市蘭盾房屋開發公司工地;高21、長27.1、寬21.5厘米;臥箱形,整體呈長方體狀,由陶板黏合而成,下承柱形立腿四條;柜頂部有可活動的方形門,柜頂部飾十五個錢紋,柜正面飾二十個錢紋,錢紋均呈規律性分布,正面有方形鎖,鎖眼鎖芯清晰可見。紅陶胎,施綠釉,底部及內部無釉。兩后腿殘缺,已修復。該器物是漢代木質錢柜的模型,為明器。
除此件錢柜外,筆者在整理資料時還發現兩件漢代綠釉陶錢柜,其中一件出土于西安市曲江雁鳴小區漢墓,現藏于秦二世陵博物館,在該館曲江新區出土文物展覽館展出;另外一件藏于日本愛知縣陶瓷資料館。
西安曲江出土的這件錢柜(圖4),通高21.5、長33.3、寬20厘米。這件錢柜在這三件中體形最大,出土時破碎嚴重,后經修復。紅陶胎,表面綠釉普遍剝落,且柜內無釉。日本愛知縣陶瓷資料館所藏的綠釉錢柜(圖5),也為綠釉紅陶胎,錢柜通高15、長24、寬20.5厘米,在三件錢柜中體形最小。
對比發現,這三件錢柜形制十分相似,均為臥柜且有四足,均以錢紋為裝飾,柜頂都有柜門。但不同之處更值得人們關注。先看做工,圖4做工最為粗糙,細節刻畫也最少;再看三者的錢紋,圖4只有正面有錢紋,而圖3和圖5正面和頂面都有,圖3錢紋最多且最清晰,圖4錢紋模糊不清,圖5的錢紋弱化,用泥質小圓點代替,但多了模擬金屬泡釘的裝飾;圖3 的鎖最為精致,圖4沒有鎖合結構,圖5的鎖跟圖3中的鎖也不相同;最后看四足,圖4足最小且沒有裝飾,圖3和圖5柜足較大,造型類似,且都以線條裝飾,圖5裝飾得更為自然。通過對比,就這三件陶錢柜出現時間早晚而言,筆者認為,圖4最早,圖3承前啟后,圖5最晚。
這三件漢代綠釉陶錢柜,造型端莊大氣,裝飾巧妙且隨時代發展而富于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漢代日常生活用具獨特的一類。
漢代陶撲滿和綠釉陶錢柜就作為我國古代錢幣儲存器具,不僅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和人們貯藏錢財的方法,也教會我們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君子雖愛財,取之要有度。古人的“存錢罐”與“保險柜”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實物,更是古代匠人高超的技藝和其中蘊含的古人無盡的智慧(圖4、圖5來源于網絡)。
(作者簡介:狄欣怡,女,漢族,河南三門峽,本科。工作單位:三門峽市博物館,助理館員,研究方向:文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