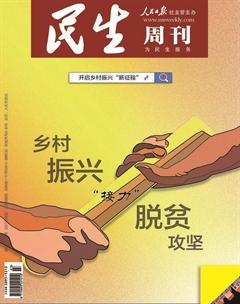守住脫貧成果 嚴防規模性返貧
王迪
2020年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之后,2021年“三農”工作重心全面轉向鄉村振興。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堅決守住脫貧攻堅成果,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張琦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之間有怎樣的關系?如何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現象發生?怎樣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近日,本刊記者專訪了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張琦教授。
民生周刊:2015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5年后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我國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您認為如何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現象發生?如何建立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
張琦:反貧困的長期性和持久性特征決定了扶貧工作并非一勞永逸,區域性貧困的解決與貧困縣全部摘帽也并不意味著扶貧工作的徹底終結。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部分地區脫貧質量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可持續脫貧任重而道遠。
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這一中國農村扶貧的主要方式是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的根本保證。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階段要繼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精準”思想,完善頂層設計,通過精準識別鞏固拓展對象、精準把握返貧原因、精準制定鞏固拓展措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規模性返貧。
構建緩解相對貧困長效機制應該在以下幾方面發力:一要進一步補齊“兩不愁三保障”的短板,大面積消除各類致貧因素;二要強化兜底保障體系,筑牢持續脫貧防線,從源頭上筑起絕對貧困的“截流閘”;三要促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全面提升,補齊欠發達地區的短板,爭取實現均等化;四要提升相對貧困地區和相對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達到逐步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的目標;五要構建和培育脫貧內生動力機制,提升相對貧困人群和落后地區的發展動力和活力;六要創新綠色減貧舉措,實現生態保護和脫貧致富雙贏。
民生周刊:目前,我國脫貧攻堅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鄉村振興進入了探索階段。您認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之間有怎樣的關系?
張琦: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戰略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一方面,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戰略存在耦合和交叉。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是圍繞“三農”問題而提出的重大決策,兩者在內容和范圍上耦合度較高。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內容包括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繁榮鄉村文化、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推進鄉村綠色發展、提高農村民生保障水平等,這些內容與脫貧攻堅強調的產業扶貧、文化扶貧、黨建扶貧、生態扶貧和社會保障兜底扶貧等方式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脫貧攻堅戰與鄉村振興戰略存在差異和不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不同點在于脫貧攻堅具有特殊性、局部性、緊迫性和突擊性的特點;而鄉村振興則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漸進性和持久性的特點。脫貧攻堅目標是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地區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消滅絕對貧困;而鄉村振興戰略則著眼于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實現農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民生周刊:那么,您認為如何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張琦:我主要提以下六點想法。第一,脫貧工作應該一以貫之,在脫貧攻堅結束后,給予脫貧地區和脫貧人口一個政策穩定期和過渡期,保持政策穩定。第二,建立防止返貧的監測和幫扶機制,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要建成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第三,做好“兩不愁三保障”,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使脫貧攻堅成果具有可持續性。第四,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后續工作。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易地扶貧搬遷是否成功關鍵在于后續,后續的扶持、就業、生活都需要做好。第五,產業發展是增強貧困地區造血功能的重要途徑,是脫貧致富的根本。要做好扶貧資產,扶貧縣的資產管理,后續使它保值增值。第六,保證財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政策和制度的有效銜接,是穩步拓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非常重要的內容,比如財政政策要基本穩定,以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啟動鄉村振興提供非常重要的資金保證。
民生周刊:鄉村振興之路會很長,未來鄉村振興到底怎么實施?比如要不要派鄉村振興工作隊?針對農村和城市不同環境,如何有針對性實施農村社會治理?
張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積極落實好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的七個方面的任務,即要加快發展鄉村產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深化農村改革、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見實效、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這些要求指導性很強,含金量很高。
鄉村振興階段設立鄉村振興工作隊還是有必要的。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了,駐村工作隊在帶動落后地區經濟發展、貧困人口脫貧、轉變基層工作作風等方面,作用十分明顯。而鄉村振興任務更加艱巨,在時間周期上也更為久遠,因此,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對發展資源的長期性需要也更加迫切。
當然,還有東西協作、定點幫扶等方式。實踐證明,近幾年這種“幫扶”制度,對當地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對幫助對象資金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精神、理念、思想的傳遞。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幫扶,建立起來的某種“內在聯系”。比如,駐扎在全國各地的幫扶干部,其對所幫扶的村子、村民,是有感情的。兩年的駐村時間,他們腦子里往往想的都是如何幫助當地村民增加收入、如何帶領鄉親們擺脫貧困,這種傾注心血的感情,是非常濃厚的。而對于村民而言,誰幫扶的他們,村民們也會心存感激,因此,這種情況下建立起的感情,是非常牢固的。對于幫扶干部而言,自身也得到鍛煉。大到產業發展、小到家庭糾紛,幫扶干部都得親力親為,從而提升其解決復雜疑難問題等多方面能力。
因此,這種幫扶方式,在完成脫貧攻堅重任的同時,又鍛煉出一批年輕干部。鄉村振興作為國家重點戰略規劃之一,時間上比脫貧攻堅更加長遠,這種將年輕干部派往一線崗位進行歷練的模式可以繼續延伸,但需根據鄉村振興戰略,適時進行調整、優化。
針對農村社會治理問題,和城市不同,農村是血緣社會、人情社會,村民間沾親帶故,難以像城市那樣基本以法治來確定權利和義務分配。有效實施農村社會治理,必須實現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充分發掘鄉村原有的鄉規民約、習慣風俗,發揮“新鄉賢”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作用,以自治激發民主活力,以法治推進現代治理,以德治滌蕩文明鄉風。
民生周刊:在您看來,“十四五”期間,振興鄉村、治理相對貧困面臨的現實基礎、難點和薄弱環節是什么?
張琦:這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治理相對貧困仍舊面臨脫貧“不充分”的問題。在“三保障”方面,貧困地區特別是一些深度貧困地區,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和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尚未實現全面均等化,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障礙。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方面,農業產業結構比較單一,產業融合帶動能力不足,難以提高綜合效益。農村普遍缺乏具有帶動作用的農村現代實用人才,以致對發展農村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不明顯。
其次,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治理相對貧困仍舊面臨脫貧“不平衡”問題。就GDP總量而言,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差距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在農村人口中出現了扶貧政策“福利懸崖”效應。隨著大量優惠政策向貧困戶傾斜,貧困戶享受的政策紅利越來越多,造成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的心理不平衡。
最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治理相對貧困仍舊受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影響。一方面,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財政資金投入緊張。另一方面,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大,貧困地區的產業就業等方面約束性增強。在我國經濟運行壓力較大和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貧困地區的產業和就業必將面臨較大的壓力,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治理相對貧困形成挑戰。
展望未來,農村在促進我國經濟“內循環”方面大有可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蘊藏的巨大潛力尚未發揮出來,隨著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果,“鄉村建設行動”的進一步實施,農村城鎮化水平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也將隨之提升,農村消費市場可謂是前景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