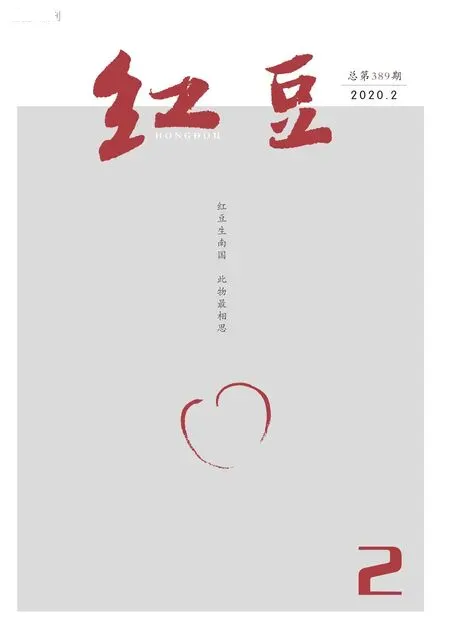聶鑫森微篇小說(shuō)二題
聶鑫森,湖南湘潭人。畢業(yè)于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中央文學(xué)講習(xí)所第八期和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作家班,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曾任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名譽(yù)主席。出版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集、中篇小說(shuō)集、短篇小說(shuō)集、小小說(shuō)集、詩(shī)歌集、散文集、隨筆集、學(xué)術(shù)專(zhuān)著等六十余部。曾獲莊重文文學(xué)獎(jiǎng)、湖南文藝獎(jiǎng)、毛澤東文學(xué)獎(jiǎng)、《小說(shuō)月報(bào)》百花獎(jiǎng)、《北京文學(xué)》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
繡球花
入夏,曲曲巷管家院子里的繡球花熱熱鬧鬧地開(kāi)放了。真的很好看,白、綠、紅、紫、藍(lán),花朵又飽滿又圓碩,仿佛無(wú)數(shù)的手舉著繡球,隨時(shí)準(zhǔn)備拋擲出去。
管家的院門(mén)也是虛掩的,誰(shuí)想來(lái)看,推開(kāi)門(mén)就可進(jìn)去。院子很寬敞,栽種的幾乎都是繡球花,高株和矮生的錯(cuò)雜為鄰。品種有本地的大雪球、大八仙花,也有來(lái)自日本的恩齊安多姆、奧塔克薩。來(lái)看花的街坊鄰居,總要豎起大拇指說(shuō):“花開(kāi)得這樣好,管爺有好手段,也有好心境!”
管爺退休前是湘山公園的花木技師。他什么花都會(huì)侍弄,但最有體會(huì)和靈性的是侍弄繡球花。湘山公園的繡球花引得游客紛紛買(mǎi)票前來(lái)觀賞。報(bào)紙上有個(gè)新聞標(biāo)題“誰(shuí)擲繡球光色影,滿城爭(zhēng)說(shuō)管鋤畦”最為讀者傳誦。管爺說(shuō):“過(guò)獎(jiǎng)了,是我和同事們一起干的,怎么都算到我身上?將來(lái)退休了,我最想侍弄的還是繡球花。讓想看的人看個(gè)夠。”
果然如此。這個(gè)夏天,繡球花開(kāi)得特別喜氣。管爺和妻子袁瑛正在給花澆水。天天來(lái)看花的是楊金,而且是華燈初上。楊金說(shuō):“管爺,袁嬸,吃過(guò)晚飯了?我爹讓我問(wèn)你們好哩。”管爺說(shuō):“謝謝。你看中哪朵花?我們來(lái)給你剪下。”管爺夫婦很喜歡楊金,模樣文靜,學(xué)問(wèn)也不錯(cuò),三十二歲就當(dāng)上了環(huán)保研究所的副所長(zhǎng)。楊家也住在曲曲巷。“今天我想求一朵粉紅色的繡球花。”楊金說(shuō)。袁瑛說(shuō):“你應(yīng)該是有女朋友了,好事呵。不能老當(dāng)快樂(lè)的剩男,你爹媽都急得上火了哩。”楊金的臉熱得發(fā)燒,結(jié)結(jié)巴巴地說(shuō):“我……只是……一廂情愿……人家……還沒(méi)點(diǎn)頭。”管爺說(shuō):“袁瑛,你話多了。快去剪朵花來(lái),別誤了孩子的大事。”“對(duì)、對(duì)、對(duì)!”袁瑛接話道。
楊金拿著一枝粉紅色的繡球花,興沖沖地走了。
管爺說(shuō):“你說(shuō)楊金是剩男,我那在深圳工作的女兒比楊金還大一歲,不也是剩女?”
袁瑛長(zhǎng)長(zhǎng)地嘆了一口氣。
管爺說(shuō):“我退休后栽了一院子繡球花,當(dāng)然是我多年的愛(ài)好,其實(shí)也有我的祈愿:哪個(gè)小伙子能給女兒拋個(gè)繡球,或者女兒也給看中的人拋個(gè)繡球。”“我……明白。”袁瑛應(yīng)道。
一個(gè)星期天的早晨,才七點(diǎn)多鐘,一個(gè)個(gè)子高挑的姑娘推開(kāi)管家的院門(mén)走了進(jìn)來(lái),然后又順手把門(mén)關(guān)上了。管爺剛給花澆完水,正坐在一個(gè)石鼓凳上歇息。
姑娘走到他面前說(shuō):“你是管伯伯吧?我叫徐嚴(yán),是中學(xué)老師。我來(lái)看看你種的繡球花。”
“啊,歡迎。姑娘,你好像是第一次來(lái)?”
“可我聽(tīng)楊金多次說(shuō)起你。”
管爺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說(shuō):“楊金是我看著長(zhǎng)大的,好角色啊,對(duì)人有禮貌,工作又發(fā)狠,你的眼光不俗。”
姑娘淺淺一笑,問(wèn):“他一連送了我三十次繡球花,都是從你這里求的?”
“我的花原本就不賣(mài)錢(qián),供大家看,也免費(fèi)相贈(zèng)。”
“那是管伯伯的雅懷。楊金求花一次兩次說(shuō)得過(guò)去,持久不斷地求花,做人就有毛病了。花店里不是沒(méi)有繡球花賣(mài),他舍不得花錢(qián);花是給大家看的,都像楊金這樣求花,花只能屢遭殺伐,悲何以堪!”
“姑娘,楊金求幾朵花,小事呀,不足掛齒。其實(shí),你也不必這樣苛求他。”
“小處見(jiàn)心性、見(jiàn)格調(diào)。管伯伯,花是楊金求的,但我必須來(lái)表示謝意。再見(jiàn)!”
管爺還沒(méi)回過(guò)神來(lái),徐嚴(yán)的背影已閃出院門(mén)外,她輕輕地關(guān)上院門(mén)。
在這一刻,管爺想起了女兒,只怕也是這樣的人物。
太陽(yáng)升高了,滿院子金屑亂飛。各種顏色的繡球花,抹上了一層金黃的光影,在等待著脫手而出的機(jī)緣。
管爺?shù)难劾锖鋈挥辛藴I水。
故鄉(xiāng)的味道
阿根夫婦覺(jué)得故鄉(xiāng)的味道離他們?cè)絹?lái)越遠(yuǎn)。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故鄉(xiāng)的味道就是湯面的味道。
蘇州人早晨講究“皮包水”,喝早茶兼吃早點(diǎn)。蘇州人的“皮包水”是吃一碗湯面。蘇州人常說(shuō),聽(tīng)?wèi)蛞?tīng)腔,吃面要吃湯。蘇州湯面的妙處,都在湯里!
蘇州的湯面,哪一種都好吃,只有清湯光面最便宜。阿根夫婦喜歡把清湯光面當(dāng)作早餐。獨(dú)生子在身邊時(shí),一家三口來(lái)吃。兒子上大學(xué)了,后來(lái)又到外地工作,他們就找個(gè)座面對(duì)面地吃。街坊鄰居打趣說(shuō):“你們也該換換口味,吃吃別的湯面。”阿根說(shuō):“別的湯面我們也吃過(guò),還是清湯光面最合口味。”
阿根夫婦曾是蘇州一家國(guó)營(yíng)企業(yè)的工人,工資不高,得節(jié)約著用,兒子讀書(shū)要花錢(qián),將來(lái)結(jié)婚買(mǎi)房更要花錢(qián),除每月正常開(kāi)支外,剩下的錢(qián)都要存起來(lái)。九年前,兒子大學(xué)畢業(yè)了,女朋友是同班同學(xué),雙雙到湘潭的高新開(kāi)發(fā)區(qū)打拼事業(yè)。第二年兒子準(zhǔn)備結(jié)婚,要買(mǎi)一套房子,阿根高高興興匯過(guò)去三十萬(wàn)元存款,幫交了首付。小兩口結(jié)婚不到一年,孩子呱呱落地。兒媳的娘家是湘潭鄉(xiāng)下的,親家母可以來(lái)幫忙。等到孫子上小學(xué)了,阿根夫婦正好退休,親家母也說(shuō)該回鄉(xiāng)下去了。孫子讀書(shū)的小學(xué)離家遠(yuǎn),得有人接送,阿根夫婦立刻趕來(lái)走馬上任。
阿根夫婦住進(jìn)湘潭城中的這個(gè)社區(qū)。一年了,他們?nèi)松夭皇欤K州話不好懂,湘潭話也聽(tīng)不明白,沒(méi)法和人溝通。但兒子孝順、兒媳賢惠、孫子聰明,這就很稱心了。他們起得早,冰箱里有備好的早點(diǎn),蒸熱就行,再做個(gè)湯,簡(jiǎn)單。然后阿根夫婦送孫子去學(xué)校。中午,兒子、兒媳在單位的食堂用餐,孫子也在學(xué)校吃飯,他們隨便炒個(gè)菜、做個(gè)湯,扒幾口飯就飽了。下午四點(diǎn)鐘,阿根去學(xué)校接孫子;妻子在家擇菜、洗菜、切菜,準(zhǔn)備晚餐。兒媳很能干、心也細(xì),也沒(méi)讓老人下廚房,她先炒了兩道不放辣椒的菜,再炒了一道辣的菜,廚房里有抽風(fēng)機(jī),門(mén)也關(guān)緊了,但辣椒的辛辣氣味仍絲絲縷縷擠進(jìn)客廳,嗆得阿根夫婦一個(gè)勁兒地咳嗽。他們很驚奇,兒子吃菜竟不怕辣了,孫子才七歲,吃辣菜眉頭也都不皺一下。
家里只剩下阿根和妻子時(shí),又沒(méi)什么事可做,要不看電視,要不就呆坐著說(shuō)閑話。
“阿根,這里的空氣都飄著辣味,炒菜的鐵鍋?zhàn)右怖蔽度肓斯牵匆蚕床粌簟!?/p>
“我們有老年乘車(chē)優(yōu)惠卡,沒(méi)事時(shí)去坐公交車(chē),下車(chē)后去大街小巷走走,未必沒(méi)有賣(mài)清湯光面的地方。”
“對(duì)呀。”
一天中午,他們真的在城東的一條小街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叫“老蘇州”的湯面店。門(mén)面不大,店堂也不寬敞,墻上掛著介紹品種的圖畫(huà),其中就有清湯光面,配圖文字說(shuō):“湯底用整只老母雞、火腿、老鴨架、瑤柱同煮,連吊三天三夜,湯色要三白三清,到了最后一道清湯,把牛肉、雞胸敲成膩?zhàn)樱脺休p輕攪拌,用膩?zhàn)游{所有的油脂雜質(zhì),只剩下純凈的清湯,用它和面、煮面。”
阿根用蘇州話喊一聲:“請(qǐng)來(lái)兩碗清湯光面!”
馬上有人用蘇州話應(yīng)諾:“好咧——”
妻子小聲對(duì)阿根說(shuō):“每碗二十元哩。”
“家鄉(xiāng)的味道,還能當(dāng)中餐,值。”
店堂里顧客不多,很安靜。
白白柔柔的面條上,撒了幾點(diǎn)翠綠的蔥花。他們先喝了一口湯,再用筷子夾起面條送進(jìn)嘴里。久別的故鄉(xiāng)的味道,驀地在舌尖上爆開(kāi),鮮得讓他們掉下淚來(lái)。
阿根夫婦不可能天天來(lái)吃清湯面,一個(gè)星期吃一次就夠了。二十元一碗的清湯面,阿根夫婦覺(jué)得有點(diǎn)貴,貴也得吃,吃了就覺(jué)得故鄉(xiāng)還貼在心口上!
幾個(gè)月飛快地過(guò)去。
一天上午,阿根夫婦再去“老蘇州”時(shí),店門(mén)沒(méi)開(kāi),招牌也不見(jiàn)了。問(wèn)旁邊的人是怎么回事。回答說(shuō):“這玩意兒沒(méi)有辣椒味,湖南人不愛(ài)吃,老板收拾行頭回蘇州去了。”
他們懶懶地回到家中,肚子空空的,卻什么也不想吃……
責(zé)任編輯? ?練彩利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