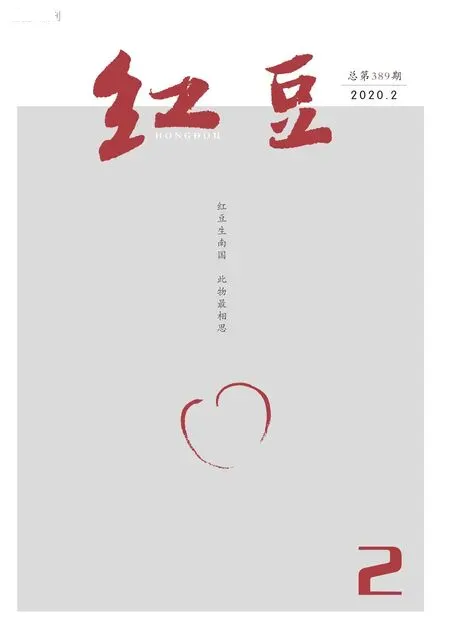作家粉店
潘立宇,1993年生,壯族,廣西南寧市人。曾任報(bào)社記者,業(yè)余時(shí)間喜愛讀書與寫作。散文作品《左江悠悠,花山依舊》獲2016年廣西新聞獎(jiǎng)(副刊作品)二等獎(jiǎng),曾參與撰寫《老南寧記憶》。
大四的最后一個(gè)學(xué)期,我在家待業(yè)。綠城那年的冬天特別長(zhǎng),開春以后,我偶爾會(huì)在飯后下樓走走。獨(dú)自一人散步的我,沒有選擇小時(shí)候和父母散步常走的廣場(chǎng)。我趁著一個(gè)人的時(shí)候,開辟了一條新路線,沿著明秀路、北湖路、衡陽(yáng)路、友愛路圍成的方形走。地鐵工地封閉施工,將生活圈硬生生劃成了兩半,那里不是不能走人,而是你感覺不到生活的氣息。于是我再一次走進(jìn)了那條橫穿過明秀路與衡陽(yáng)路的小巷——衡秀里,那條從我的童年橫亙到如今的小巷。那里很多店面都不知換了多少次門臉,但我欣喜地發(fā)現(xiàn),童年第一次搬家后住的院子還在,接受啟蒙教育的幼兒園也還在。
散步路過的時(shí)候,我偶爾會(huì)透過鐵柵欄門向里邊望望,看看有沒有明顯的變化。也許是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角度,每次張望時(shí)總覺得變化很大。幼兒園與住宅區(qū)小門之間有數(shù)間店鋪,其中有一間,便是那個(gè)熟悉的坐標(biāo)。路過抬頭一看,還是它,那個(gè)熟悉的名字“作家粉店”。
“作家”兩個(gè)字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憶,勾起了我與它的生命連結(jié)。童年關(guān)于它的記憶已經(jīng)只剩下模糊的一點(diǎn),仿佛除了名字,已經(jīng)絲毫想不起它的其他部分。我努力地回想,味道永遠(yuǎn)是銘刻在腦海深處最不容易忘記的東西。記憶中我是在這吃到的第一碗桂林米粉,我還依稀能觸摸到那種朦朧的印象,應(yīng)該是在那吃的。那也許是我第一次嘗試桂林米粉不加湯直接干拌著佐料吃,學(xué)習(xí)如何做一個(gè)廣西人。對(duì)于生長(zhǎng)在南寧這片土地的我,米粉也一定會(huì)和我結(jié)下一輩子的緣分,不算上全然記憶模糊的幼年時(shí)期,那應(yīng)該是記憶中真真切切的第一次。記憶中去這家店吃米粉大都是早餐時(shí)間,是母親早上送我去幼兒園帶我吃的。我很真切地記得,這家店應(yīng)該是父親帶我去的,因?yàn)槟菚r(shí)的母親是一個(gè)全能的家庭主婦,她應(yīng)該是一直有自己做早餐給我吃的習(xí)慣。
那時(shí)的父親是一個(gè)不會(huì)做菜、懷揣著作家夢(mèng)想、剛調(diào)入南寧工作的媒體人,所以周末他經(jīng)常帶我去這個(gè)于他來說很有意味的地方,既填飽肚子,又以一種特有的方式給予他某種心理暗示。這家粉店或許就以它獨(dú)特的名字吸引了父親,從而在我的童年里留下不長(zhǎng)但卻無法忘卻的光影。
作家粉店這名字著實(shí)值得人玩味,那時(shí)我不知作家為何物,年紀(jì)稍長(zhǎng)后也只道是店主為附庸風(fēng)雅隨意而起的店名。現(xiàn)如今總是以純粹、地道的文科生自命的我,不假思索也能說出一些作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風(fēng)雅韻事。想想若是他們中的某位真的來到這店里吃粉,必是文學(xué)史上之趣事。
我想假如詩(shī)仙李白來這吃粉,或許會(huì)說,老板,這米粉不錯(cuò)。不過……掌柜的,這有酒嗎?給我拿上來,我吃飽喝足了要給你題一首贊美米粉的詩(shī)。隨園先生袁枚來這吃粉,或許會(huì)評(píng)論道,這米粉細(xì)膩爽口,我要將它收入《隨園食單》,不知掌柜能否容許我打包一份,讓我之后細(xì)細(xì)研究啊!大文豪托爾斯泰來這吃粉,或許會(huì)想,世上居然還有位辛勞開店自給自足的作家,他雖沒有高貴的出身,但他一定是精神上的貴族!然后捋著胡子,眼神誠(chéng)懇地對(duì)老板說,先生,我能和您一起勞動(dòng)嗎?您也教教我如何做米粉吧。
那天晚上米粉店已經(jīng)關(guān)門,我沒有能走進(jìn)去。但我猜想,那墻上的價(jià)目表,應(yīng)該也從曾經(jīng)兩三元一碗變成如今十多元一碗。當(dāng)年若有一部隨手能拍照的手機(jī),拍下一張,與如今的米粉價(jià)格表對(duì)照,不失為南寧市餐飲業(yè)發(fā)展和居民日常消費(fèi)增長(zhǎng)的生動(dòng)史料,甚至能算得上是廣西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局部縮影。小巷左方不到百米的路口,建設(shè)地鐵的工地晝夜不停地施工,未來它將通向城市的另一端。右方不到百米的街角,一幢幢大樓又深又廣的地基已見雛形,它一定會(huì)建成數(shù)十層的大廈。在南寧我知道有許多比作家粉店還要老的粉店,但無形中它與我的緣分最深,悄無聲息地融入我的記憶中。
在一次和父親的閑聊中,我得知了店名的真實(shí)來歷。粉店的初創(chuàng)者是一位本地的文壇前輩,一九九八年他開米粉店是為了貼補(bǔ)生活,支撐自己的寫作夢(mèng)想。二〇一八年在和朋友偶然談?wù)撝校視r(shí)常能聽到這樣的內(nèi)容:聽說現(xiàn)在粉店開得都很火,咱幾個(gè)朋友加盟一個(gè)品牌店,或者合力經(jīng)營(yíng)一家應(yīng)該能賺不少錢。
我們走過的時(shí)光不止二十年,更像是兩個(gè)截然不同的時(shí)代。現(xiàn)在的我們還有多少人有勇氣大聲宣示自己的理想,將理想置于生活之上,為一家米粉店起名叫作家粉店?
那店名里無限的溫情與理想的火熱,融入毫無設(shè)計(jì)的招牌,讓我仿佛看到一個(gè)披著生活平淡外衣,卻仍將理想高舉過頭頂?shù)娜恕_@普普通通的招牌無言地述說著那一代知識(shí)分子的辛酸故事與歲月榮光。我反復(fù)打量、琢磨著這平淡無奇的招牌,感到詞窮,心頭一次次被一股難以名狀的感動(dòng)沖撞,被這墜入塵世卻仍熠熠生輝的光芒折服。
責(zé)任編輯? ?謝?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