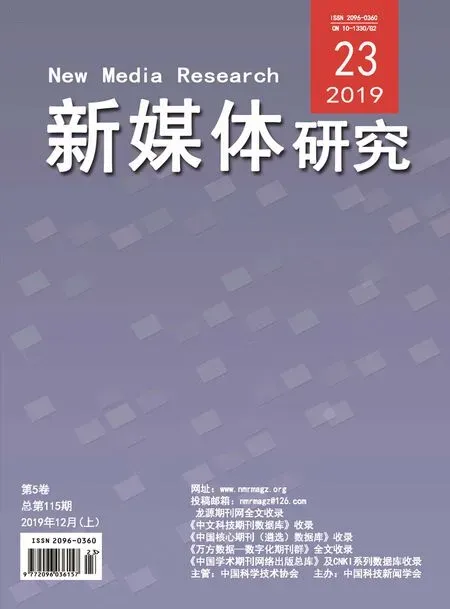微博超級話題中的“擬熟人”交流現象研究
臺曉霞
摘 要 傳統中國的人際關系建立在血緣、地緣、業緣的基礎上,互聯網時代以趣緣為紐帶出現的社交群體拓展、補充了傳統人際關系的維度。有著強大流量聚集地的微博超話作為趣緣群體的一大代表“基地”,用戶之間的互動及其社會關系十分復雜。超話內的用戶本應該是陌生人,在超話中的交流話語和狀態卻猶如熟人間親密。文章提出“擬熟人”的交流現象,從強弱關系理論入手,通過對超話社區的參與觀察來研究趣緣群體中“擬熟人”現象的表現、信任機制及其影響,發現以陌生人交流為主的趣緣群體也能建立強關系。
關鍵詞 超級話題;強弱關系;用戶關系;信任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23-0089-04
互聯網產生后,用戶間的互動交往成為社會關系結構重要的一部分。各類社交媒體層出不窮,除微信等以強關系交往為主的社交媒體外,陌陌、Soul、探探等陌生人交往軟件也在社交媒體市場中展現出強勁的競爭力。在線上交往中這種陌生人的交流已然是司空見慣的程度。在與陌生人這類弱關系人群交往時,很多人展現出的是一種“自來熟”的態勢,跟以前“遠離陌生人”“不能跟陌生人說話”的教育模式不同,與陌生人交往仿佛讓我們更自在。用戶間是否能互動交往、互動交往的感受如何都對大量App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微博、抖音、LOFTER這一類的以弱關系為主的社交媒體,用戶間的交往可以看作是一種廣場式社交,“只要關注就能獲得信息,以信息共享為主導”[ 1 ],但用戶間的評論、私信等互動行為使社交媒體更具有活力。
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是一種“差序格局”。每個人的社會關系都可以被身邊人影響或改變。就像三度理論,與身邊的某位同學或同事成為朋友后,那么就有可能認識這位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說現實生活中個人關系的建立基本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為依托,以現實生活中能夠見面接觸為條件,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關系使彼此間的生疏和懷疑會消除很多。那么,基于以陌生人交往為主的網絡趣緣群體中用戶之間呈現出怎樣的交流現象呢?趣緣群體為何選擇微博平臺中的超話為代表?
超話是超級話題的簡稱,它是微博于2016年上線的一款將話題模式和社區屬性相結合的興趣內容社區。超話的種類繁多龐大,聚集在這里的趣緣群體不勝枚舉。范式龍依據交流工具將網絡趣緣群體主要載體表現形式分為“吧趣緣”“客趣緣”“圈趣緣”“娛樂趣緣”[ 2 ]。以TAG、相互關注為主要交流方式的微博在這里被分為“客趣緣”,但微博超話中的趣緣群體卻更像“吧趣緣”和“客趣緣”的結合體。超話中的用戶以文字、圖片、視頻形式的帖子進行交流互動,這符合“吧趣緣”的條件;在瀏覽帖子或與其他用戶互動的過程中隨時可以對感興趣的用戶進行關注,這符合“客趣緣”的條件。以“吧趣緣”和“客趣緣”相結合的超話導致其信息傳播模式以及組織結構十分復雜,對其用戶關系的研究也更有意義[ 3 ]。
在微博超話中,用戶之間是陌生人的狀態下,社交恐懼的癥狀卻仿佛消失不見,彼此間可以用一種熟人的狀態進行交流,呈現出“擬熟人”的交流現象。
“擬熟人”是指陌生人之間的交流話語和狀態卻猶如熟人間親密。用戶通過微博超話中的互動行為能夠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找到親密關系甚至進行一些互惠行為。“擬熟人”現象的描寫與《強勢弱關系與熟絡陌生人:基于移動應用的社交研究》中提出的“強勢弱關系”概念基本一致,即明明是弱關系卻呈現出強關系的性質[ 4 ]。
強弱關系理論由美國學者格蘭諾維特提出,他認為人際關系的強度取決于雙方結成關系的時長、交流的頻率、交流調動情緒的強度、關系雙方所感受到的親密程度,以及關系雙方是否有互惠的責任,即互動時間、情感強度、親密程度、互惠行動是四個界定強弱關系的指標。但格蘭諾維特也指出這只能大體進行評價,不能具體量化。如果用這四個指標來界定微博超話中的用戶交往關系,那么超話用戶之間基本都是陌生人的情況下彼此都是弱關系。但在社交媒體時代,用戶間的關系強度不應該是非強即弱或非弱即強,他們可以超越強弱關系的界定,成為“擬熟人”。用戶可以自主選擇是否愿意將弱關系向強關系轉變,將陌生人向熟人轉變。因為超話中用戶的興趣重合,有極大可能成為朋友,而且這種興趣越特別,成為朋友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樣的凈效應就是人們更容易喜歡與自己有相同的古怪愛好的人,但他們互相發現則更難。”[ 5 ]微博超話種類繁多,人們在超話中可以很輕易地找到與自己興趣相投的伙伴,“構筑起廣闊的共同意義空間,建立一種基于思想交換的心理強關系,而非地域接近性所萌生的地緣強關系。”[6]
2.1 以人際信任為基礎的“朋友圈式”發帖
微信的朋友圈多是由現實中接觸到的朋友、同事組成,彼此間以強關系為主,并且帶有一定的信任。超話中的發帖內容會呈現出微信朋友圈式的特點,對超話中其他的用戶帶有一定的信任,這種信任可以看作是建立強關系的基礎。超話中會設計分區,發帖的內容不用必須貼合超話的主題內容,甚至有的超話會設置水帖專區,因此,不少用戶會選擇在超話中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如果是有趣的事件,會有很多人其樂融融一起討論;如果是悲傷的事情,也會有很多人進行安慰。另外,超話內也會有人進行求助,求助的事情或大或小,并且總是會出現愿意提供熱情幫助的用戶。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微博就專門設立了肺炎患者求助超話,并且聯動武漢地方政府以及央視新聞、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號,開通肺炎患者求助專區,多位患者通過在超話內發博得到解決。求助微博中多會帶有家庭住址和聯系電話等私人信息,在這些求助的微博下面可以觀察到多數發言都是在幫助患者將微博轉發擴散,或提供建議,努力為患者尋求到更多幫助。同時也有很多用戶在患者微博下進行評論,為患者祈福。
2.2 平臺轉換:由弱關系為主的微博轉向強關系為主的微信
用戶間的聯系從微博超話轉向微信時,可以將用戶的關系看作是從弱連接走向強連接進一步強化。“當前,跨平臺矩陣是許多新媒體運營的手段。在跨平臺過程中,微信形成的關系較強,微博形成的關系較弱,是否選擇在強弱關系中實現跨平臺互動聯系,仍然取決于用戶對于在媒介使用過程中的主動性。”[ 7 ]在與教育學習類有關的超話中,例如考研類超話中,不少考研人就會在超話中尋找自己的研友,每天一起加油,鼓勵對方。如果幸運地發現對方與自己的目標院校或目標專業一致甚至會選擇添加對方的微信,與對方分享自己的資料。另外,與對方分享資料的過程可以看作是一種互惠的過程,而互惠是強弱關系界定的其中一個指標。
2.3 渠道增加:由線上交往轉為線上線下同步交往
與他人約會時,我們總是與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朋友或同事這類強關系進行。雖說“擬熟人”強調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共通關系,但線下的接觸還是會為個體間的交往錦上添花。畢竟超話中的成員都是因為志同道合聚集在一起,這里的多數用戶在現實中身邊缺少能一起互相傾訴的角色,就會更渴望將線上的關系延續到現實中。在明星類超話中(這里的明星類超話指演員、歌手、相聲演員、電競選手、網紅等各種受人追捧的角色的超話),當后援會組織線下應援活動時,就會發現超話中會有很多粉絲發線下應援活動打卡的圖片。另外,當偶像有線下活動時,很多粉絲也會千里迢迢趕去見偶像一面。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有粉絲在超話中詢問是否有其他粉絲愿意結伴同行。很多線下活動也會專門建立微信群,當粉絲在超話中詢問線下活動事宜時,會有其他粉絲在評論中告知可以加入微信群。超話中的很多用戶會通過線下的活動認識更多朋友。很多追星的小伙伴也坦言過自己因為追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超話是很多用戶從線上交往轉向線下交往、從弱關系或潛關系轉化為強關系的橋梁。
“囚徒困境”告訴我們信任往往會使交往雙方達成合作,“相互信任保障了互惠過程,可以提供在必要時能將潛在的社會資本變成動員的社會資本”[ 8 ]。互聯網產生后,人們的社會交往由線下轉為了線上線下共同存在的模式,信任在這兩種狀態下依舊非常重要。微博超話中信任的存在為更多的用戶關系交往提供了可能,也催生了“擬熟人”現象的出現和發展。以弱關系交往為主的超話中信任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微博用戶主頁內容可以用來評判個人性格品質。超話中交流的用戶因為相隔網絡,并不清楚另一方現實中真實的樣貌,美丑、胖瘦、窮富等外在因素成為次要條件,而微博主頁發布的內容成為對該用戶進行評判的主要條件。微博主頁發布的內容越多越豐富,就越容易讓人對其產生信任及安全感,這種發布內容的行為可以看作是自我表露的過程。因為這代表著能從對方發布的大量微博中窺探到對方的某些隱私和信息,也可以從該用戶微博主頁的發言內容來判斷該用戶是否讓我產生好感,以及是否能讓我主動與對方成為強關系。雖然微博用戶目前并不是實名制,用戶名稱以及地點年齡等個人資料方面也只是個人隨意進行設置,但是那些合理填寫個人資料以及經常發布微博的用戶更容易讓人產生信任。
其次,圈層交往增加預設信任行為。現實生活中遇見擁有共同愛好的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亞文化青睞的人。再加上如今快節奏的生活及各種利益關系,很難在現實生活中對以地緣和業緣形成的關系產生情感,人們時常會感覺到孤獨,那么這種在網絡上基于趣緣形成的群體空間給很多人提供了去處。人們愿意將自己的情感歸入趣緣群體,人們主動加入趣緣群體本身就是對該趣緣群體的一種認同。在這種共同的興趣和文化訴求下,用戶之間在互動過程中會預設信任,即預設對方是值得信任的,這就讓超話中用戶之間的交流話題及氛圍比較輕松融洽。這種預設信任也會降低用戶融入微博超話的門檻,增強了用戶之間的互動交流。成員對彼此的稱呼也會用家人們、兄弟們、姐妹們等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名稱,女孩子之間甚至會互相叫對方老婆,這些稱呼更加拉近了趣緣群體間的關系。
另外,分享能成就信任。“個體間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一般道德原則以及一般社會交換過程基礎之上”[ 8 ],長期的互惠交換、人情交換使人們之間產生信任,但在超話中,更多的并不是用戶之間的互惠,而是單人的分享。用戶在超話中分享自己原創的獨有的信息和資源,當然,信息和資源既可以指觀點想法等文字類也可以指圖片或視頻類,其他用戶選擇觀看或是互動都由自己決定,但這種與超話中其他用戶進行分享的行為在超話中就是想要獲取信任的行為。若在超話中頻繁分享自己的資源信息,那么其他用戶會對自己的微博昵稱感到“面熟”,對自己也會多一份信任。
4.1 個人:減少孤獨感,寄托情感
市場化的社會轉型以來,不少年輕人背井離鄉,在離開以血緣和地緣形成的關系以后,孤獨地生活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家人、朋友交流和接觸的減少以及現實生活中與人分享興趣愛好的困難,使個人有強烈的孤獨感。微博超話類型豐富多樣,趣緣群體可以為血緣、地緣、業緣滿足不了的交流提供有效的情感補償,人們通過在超話中與人交流的親近感來滿足現實中的孤獨感。這種交流可以突破地理限制,填補個人的社交空洞。
4.2 平臺:增加了不同社交平臺之間聯動
微博超話滿足不了用戶交流的需求和欲望時,用戶就會選擇以強關系社交為主的微信,通過微信繼續保持強關系。用戶在微博超話這種趣緣群體中尋找和建立強關系后會選擇用微信來維持這段強關系,這就增加了微博和微信的聯動。除微信外,其他社交媒體也會與其產生聯動效果。例如,在cp超話中,很多粉絲會為自己喜歡的cp撰寫文章,由于微博某些方面的限制,不少粉絲就會選擇用LOFTER更新文章,并通過文章鏈接增加兩個平臺的聯動。另外,豆瓣小組與微博超話的性質相似,不少用戶會在超話中搬運或分享豆瓣平臺中的討論話題,超話中會引起新一輪的討論交流。這些行為還會為LOFTER或豆瓣等社交媒體吸引新的用戶。
4.3 社會:充實和改善現實社會的人際網絡結構,強化社會資本[ 9 ]
線上的人際交往可以分為熟人交往和陌生人交往。熟人交往即現實中的人際關系延伸到社交媒體中的交往。現實中,朋友和親人這類強關系之間不可能一直保持面對面接觸,通過線上交往則可以得到補充和強化。陌生人交往即與從沒有在現實生活中接觸過的人進行交往。這種交往在現實社會中得到實現比較艱難,但在網絡社交媒體中是普遍的,用戶之間通過互相接觸,在線上交往中成為強關系,甚至能夠將線上交往延伸到線下交往,成為線下強關系,這都能夠促進人際網絡結構的補充和完善,為自己帶來資源。
4.4 圈層化嚴重,信息繭房、沉默的螺旋效應明顯
微博超話有著嚴重的圈層化現象,且超話中呈現出的關系越強,圈層化越嚴重。圈層化意味著擁有很強的領地意識及內外有別意識,它為用戶提供親密關系、增強自我價值認同以外,還會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果[ 1 0 ]。一些亞文化超話中談論的話題往往都與超話主題有關,用戶每天瀏覽話題或參與話題的討論,潛移默化地接受超話中信息的影響,其他平臺也會搜索與此相關的內容,長此以往,受到的信息繭房效應會顯現出來。
另外,超話中發布的信息總是迎合超話的主題,多數粉絲不能允許有與之相反的觀點出現,即使是理性的觀點,也會被超話中其他的粉絲群起而攻之。這樣,在一些爭議性的話題中,理性的討論會越來越少。
概言之,“擬熟人”能夠從趣緣群體中生成。趣緣能夠滿足血緣、地緣、業緣滿足不了的情感,群體間在產生情感的過程中能體現出強關系的性質,通過其他平臺及現實接觸的助力成為線下強關系。超話中強關系建立的過程能夠滿足個人情感,增加不同平臺的聯動,完善現實中的人際網絡結構。但也要注意圈層化帶來的信息繭房及沉默的螺旋等不利影響,這就需要用戶提高自己的網絡及算法素養,減少超話帶來的負面影響,微博平臺也可以采取策略提升用戶互動效果。
參考文獻
[1]范孟娟.社交媒體用戶互動機制及關系轉化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17.
[2]范士龍,孫瑩.青年網絡趣緣群體聚眾行為研究[J].當代青年研究,2017(6):69-74.
[3]李瑞.漢服網絡趣緣群體互動研究[D].上海:上海財經大學,2020.
[4]許德婭,劉亭亭.強勢弱關系與熟絡陌生人:基于移動應用的社交研究[J].新聞大學,2021(3):49-61,119.
[5]克萊·舍基.未來是濕的[M].胡泳,沈滿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6]喻國明,朱烊樞,張曼琦,等.網絡交往中的弱關系研究:控制模式與路徑效能:以陌生人社交APP的考察與探究為例[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40(9):141-146.
[7]喻國明,曾佩佩,張雅麗,等.趣緣:互聯網連接的新興范式:試論算法邏輯下的隱性連接與隱性社群[J].新聞愛好者,2020(1):9-13.
[8]馬克·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M].羅家德,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9]邊燕杰,繆曉雷.論社會網絡虛實轉換的雙重動力[J].社會,2019,39(6):1-22.
[10]彭蘭.網絡的圈子化:關系、文化、技術維度下的類聚與群分[J].編輯之友,2019(11):5-12.
3662500589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