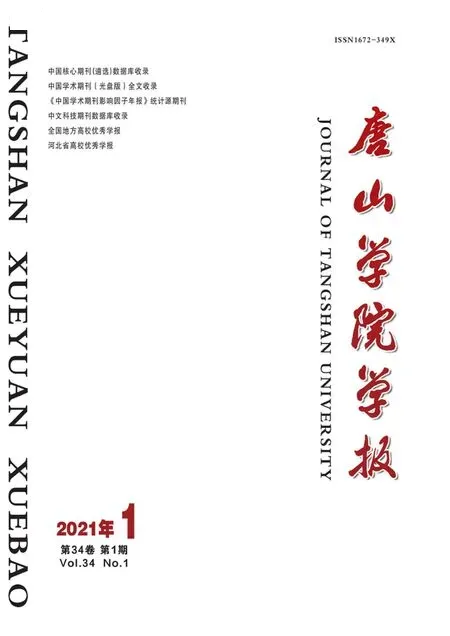元代笞杖刑制“七作尾數”之成因考辨
譚天樞
(南開大學 法學院,天津 300350)
元代笞杖刑制有以“七作尾數”的特點,其產生的原因備受關注與爭議。當前學界對此存在不同的說法:第一,明中葉以降,葉子奇提出了“饒三下說”的解釋,并逐漸成為主流觀點,影響頗深;第二,少數學者提出了“杖十七說”。這兩種學說的準確性和合理性尚待分析和考辨。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更為可靠的史實依據或是相對穩妥的結論?這正是本文加以分析和考證的重點與核心。
一、蒙元法律中關于笞杖刑制“七作尾數”的規定流變
大蒙古國建立之初,法律形式主要以蒙古部族傳統的札撒為主,蒙語“札撒”為法律、條例之意,取材于長期的歷史與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各種習慣和準則——約孫,具體表現為部落首領發布的各條旨令。成吉思汗時期,札撒的內容被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并在窩闊臺元年(1229)正式匯集頒行,名為《大札撒》,現已佚失,具體內容散見于典籍之中。《蒙古秘史》記載了成吉思汗于虎兒年(1206)關于護衛軍制度的一道旨令:
值日班的散班,分為四班,委派班長如下:不合管理一班護衛,阿勒赤歹管理一班護衛,朵歹扯兒必管理一班護衛,朵豁勒忽扯兒必管理一班散班。委派這四班護衛長的令旨宣布了。各班長令所屬護衛值班,三夜一換。護衛人等誤班,鞭誤班人三條子。再犯鞭七條子。又該人無病及未得所屬官長允許第三次誤班,鞭三十七條子,這是他已經不愿為我們出力,當流放遠方![1]193
該旨令中出現的“鞭七條子”和“鞭三十七條子”是目前史料中關于蒙元時代笞杖刑制“七作尾數”的最早記載,在現代復原的《大札撒》中也有相同的表述,很可能是依據《蒙古秘史》而作(1)但是復原的《大札撒》第五十四條規定:“偷盜他人非重要財物的,處杖刑;根據情節的不同,分別杖七下、十七下、二十七下、三十七下、四十七下,而止于一百零七下。”筆者沒有找到成吉思汗時期及以前的依據,而這段表述與元代杖刑特點相同,故推測此處可能是依據《通制條格》《元典章》等元代法律所復原,并非成吉思汗時期的刑制原貌。:
第三十八條:怯薛軍違反管理制度的,免死。初犯的,處鞭刑三下;再犯的,處鞭刑七下;第三次違犯的,處鞭刑三十七下;仍不悔改的,處流刑。[2]7
窩闊臺在滅金之后,再次重申了該旨令:
各班巡察如有誤時者,依前旨鞭三條!如再犯,鞭七條!又該人無故或未得其首長準許,三次再犯,視為故意違犯我的旨意,鞭三十七條,流放無人煙的遠處去。[1]245
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秘史》余大鈞的譯注本中,該刑罰被譯作“杖責七下”和“杖責三十七下”,額爾登泰、烏云達賚的校勘本中作“笞七下”和“笞三十七下”;色道爾吉譯的《蒙古黃金史》中作“笞撻七下”和“笞撻三十七下”(2)參見《蒙古秘史》,余大鈞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頁;《蒙古秘史》,額尓登泰,烏云達賚校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24頁;[清]羅桑丹津:《蒙古黃金史》,色道爾吉譯,呼和浩特:蒙古學出版社,1993年,第149頁。。該翻譯用詞有如此的差異,是由于蒙元的笞杖刑制與漢法刑制的發展趨勢相似,都是由細長狀、抽擊類的刑具作為原型分化、演變而成。《唐律疏議》中強調:“笞者,擊也,……漢時笞則用竹,今時則用楚。”“杖者,持也,……《書》云‘鞭作官刑’,猶今之杖刑者也。”[3]3-4刑罰創設之初,大多采用鞭條、竹柳、棍板等物處刑,之后刑具規范為具有一定標準的笞、杖,且在書面用語上對此也進行了規范。再加之蒙漢兩族文人翻譯時的文字取向有所不同,蒙古文字的記載更傾向于“鞭”,而漢族官吏依據《唐律》的解釋更傾向于譯為“笞、杖”,故此三詞在運用中發生了一定的混同、互譯。例如:“牛兒年(1205),成吉思合罕降旨,賜給速別額臺鐵車,派他去追擊脫黑脫阿的兒子忽禿、合勒、赤剌溫等。臨行時,命令他說:‘……有違反這個命令的軍人,就予以鞭打。’”[1]163立國后,太祖令金國降臣郭寶玉“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重罪處死,其余雜犯量情笞決”[4]3521。上述太宗的旨令提及的鞭刑,在《元史》中也被譯作笞刑、杖刑。
然而,關于大蒙古國時期笞杖刑尾數的記載還存在其他數目,在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的行紀中就有所差異:
如果有人泄露了他們的機密,特別是泄露了他們準備出發作戰的機密時,就要在臀部打一百杖,讓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用粗棒盡可能用力地去打。[5]
他們對大盜竊也處以死刑,但小偷小摸,如盜竊一只羊,只要不是屢次被當場抓住,他們就只痛打竊賊一頓,而且如果打一百下,他們必須用一百根棍子。[6]
志費尼對蒙哥即位前后薩倫的·亦都護叛亂的記載中,也有笞杖刑及其具體數量:
忙哥撒兒那顏跟著審問此案,亦都護否認有罪,因此嚴刑拷打。他們狠命擰他的雙手,使他精疲力竭撲倒在地。接著又用木桚緊箍他的前額。獄卒松了桚,以此屁股上結實地挨了十七下以示懲處。……撒渾在陰謀中牽連不深,他和拔都的宮廷又有些關系,因之只在屁股上挨了一百單十下結實的棍子,就無事了。[7]
從上述記載來看,笞杖刑制在太宗至憲宗時代已經粗具規模、漸成體系,而且處刑數量除了“七作尾數”外,還存在整十數目,這表明這一時期的笞杖刑的數量是在浮動和多樣的。之所以產生這種差異,可歸因于當時的法制和政治環境:從太祖立國迄元朝建立的六十多年間,朝廷以征戰作為第一要義,頻繁的戰爭使得法制運行極不穩定,統治者只能以傳統的習慣法匯總,再借鑒內附民族和被征服地區的法律,暫時對統治秩序加以維持,新法的制定被長期擱置,所以在法律施行時,就難免會有臨事制法和法律之間銜接不當的問題。隨著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內附民族的數量增多,新的法律元素不斷融入,進一步加劇了法制秩序的紊亂。例如在志費尼的記載中,關于處刑數量為整十數是否受到了波斯本地法律和伊斯蘭宗教法的影響,抑或是沿用金律的規定,尚待考證。而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作為當時的傳教士,來華時間短暫,對當時的法制現狀并不熟稔,其觀察的視角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在元代繼受的法律中,最為典型的是金朝的《泰和律義》,金朝覆滅之后,它被作為處理北方漢人、女真、契丹、高麗等族群糾紛的基本法律而使用,世祖即位后的幾次新法頒行,都是以《泰和律義》作為藍本。中統二年(1261)八月十八日,由世祖降旨頒行新任參知政事楊果起草的《中統權宜條理》中對杖刑數量作出了規定:
制曰:……朕惟欽恤,期底寬平。乃姑立于九章,用頒行于十道。比成國典,量示權宜;務要遵行,毋輕變易。據五刑之中,流罪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著為定律,揭示多方。[8]
這部法令的具體內容已無從考證,僅在王惲的《中堂事記》中留有詔文。其中,“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這一規定被日本學者安部健夫和植松正視為“笞杖刑量附加尾數‘七’的最初的法令”[9]。結合前文分析來看,雖然這種觀點的準確性值得商榷,并且從“權宜”“姑”等字眼判斷,這是一部臨時性、粗略化的暫行規定。但不可否認,笞杖刑制以“七作尾數”的特點被首次作為系統性法律規定,從而初步厘清了處刑數量不一致的混亂局面。至元八年(1271),《泰和律義》被元廷明令禁用后,世祖開始著手制定新法,于至元十年(1273)“敕伯顏、和禮霍孫以史天澤所定新格,參考行之”[4]151-152。《元典章》卷三十九《刑制》開篇的《五刑訓義》記載了笞、杖、徒、流、死五種基本刑罰(見表1),元廷在施刑數量上作出改革:除死刑外,一律斷以杖刑,并以七作尾數。馬可·波羅對此描述道:“其治理獄訟之法如下:有竊一微物者,杖七下,或十七,或二十七,或三十七,或四十七,而止于一百零七,視其罪大小而異;有時被杖至死者。”[10]
結合《元典章》收錄匯編的自元世祖以來的詔令、條格和判例的內容進行分析,中統元年至至元八年的條文中,已經出現了大量“七作尾數”的笞杖刑判決,大部分與“舊例”(3)所謂“舊例”,主體是《泰和律義》的條文內容或是由其衍生的暫行判例。劉曉教授認為,《至元新格》只能算作是行政規章,內容原則性較強,無具體處罰內容,在司法審判中基本無可操作性,故此時很可能是《泰和律義》仍在司法實踐中繼續沿用。劉曉:《元代法律形式與法律體系的構建》,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9年12月,第85頁。的刑罰折算關系符合表1刑制圖表。姚大力教授認為,“元政權在中原的司法實際中,基本上采取沿用金泰和律定罪量刑、再加以折減施行的做法”,并且他判斷《中統權宜條理》是“五刑之制”圖表的基本依據[12]。筆者認為,世祖的三次新定條格很可能也是延續了《中統權宜條理》的主旨精神。沈家本在比較《大元通制》與《至元新格》的內容時也強調:“《新格》當已包于《通制》之內,而《通制》未必與《新格》全同。”[13]370與《大元通制》同一時期的《元典章》在內容上也應該符合這個規律,承繼了《至元新格》的主要內容。再者,大德九年(1305)刑部在回答山東宣慰司的關文中強調:“照得舊例:笞五十,杖五十,至元二十八年奏準定例。《至元新格》內一款,節該諸杖罪云云。欽此。本部議得:古者笞五十,杖五十,蓋為數止滿百,故各半其數;今既杖數至一百七下,所據五十七以下當用笞,六十七以上當用杖,行之已久。”[11]1351可見,“七作尾數”的規定在《至元新格》中已正式確立,繼而影響到了后續的《大元通制》和《元典章》。因此“五刑之制”的來源路徑應該是:《中統權宜條理》 《至元新格》 《元典章》。由于元廷在中后期加緊社會控制,加劇了刑罰的嚴酷性,恢復了徒刑和流刑,如延祐二年(1315)對盜賊犯罪出臺新例,其處罰力度相比于以往常例要加重許多,出現了徒刑加杖的規定,“今后強盜持杖……不曾傷人,不得財,斷一百七,徒三年”[11]1643。英宗時期,漳州路推官烏古孫良楨于至治二年(1322)上疏稱:“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4]4287元廷遂定為例,此即為表1中“加徒減杖例”的由來。該例是將七等徒刑合并為五等,取消徒四年、徒五年兩等刑罰,杖刑“皆先決訖,然后發遣合屬,帶鐐居役”。

表1 《元典章》刑制圖表[11]1331
需要注意的是,元代還存在笞杖刑數量為“整十”的情形:如“私宰牛馬”之罪,中統二年(1261)五月的圣旨規定:“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飲食宴會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殺牛馬。如有違犯者,決杖一百。”[11]1897至元八年(1271),在處理中都地面“夤夜私宰牛只”現象時,尚書省上奏稱:“俱系夤夜宰殺,又不經由牙稅,顯是偷買偷殺。合無中書省里會諸衙門官員,勾集各管局分頭目,明白省會,先要甘執?”其后得到了圣旨的肯定:“教省里聚會,要了文書,省會了。若有違犯底,定將頭目及犯人重要罪過欽此乞照。”[11]1899大德七年(1303),江浙行省給福建宣慰司的札付對上述兩道圣旨加以援引,還特別強調:“欽依已降圣旨事意申報所在官司……如有違犯者,取問是實,依條斷罪施行。”[11]1898同時期河南省給中書省的咨文中亦是似此援引。這一規定在大德十年(1306)被刑部郎中趙奉政再次提及:“私宰自己馬牛,杖斷一百。”[14]133再如延祐五年(1318)的《申明鹽課條畫》和延祐六年(1319)的《鹽法通例》中多次提到“笞四十”“杖一百”“杖六十”的規定,而這些規定之前都有一處前綴:“宜申舊制宣諭”或是“欽奉圣旨內一款節該”[11]830-843。這些前綴表明,新定鹽法是對根據原有“舊例”而形成的圣旨進行重申。雖然無法確定這些整十數的刑罰最后在施行中有無經過表1的折算,但是經過上文的論證得知,這些圣旨基本產生或派生于禁行《泰和律義》以前的年代。在《大元通制》等新法頒行之后,元廷依然將這些圣旨或是原封不動式地加以照搬,或是移花接木式地稍加改動,作為新法調整元代中后期的社會關系,方才形成了“七作尾數”系統規定的例外情形。從本質上講,這些規定屬于“舊例”,是在元代漸已成熟的法律系統中的些許“遺跡”,是《泰和律義》這支殘燭在發揮著最后的余熱。
二、關于“七作尾數”之成因的各種觀點
(一)“饒三下說”之存疑與考證
對于元代笞杖刑制“七作尾數”的產生原因,流傳最為廣泛的便是“饒三下說”: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15]50
這一表述最早見于明人葉子奇的《草木子》,葉氏將其作為世祖恤刑慎罰、愛撫民眾的典例,又言:“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15]50這種說法一經出現便廣為傳抄,成為明清以來的主流觀點,許多筆記雜談中皆有相同的表述。沈家本在考證“七作尾數”這一問題時,也引用葉氏之說,認為“以七為度,說見于此”[13]371。復原《大札撒》的學者在解釋“七作尾數”時,將“饒三下說”作為成吉思汗的規定,并解釋道:“這是按照蒙古舊俗……體現大汗對民眾的寬容,各等分別減免三下而成,元朝也繼承了這一傳統。”[2]180自然也是源自葉氏之說。甚至許多法制史教材都作為產生原因加以援引,這似乎更加增強了“饒三下說”的證明力度。
但“饒三下說”存在諸多疑問:首先,葉氏的《草木子》據考證成書于明洪武初年,刊行于正德十一年(1516),成書之時距離元世祖制定新法已然有百余年,如此大的時間間隔會使該說的證明力度有所降低;其次,“饒三下說”既無一手的元代史料作為依據,亦無前人相關的記載作為輔證,葉氏本人對此更無解釋,那么此說就顯得過分突兀,有孤證不立之嫌;再次,《草木子》本身為小說家之言,其內容多有筆者杜撰,也有坊間傳聞,作為制度史料的考證依據略有不妥,馮夢龍就曾對此評價道:“此雖仁心,亦近于戲矣。”因此,“饒三下說”的可信度恐怕要大打折扣。盡管葉氏在該書中另有記載:“北人不識字,使之為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日子,七字鉤不從右,七而從左轉,見者為笑。”[15]63但此處似為北人不識七字之笑談,無法與“七作尾數”建立聯系,同樣為小說家之言不能考證真偽,更不能作為由來的證明。
雖然“饒三下說”屬于小說家之言,但是其背后反映的立法價值取向卻有史據:世祖清醒地認識到,統治如此廣闊的多元民族和文化區域,只靠軍事征服和嚴刑峻法不可能長期立足,極有必要學習漢族地區有益的治國方略,由此產生了“恤刑慎罰”的立法指導思想。這一思想在其即位前就有所踐行,如憲宗二年(1252),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就因濫刑受到了忽必烈的責問。即位之后,這一指導思想得到了更為全面的落實。中統四年(1263)十一月二十三日,忽必烈降旨:“至如我或怒其間,有罪過的人根底,‘教殺者。’便道了呵,恁每至如遷延一兩日再奏呵,亦不妨事。”[14]128這一思想和世祖“愛民仁政”的治國策略互為表里,他曾經數次下詔禁止蒙古官軍侵擾民眾,如中統三年(1262),“諭諸路管民官,毋令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擾及良民”[4]83。又如至元十五年(1278),“詔諭軍前及行省以下官吏,撫治百姓,務農樂業,軍民官毋得占據民產,抑良為奴”[4]204。其目的在于通過寬緩刑罰、安撫民眾來施行“懷柔”政策,以圖緩和統治區域內部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從而贏得民眾的支持與信任。正如《事林廣記》中所載:“今我大元圣聰又減輕笞七下,且易楚用柳,可見愛民如子也。”[16]此即元初統治者追求的社會效果。而源自蒙古部族自身文化傳統的“七作尾數”笞杖刑制,在數目上恰恰少于漢法刑制的整十數,數量上的遜差似乎與世祖的“恤刑慎罰”思想實現了客觀上的默契,而這一巧合自然就假以后人過度解釋和推演的空間,方才產生了流傳甚廣的“饒三下說”。
(二)“杖十七說”與唐宋刑制的演變
學者楊耀田持與“饒三下說”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此規定承繼于唐末以來的刑制變革,元代以“七”為額的杖刑,有可能是將中原漢地應用較為普遍的“十七杖”擴展融入整個杖刑數額中而已,進而成為元代杖刑的獨創點(4)楊先生的觀點見此文:《有關元代笞杖以“七”為數的吧啦》,https://www.douban.com/note/328609514/.訪問日期:2020年12月9日。。
五刑體系在唐中后期開始出現嬗變,主要原因為君主以敕代律,“凡律法之外,有殊旨別敕,則有死流徒杖除免之差”[17]。這種臨時設刑的現象沖擊了原有的刑罰體系,特別是脊杖的恢復、“杖殺”的出現以及“重杖一頓”“加決杖”等“情杖”法外施刑的常態化,更造成了施刑的混亂。五代時期,由于軍人政權的相繼建立,君主敕令對于法律的干涉加深,刑罰體系的紊亂程度有增無減。此時期的法律開始出現“杖十七”的記載:長興四年(933),唐明宗頒布鹽法,對于違犯者“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決脊杖十七,放;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18]。廣順元年(951),周太祖新頒銅法:“今后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在一色即不得瀉破為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并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脊杖十七,放。鄰保人,決臀杖十七,放。”[19]楊耀田先生認為,“脊杖十七”的記載被元代笞杖刑制所吸納,并列舉敦煌出土文獻《茶酒論》中的“脊上少須十七”的表述為證[20]。但上述兩處法令的記載均存在疑問:王溥的《五代會要》關于長興四年鹽法的記載為“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21]423;其關于廣順元年的銅法的記載也與《舊五代史》相左,“其地分所由節級,徒一年;鄰保人杖七十”[21]436。那么對這幾種相異記載如何辨別?筆者認為,無論是《冊府元龜》《舊五代史》,還是《五代會要》,都屬于宋人對前代法律的記述,其過程有可能已經過宋建隆“折杖法”(見表2)的折算。

表2 《宋刑統》卷一《名例律》所載“折杖法”
根據“折杖法”,徒二年折脊杖十七下,長興四年鹽法的兩種記載可以通過“折杖法”聯系起來,也即《冊府元龜》的記載已經過宋代“折杖法”的轉換,這就與王溥的“徒二年”的記載相吻合了。至于廣順元年的銅法在處刑數量上似乎并不符合表2中的折算關系,但就“放”這一處理結果而言,無疑是宋代“折杖法”的痕跡,所以《舊五代史》的記載也并非是原刑。并且“脊杖二十”似乎比“脊杖十七”出現頻率更高,元廷為何不采“二十”之數?再者,《茶酒論》屬于“賦”體文章,其中的“脊上少須十七”很有可能是為了句尾押韻,與前文的“將到市廛,安排未畢。人來買之,錢財盈溢。言下便得富饒,不在明朝后日。阿你酒能昏亂,吃了多饒啾唧”[20]在音律上相呼應。拋開“賦”的文體格式,亦可作“十八”或“二十”等數,并不代表“脊杖十七”在司法實踐中的使用頻率。因此,上述史料無法證明“脊杖十七”是五代、兩宋使用較為廣泛的刑罰,更無法得出元代笞杖刑“七作尾數”就是吸納了“脊杖十七”這一結論。
三、“七作尾數”可能來源于北方游牧民族集團的“尚七”傳統
在對既有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成果分析的過程中,北方游牧民族集團對“七”這個數字的頻繁使用引起了史學家們的注意。在西伯利亞地區出土了許多與“七”相關的物品,如安加拉河左岸的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現了由七件墜飾組成的兒童墓葬,又如青銅時代巖石上的七線的刻痕,溫海清教授將其視為內亞族群最早的“七”崇拜現象[22]。公元5世紀以后,“七”這一數字在北方游牧民族集團的祭祀、朝儀、外交、婚喪活動和天文歷法中數見不鮮。《魏書·禮志》載:“天賜二年(405)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一……置木主七于上(5)至于《魏書》和《遼史》中出現的“七木主”和“七廟神主”也被溫海清教授作為北方游牧民族集團“尚七”的例證之一,值得商榷。孝文帝漢化改革后接受華夏禮法,按照《禮記·王制》的規定:“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早在道武帝時便已經設立太廟,以平文帝為太祖,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491)復議祖宗,改道武帝為太祖,重列昭穆。遷都洛陽后,高陽王元雍“奉遷七廟神主于洛陽”(《魏書·高陽王雍傳》)。因此,“七廟神主”應是來源于漢地禮制。參見劉連香:《民族史視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38頁。……選帝之十族子弟七人執酒……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23]《周書·突厥傳》載:“死者,停尸于帳……繞帳走馬七匝,一詣帳門,以刀嫠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24]《遼史·禮志》中曾多次出現“七拜”,如:“臣僚接見儀:……皇帝御座,奏見榜子畢,臣僚左入,鞠躬。通文武百僚宰臣某官以下祗候見。引面殿鞠躬,起居,凡七拜。”“宋使見皇帝儀:次引漢人臣僚北洞門入,面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官某以下起居,皆七拜畢。……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祗候見,起居,七拜。曲宴高麗使儀:……宴畢,引使副謝,七拜。”[25]“七拜”也出現在元代宮廷禮儀中,《玉堂嘉話》載:“至元十五年(1278)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26]
中興二年(532),高歡擁立魏孝武帝元修,登基之禮為:“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于氈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云龍門入。”[27]其中“以黑氈蒙七人”的禮儀在海敦的《東方史之花》中得到再現:“韃靼人設好寶座,在地上鋪一張黑氈,讓成吉思坐上去。七個部族的首領齊舉黑氈,把成吉思抬到寶座上,稱他為汗,向他跪拜效忠。”[28]31羅新教授認為,海敦既未到過蒙古,亦不可能親歷成吉思汗的登基典禮,他所述“曾兩次目睹韃靼人選立大汗”,是指他在波斯伊利汗國的經歷[28]37。所謂的成吉思汗登基儀式,應該是他根據伯父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的轉述而聯想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一記載并不影響蒙古部族的“舊俗”與“代都舊制”之間的聯系。
除此之外,蒙古部族之中還流傳著“七位幸存者”的傳說,如至大三年(1310)發生在福建宣慰司地面的一件“亂言”案,回回人木八剌將兒時聽的傳說嫁禍于同村村民馬三,并進行誣告。傳說具體內容為:
住(往)常時漢兒皇帝手里有兩個好將軍來,殺底這達達剩下七個,走底山洞里去了。上頭吊著一個驢,下面一個鼓兒,聽得撲洞洞響,唬得那人不敢出來。您殺了俺,幾時還俺?那將軍道:日頭月兒廝見呵,還您。如今日月廝見也,這的是還他也。[11]1401-1402
雖然該傳說不排除有木八剌訛化和虛構的成分,但是“達達剩七人”的傳說確實在同時期的多本域外書籍中記載。如,道森的《出使蒙古記》中載,蒙古人和契丹人“經過一場大戰,蒙古人大敗,除剩下七個人外,在這支軍隊中的所有的蒙古貴族都被殺死”[29];察合臺語史籍《選史——勝利之書》中也提到避難于“額兒吉尼——昆”巖洞中的七人和七犬交媾生子,經過五百年繁衍生息,創立蒙古部族的先祖傳說;完成于1050年前后的中亞史料《記述的裝飾》將其記敘為七個韃靼人外出尋找新的牧場時幸免于難(6)參見鐘焓:《中古時期蒙古人的另一種祖先蒙難敘事——“七位幸免于難的脫險者”傳說解析》,載《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突厥時期的《翁金碑》記載:“那時在漢人之北的野咥人及烏古斯人之間,有七個人開始與我們為敵。”筆者猜測這一表述可能與“七位幸存者”的傳說存在某種關聯。。數字“七”能夠與自身部族的起源傳說相關聯,足可見其對于蒙古人的重要意義。
公元8世紀突厥汗國的《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銘文中,兩位可汗的喪葬日期都與“七作尾數”有著重要關聯:“闕特勤卒于羊年十七,九月二十七舉行葬典。其祠宇、藝術工作(圖繪?)及刻石皆謹成于猴年七月二十七。”“朕父可汗(毗伽可汗)狗年十月二十六日崩,豬年五月二十七日,吾等舉行葬禮。”[30]《闕特勤碑》漢文碑銘載:“大唐開元廿年(732)歲次壬申十二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7)除此之外,兩汗的碑銘中還有大量關于“十七人”“七十人”“七百人”的記載,也可作為“尚七”例證。同時期的《闕利啜碑》和《暾欲谷碑》中亦有“在與九姓烏古斯的七次交戰中”“七百人”和“頡跌利施可汗與漢人交戰了十七次,與契丹人交戰了七次”的表述。參見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41-268頁。殯葬儀式選擇在陰歷二十七日舉行可能有天文學方面的原因:月亮的運轉周期是28天,以7天為一個階段。突厥學家路易·巴贊認為:“每個陰歷的二十七日,于月亮最后的下弦消失時,便是月星于數日后再出現的前奏……它是死者消失的象征,也是在彼世復活的前奏。”[31]這一點在蒙古人的傳說中也同樣可以得到驗證:“在蒙古人尚居住在北杭愛山發祥地的時候,那里就居住有一位早已經擁有巫術修習的老翁。當他感到自己瀕臨死亡時,便告訴其子說,自己死后將會庇護他,條件是其子必須以非常隆重的殯儀安葬他,然后再對他祭祀……死者的兒子非常有規律地于每月一、七、九日前往其父墓前舉行茶祭、水祭、奶祭和酒祭。”[32]12-13蒙古部族受其傳統薩滿教的影響,有濃厚的自然崇拜,其中天神崇拜為其最高形式,即“蒙客·騰格里”。數字“七”也同樣出現在薩滿教的神靈信仰之中:“風、雷、霧、電和云也都有他們各自的一組騰格里天神。白色閃電騰格里天神及其所有神伴都居住在西南,77位西哈爾(Siqar)、99尊好責罵的天神庫庫爾(Kükür)和13尊令人毛骨悚然的雷神。”[32]71
關于數字“七”的象征意義,也即為何“尚七”,除月亮運轉周期外,還有以下兩種觀點。
其一,“七”來源于北斗七星,蒙古人稱北斗七星為“七老翁星”,其在蒙古人的信仰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成為族群繁衍和財富增殖的代表,每顆星體都有自身的梵文名稱和特殊內涵:
七老翁星的起源是:99大天神的家族,所有77大地母。
金森迪(Sündi)星,你使一人變成百余人;
布拉瓦巴達拉(Buravabadara)星,你使一匹母馬變成千匹母馬;
阿斯里斯(Aslis)星,它使一只綿羊變成千只白綿羊;
烏魯基尼(Urukini)星,它使一只牛變成百只紅牛;
阿布拉德(Aburad)星,它使一頭駱駝變成10只黑駱駝;
拉拉迪(Raradi)星,它使一塊田達到10塊田的產品;
摩爾巴爾(Molbar)星,它使一個窮人變成富翁。(8)[蒙]策·達木丁蘇隆:《蒙古文抄本集》,第14卷,烏蘭巴托,1959年,第135-136頁。轉引自[法]海西希:《蒙古的宗教》,耿昇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第109-110頁。
其二,數字“七”具有抽象的神話意義可能來自空間方位,前、后、左、右、上、下加之本位這七個方向,已達窮極。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以及天穹和大地都被賦予了特定的神學意義,而主體所在的中央區域則是被視為自身部落或族群的特定空間[22],也即“神話空間感和神話時間感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兩者一起構成神話數觀念的起點”[33]。
依據上述史實和思路,我們可以作出以下推論:北方游牧民族集團自始以來就存在著對“七”的數字崇拜,對這一數字的選擇很有可能來自北斗七星,抑或是其他神學觀或是宇宙論。這種精神基因在游牧民族內部的族群更迭之時,被悄然保留在歷史的血液中,因因相循,無論主流集團冠以何名,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迄至蒙古部族的崛起,這一鮮明的特征仍在其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得以顯現。所以,要想探索蒙元時代的某一歷史特征,勢必要對整個北方游牧民族集團的歷史進行回溯,只有這種沿波討源才能較為完整地厘清歷史發展脈絡。正如海西希所說:“我們根本不可能具體確定具有典型特點和屬于某一固定時代的內容,尤其是在研究這些宗教史現象的時候更為棘手。各種影響互相交織得非常緊密,文化特點與其他特點過分地摻和在一起了。各民族集團的名稱很多,而且變化也很頻繁,一般都取古代著名民族集團的名稱為名。各民族集團也經常交換棲身地,從附近的和被征服的居民中借鑒來了某些特點。當他們被戰勝之后,以使自己的宗教觀念和文化特點徹底讓步于勝利者。”[32]22-23基于此結論,就不難看出蒙元時代的笞杖刑制“七作尾數”即為“尚七”傳統的衍生現象之一(9)在元以后的蒙古族法律中,“七”這一數字似乎悄然消失了,但是“九”這一數字被保留了下來,元代的“盜一罰九”演變為“九作尾數”,并且笞、杖(鞭)刑罰數量又恢復到整十數。如康熙六年(1667)的《蒙古律書》第八十七條:“看守非死囚之犯疏脫,章京罰牲畜二九,分得撥什庫罰牲畜一九,小撥什庫鞭八十,披甲人鞭五十。”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六年〈蒙古律書〉》,載《歷史檔案》2002年第4期,第3-11頁。這種刑罰的變遷可能是受到了喇嘛教對傳統薩滿教的滲透和影響,尚需進一步考證。。并且數字“七”適用于刑罰數量這一特征在元代之前的刑制中也可以找到痕跡,如武珪的《燕北雜錄》所記契丹的“鐵骨朵”刑具:“鐵瓜(番呼鬃睹)以熟鐵打作八片,虛合成,用柳木作柄,約長三尺,兩頭鐵裹,打數不過七下。”[34]
此處值得一提的是,有觀點認為蒙古人以“七”為兇數,所以將“七”寫作“”是為了規避本字,受刑罰本身帶有消極、負面意義,所以在笞杖刑罰數量上選擇“七作尾數”,其所援引的依據為《元史·祭祀志》的記載:“凡宮車晏駕,……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箸各一。”[4]1925-1926其中,喪葬品的數量之和為七,可驗證“七”為兇數。另一依據為鄭思肖的《心史》:“韃靼風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咒其尸曰:‘汝今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為祟之跡。”[35]82此段文字也被溫海清教授加以引用。但是,整部《心史》的主觀臆斷和偏見居多,其中很多記載都經不起史實和邏輯的推敲,《四庫提要》認定其為明末之人冒名偽作,魯同群教授亦持此觀點[36]。如《犬德》篇載:“元賊南破中國,至于犬亦殺食,幾于盡。”[35]43b這顯然違背史實和蒙古風俗。并且鄭氏自認:“我不與北人密,不入北地,不詳聞孰見,其惡豈能盡書?”[35]85a鄭氏從未涉足北方,又缺乏與北人的溝通交流,對蒙古風俗可能未窺全貌,其所述真實性恐怕不高。而《元史·祭祀志》的記載則可以作為蒙古族“尚七”傳統的例證之一,但如果多邁一步,區分兇吉,就現有材料還無法得出此結論。
四、與唐、宋、金律之比較:刑罰加重抑或減輕?
元初新定刑制,在本質上與唐大中“折杖法”、宋建隆“折杖法”相似,都是對既有刑罰體系的“重新洗牌”,其目的都在于通過寬緩刑罰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國家政權。因而就立法初衷而言,實有減輕刑罰之傾向無疑。但若具體評價其加重抑或減輕,則需要選擇合適的參照坐標,尤其是結合前代的刑罰來比較分析。正如宮崎市定所言:“如果把元代在中國史軌道上割裂出來,要搞懂元代是很難的。”[37]
金律雖然以《唐律疏議》為藍本,但是刑罰要嚴苛許多。第一,徒刑分為五等,增加四年、五年兩等。第二,變相肉刑產生,“州縣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杖不分決,與殺無異”[38]669。金廷又以官員決杖之數多寡作為考課依據,導致杖刑實質加重。雖然章宗于承安四年(1199)改定杖刑分寸,并統一用銅杖施刑,但泰和元年(1201)又“以見行銅杖式輕細,奸宄不畏,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38]675。第三,具體罪名的處罰加重,以竊盜罪為例,唐律規定:“諸盜竊,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3]358而金律規定:“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終身,仍以贓滿盡命刺字于面,五十貫以上死,征償如舊制。”[38]670第四,贖刑加倍,加重了受刑者脫罪的負擔。元初刑制體系改革中,杖刑的上限為一百零七下,數目大為減少,而且從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書省又援引了唐太宗時禁止鞭背的規定,要求“罪人毋得鞭背”[11]1213,脊杖取消。故較之金律,元初經笞杖刑制改革刑罰減輕了許多。
表3為唐、宋、元杖具規格的比較。

表3 唐、宋、元杖具規格之比較
從表3可以看出,元代的杖具規格幾乎與唐代無太大差異,比宋代相比重量可能還要稍輕(10)唐、宋、元三代各自的長度差異非常細微,唐代的一尺介于29.4~31.7 cm之間,宋、元的一尺介于30.8~30.91 cm之間,就算是考慮到這一差異,將尺折算成分、厘等單位,該差異幾乎被淡化,故在此沒有將該因素納入考量。。但許多人直觀地認為,元代笞杖刑制名為在十等刑罰上減三下,但自七至十七實際上有十一等,反倒是杖刑的最高限額加了七下而加重了刑罰。大德年間,元人王約就曾上奏:“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4]2604但由于元廷的謹慎態度,此事旋即擱置。明人丘濬認為:“其初本欲減以輕刑也,其后承誤,反以為加焉。”[39]沈家本認為:“元之笞數,自七下起,實是減而非加也。笞、杖各五,當止九十七,乃笞多一等,止于五十七,于是杖自六十七起,止于一百七,則本減而變為加矣,其故無可考。”[13]371通過上文對立法初衷的分析來看,加等是與之相違背的,這個“漏洞”使元初法制飽受詬病。且不經意間的加一等使得司法審判的科刑秩序變得混亂,具體是指第六等五十七下的適用十分尷尬,“司、縣五十七以笞決,路、府、州郡五十七卻以杖斷”[11]1350,濟南路官員向上級申明了這一問題后,這才有了大德九年(1305)的刑部答復進行釋明。從中國法制歷史的整體態勢上看,元初刑法改革確實有“輕刑”的趨勢。但須注意,元刑的各等和前代刑罰所代表的法律內涵并非一一對應,徒流刑折算后所形成的笞杖刑已經不能和前代笞杖刑作簡單直觀的比較,至少從等第上的多少作孰輕孰重的結論略顯草率。因此,這一復雜問題還是要放之具體的罪名和審判實踐加以判斷,切不可一言以蔽之。
(感謝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元史學教授王曉欣先生對文章的指點,拙文若有紕漏,由本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