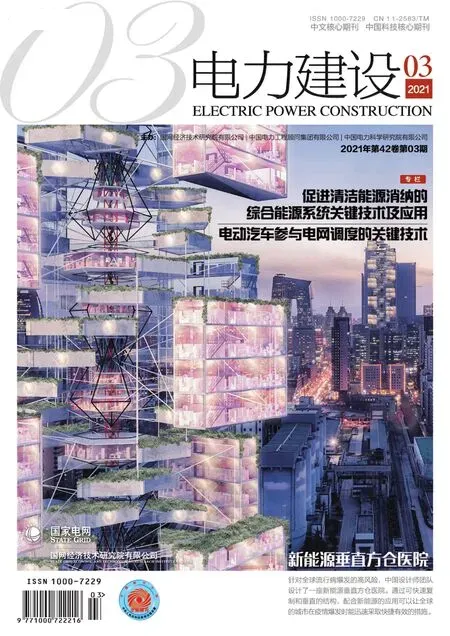預防暫態低頻減載的儲能容量配置多目標動態優化方法
劉慶楷,劉明波,陸文甜
(華南理工大學電力學院,廣州市 510640)
0 引 言
電網頻率是衡量電力系統中有功功率與負荷平衡的重要指標。如果大型電力系統由于發電損失而導致有功功率不足,將會使得系統頻率下降。頻率的下降首先由同步發電機的旋轉慣性阻止,然后同步發電機調速器動作,阻止系統頻率的進一步下降,這2個事件一般在事故發生后的幾十秒內完成。當系統遭遇大擾動如直流閉鎖或大機組脫機時,電網頻率快速跌落,當其達到系統頻率的限制值時,電網的低頻減載將會啟動,自動切除部分負荷,以保證系統穩定運行。實際上,在某些故障下,系統有足夠的能力使穩態頻率恢復到低頻減載的觸發頻率值之上,然而由于暫態過程中系統頻率的快速跌落,仍會導致暫態低頻減載的觸發[1]。如果能在系統受到大擾動時,快速向電網注入一定的有功功率,就能避免暫態低頻減載事件的發生,這對于增強電力系統的可靠性、減少切負荷導致的經濟損失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儲能由于具有充放靈活,響應速度快的特點[2-6],可以快速響應系統頻率變化,被認為是預防電網暫態低頻減載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年來,針對儲能參與電網快速調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文獻[7]將儲能等值成虛擬同步發電機,結合小信號線性化的系統模型,優化整個線性系統的H2范數以獲得最優的儲能虛擬慣性控制參數。文獻[8]提出了一種基于線性二次型調節器的儲能自適應控制方法,通過線性二次型調節器技術,確定最優的狀態反饋增益,并根據系統的實時頻率反饋調節儲能參數,以滿足系統的調頻需求。文獻[9]提出了一種基于儲能的自調節虛擬同步發電機控制方法,在虛擬同步發電機運行期間連續搜索最優參數,以最小化系統頻率的變化幅度。然而,上述研究在設計儲能的控制策略或優化儲能的控制參數時主要關注系統整體的頻率響應質量,忽略了控制過程中儲能的功率和能量限制。并且,上述控制方法均沒有對暫態調頻過程中的系統頻率值進行硬性限制,不能預防電網暫態低頻減載事件的發生[10]。
為了合理考慮儲能的功率和能量容量限制,同時預防電網暫態低頻減載,文獻[11]針對墨西哥某實際獨立電網,以最小化儲能配置成本為目標,將儲能的容量約束和系統頻率約束加入到動態模型中,聯合優化儲能的控制系數和參與快速調頻的儲能容量,以避免電網在嚴重事故發生時觸發低頻減載。文獻[12]針對澳大利亞的某個實際微電網,采用灰狼優化算法,同時優化儲能參數和參與微電網快速調頻的能量值,以最小儲能配置成本獲得滿足系統要求的頻率響應。文獻[13]從理論上推導了暫態過程中系統頻率變化的非線性表達式并對其進行線性近似,并在此基礎上得到預防電網暫態低頻減載的最優儲能參數與容量配置。上述文獻將儲能的容量約束和系統頻率約束加入到動態優化模型中,并以最小化儲能成本為目標對預防電網暫態低頻減載的儲能進行配置。然而,上述文獻對儲能的輸出功率約束均采用簡單的上下限不等式約束描述,不能準確描述儲能的輸出功率限制。由此得出的儲能功率容量配置結果為功率不加限制時的儲能輸出功率最大值,不一定為儲能在最優控制參數下對應的最優儲能功率容量,在最優控制參數下,存在更小的儲能功率容量可以滿足系統頻率安全約束[14]。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本文采用基于儲能飽和輸出限幅環節的分段函數約束對儲能的輸出功率進行精確表達。
此外,上述預防暫態低頻減載的儲能容量配置模型中,都只考慮儲能的配置成本目標,由此得到的最優儲能配置方案在應對預想的大擾動時,將使得系統頻率的最低點容易靠近低頻減載的觸發值,缺乏安全裕度[15]。因此,本文提出一種預防暫態低頻減載的儲能容量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旨在同時考慮儲能配置成本和暫態頻率調節性能2個相互沖突的目標。為精確表示儲能的功率輸出限制,采用具有分段函數約束的儲能動態模型,并采用大M法對分段函數約束引入的非線性問題進行處理。然后采用隱式梯形積分法將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轉化為多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模型。最后采用規格化法平面約束法和CPLEX求解器獲得上述多目標儲能容量配置問題的帕累托最優解。
1 電力系統等值頻率響應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電力系統需要儲能參與快速調頻的場景,主要考慮電力系統的固有頻率特性與一次調頻過程,而二次調頻由于時間尺度較大,不在本文的考慮范圍之內。在一個具有N臺發電機的多機系統之中,假設所有發電機以相同的頻率擺動,可以獲得圖1所示的含儲能的電力系統等值頻率響應模型[1]。

圖1 電力系統等值頻率響應模型Fig.1 Equivalent frequency response model of power system
假設t=t0時,電力系統發生了一個大的擾動(如直流閉鎖、機組脫機、負荷突增等),根據圖1的頻率響應模型,可以得到頻率與不平衡功率之間的微分方程表達式:
(1)
式中:Heq為多機系統的等值慣性常數;f0為電力系統標稱頻率;Deq為負荷阻尼系數;Δf(t)為電力系統實際頻率與標稱值的偏差值;ΔPm(t)為發電機一次控制器提供的機械功率增量;ΔPess(t)為儲能注入網絡的功率;ΔPe(t)為大擾動中損失的功率或者突增的負荷功率。
等值慣性時間常數的計算公式為:
(2)
式中:SB,i為系統中同步發電機i的額定功率;Hi為同步發電機i的慣性常數;SB為系統的基準功率。
根據圖1,同步發電機一次控制器提供的機械功率增量可以用含等值調速器-渦輪機時間常數Tg和等值下垂系數R的一階模型表示,寫成微分方程的形式為:
(3)
等值下垂系數R可由各發電機的下垂系數Ri計算得出:
(4)
在本文中,儲能采用PD控制器及限制環節進行等效。采用PD控制,儲能部分的注入功率與系統的頻率變化率成正比,可以有效降低暫態過程中的系統頻率變化率。而且在頻率下降的過程中,PD控制器可以快速感知電網的頻率變化,迅速增加儲能的輸出功率,提供快速調頻服務,起到支撐電網頻率的作用[16]。由于限制環節的存在,儲能的實際輸出功率為分段函數形式。假設儲能初始的輸出功率為0,儲能的實際輸出功率ΔPess(t)可表示為:
(5)
式中:Pmaxess為儲能輸出功率上限,即為儲能所需要配置的功率容量;ΔPchoose(t)表示采用PD控制器后不加限制的儲能理想輸出功率,根據圖1可表示為:
(6)
式中:KD、KP代表PD控制器的控制參數;Tess代表儲能的時間常數;X(t)為引入的中間變量。
2 含分段函數約束的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
本文考慮的多目標優化問題包括2個目標:一是最小化儲能容量配置成本;二是最優化系統的暫態頻率調節性能。儲能配置成本分為功率容量成本和能量容量成本。儲能的功率容量決定了儲能在整個頻率響應過程中輸出功率的上限,能量容量決定了儲能參與調頻過程的持續時長。為了量化系統的暫態頻率調節性能,本文將暫態過程中頻率偏差平方的積分值作為目標之一加入到優化問題之中,結合第1節的電力系統等值頻率響應模型,構造出具有分段函數約束的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
2.1 目標函數
第1個目標函數為最小化儲能的配置成本,考慮儲能的功率容量與能量容量,可得:
minf1=c1Pmaxess+c2Emaxess
(7)
式中:Emaxess為儲能需要配置的能量容量;c1和c2分別為單位功率與單位能量成本。
第2個目標為最優化調頻過程中的性能指標。由于暫態過程中頻率偏差的正負性不定,所以本文將頻率偏差的平方值在整個暫態過程中的積分值作為目標函數,用于衡量儲能參與系統快速調頻的效果[2]。

(8)
式中:t0為暫態過程開始的時刻;tf為暫態過程結束的時刻。
2.2 約束條件
2.2.1系統動態頻率特性約束
在本文中,系統的動態頻率特性包括系統的固有頻率特性約束、發電機一次調頻特性約束以及儲能的輸出功率約束,即為由式(1)、式(3)、式(5)、式(6)組成的微分方程組,用緊湊的形式來表達,如式(9)所示:
f(x,Pmaxess)=0
(9)
式中:x=[Δf(t), ΔPm(t), ΔPess(t), ΔPchoose(t)]T,為電力系統等值頻率響應模型的狀態變量。
2.2.2儲能運行約束
儲能在參與調頻的動態過程中,除了需要滿足式(5)和式(6)所示的輸出功率約束之外,還須滿足如下運行約束條件:
(10)
ΔPd(t)+ΔPc(t)=ΔPess(t)
(11)
ΔPd(t)·ΔPc(t)=0
(12)
(13)
式中:ΔPd(t)代表儲能系統放電功率;ΔPc(t)代表儲能系統充電功率;ηd代表儲能系統的放電效率;ηc代表儲能系統的充電效率。式(10)代表儲能的能量轉移約束。
同時,為了延長儲能的使用壽命,避免儲能過充過放,儲能的荷電狀態(state of charge,SOC)應維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CSOCminEmaxess≤Eess(t)≤CSOCmaxEmaxess
(14)
式中:CSOCmin、CSOCmax分別為儲能荷電狀態的下限和上限。
2.2.3系統運行安全約束
如上文所述,配置儲能的目的是在系統發生嚴重事故后,通過儲能的快速出力避免暫態低頻減載的發生,因此引入了暫態過程中系統運行的安全約束:
Δfmin≤Δf(t)≤Δfmax
(15)
(16)
式中:Δfmax和Δfmin分別為最大和最小頻率偏差值。式(15)為系統頻率的安全約束,在暫態過程中系統的頻率不得小于低頻減載的觸發頻率,同時也不能大于系統規定的頻率上限;式(16)為系統頻率變化率(rate of change of frequecny, RoCoF)約束,在暫態過程中系統的頻率變化率不得大于系統規定的最大值以保證系統的安全運行。
3 將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轉化為多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模型
第2節所提的多目標動態優化問題難以直接求解,本節采用大M法[17]和隱式梯形積分法,將本文提出的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轉化為多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模型。
3.1 微分方程與積分方程代數化
將式(8)由積分方程寫成代數方程,可得:
(17)
式中:tk代表第k個具體的時刻;h代表步長;n代表總時刻數。
通過隱式梯形積分法將微分方程式(1)、式(3)、式(6)轉化為代數方程,可得:
(18)
ΔPm(tk+1)-ΔPm(tk)=
(19)
(20)
(21)
ΔPimba(tk)=ΔPm(tk)+ΔPess(tk)-
ΔPe(tk)-DeqΔf(tk)
(22)
將儲能能量轉移約束的積分表達式式(10)代數化。設儲能參與調頻的初始能量值為最大能量值Emaxess的α倍(0<α<1),把式(10)由積分形式改寫成差分形式:
Eess(0)=αEmaxess
(23)
Eess(tk+1)=Eess(tk)-h[ΔPd(tk)/ηd+ΔPc(tk)ηc]
(24)
3.2 儲能運行約束線性化處理
本文采用大M法對非線性約束式(12)及分段函數式(5)進行線性化處理。
1)對非線性的式(12),在時刻tk引入一個整數變量U1(tk),得到差分后的ΔPd(tk)與ΔPc(tk)的線性化表達式:
0≤Pd(tk)≤M[1-U1(tk)]
(25)
-MU1(tk)≤Pc(tk)≤0
(26)
式中:M為一個充分大的正數。
2)對儲能輸出功率的分段函數表達式,將式(5)改寫為:
(27)
式中:Nbig是一個充分大的正數。
在時刻tk引入3個0-1變量Z1(tk)、Z2(tk)、Z3(tk),以及3個連續變量ΔPess1(tk)、ΔPess2(tk)、ΔPess3(tk),通過大M法可以將式(27)式轉化為:
ΔPess(tk)=ΔPess1(tk)+ΔPess2(tk)+ΔPess3(tk)
(28)
Z1(tk)+Z2(tk)+Z3(tk)=1
(29)
-Nbig-ΔPchoose(tk)≤M[1-Z1(tk)]
(30)
ΔPchoose(tk)-(-Pmaxess)≤M[1-Z1(tk)]
(31)
-Pmaxess-ΔPchoose(tk)≤M[1-Z2(tk)]
(32)
ΔPchoose(tk)-Pmaxess≤M[1-Z2(tk)]
(33)
Pmaxess-ΔPchoose(tk)≤M[1-Z3(tk)]
(34)
ΔPchoose(tk)-Nbig≤M[1-Z3(tk)]
(35)
-MZ1(tk)≤ΔPess1(tk)≤MZ1(tk)
(36)
-MZ2(tk)≤ΔPess2(tk)≤MZ2(tk)
(37)
-MZ3(tk)≤ΔPess3(tk)≤MZ3(tk)
(38)
ΔPess1(tk)≤-Pmaxess+M[1-Z1(tk)]
(39)
ΔPess1(tk)≥-Pmaxess-M[1-Z1(tk)]
(40)
ΔPess2(tk)≤ΔPchoose(tk)+M[1-Z2(tk)]
(41)
ΔPess2(tk)≥ΔPchoose(tk)-M[1-Z2(tk)]
(42)
ΔPess3(tk)≤Pmaxess+M[1-Z3(tk)]
(43)
ΔPess3(tk)≥Pmaxess-M[1-Z3(tk)]
(44)
至此,經過大M法和隱式梯形積分法的處理,本文提出的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可以轉化為如下的多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問題:

(45)
對于轉化后的多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問題,可以采用規格化法平面約束法[18-19]將其轉化為一系列單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問題,再對得到的單目標優化問題調用CPLEX求解器進行求解。本文所提方法的流程如圖2所示。
4 算例分析
為驗證本文所提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與所提算法的可行性與有效性,本文采用IEEE 24節點系統進行仿真計算。儲能的類型采用主流的磷酸鐵鋰電池,其充放電效率都設為90%,即ηd=ηc=0.9,儲能的單位功率成本c1為1 100元/kW,單位容量成本c2為2 000元/(kW·h)[20]。該系統的接線如圖3所示。其總負荷為2 850 MW,該系統的基準功率為100 MV·A,額定頻率為50 Hz,低頻減載觸發的觸發頻率為49.5 Hz[5],系統允許的最大頻率變化率為0.5 Hz/s,仿真的持續時間為100 s,儲能的接入節點為22號節點。系統頻率響應模型的等值參數[21]、SOC上下限[22]以及優化所需的其他參數如表1所示。

圖2 多目標動態優化流程Fig.2 Flowchart of the multi-objective dynamic optimization

圖3 IEEE 24節點系統接線圖Fig.3 Connection diagram of IEEE 24-bus system
假設位于母線18的輸出功率為400 MW的發電機脫機是預想的整個系統中最嚴重的事故,針對此極限場景進行多目標儲能配置,用本文的方法求得的多目標問題的帕累托前沿如圖4所示。

表1 IEEE 24節點系統參數Table 1 Parameters of IEEE 24-bus System

圖4 儲能配置兩目標優化模型的帕累托前沿Fig.4 Pareto frontier of b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for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由圖4可知,采用本文方法求得的帕累托前沿分布均勻,具有較好的求解效果。通過模糊隸屬度函數和熵權法[23],可以得到最優折中解。
為了驗證本文所提多目標模型的有效性,將多目標模型所得的儲能配置(方案1)與單目標模型結果對比。其中,僅優化目標函數1的儲能配置為方案2,僅優化目標函數2的儲能配置為方案3。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方案2配置的儲能功率和能量容量最小,其所對應的儲能配置成本目標值f1最小,然而此時系統的頻率偏差平方的積分值f2最大;方案3配置的儲能功率和能量容量最大,使得系統的頻率偏差平方積分值最小,但是卻使得儲能配置成本最高。而在方案1中,由于同時考慮了成本和調頻效果目標,可以在改善系統頻率的同時降低儲能的配置成本。3種配置方案對應的系統頻率變化、系統頻率變化率以及儲能輸出功率對比如圖5—7所示。其中圖5—7均通過將儲能配置方案輸入搭建的Simulink仿真模型進行仿真得到。

表2 3種儲能配置方案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three schemes for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圖5 3種配置方案的系統頻率曲線Fig.5 System frequency response curves under three schemes for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圖6 3種配置方案的系統頻率變化率曲線Fig.6 Curves of rate of frequency change under three schemes for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從圖5和圖6可知,采用多目標優化得到的最優折中解,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得到幾乎與方案3配置一樣的頻率調節效果。與僅優化儲能配置成本的配置方案2相比,方案2的系統頻率最低點十分靠近低頻減載的觸發頻率,而方案1的頻率最低點則相對遠離邊界值,保持了一定的安全裕度,體現了多目標優化的效果。采用最優折中解配置方案,與不配置儲能相比,頻率最低點提升了0.55 Hz,頻率變化率提升了0.4 Hz/s,起到了較好的配置效果。

圖7 3種配置方案的儲能輸出功率曲線Fig.7 Output power curves of energy storage under three configuration schemes
圖8為儲能配置方案1的SOC變化曲線。由于儲能的初始SOC為0.8,仿真事故為脫機事故,需要儲能系統注入功率,所以使得儲能系統一直處于放電狀態,SOC一直處于下降的狀態。儲能系統的SOC在0.2~0.8的區間內變化,滿足了儲能的安全運行需求。由此得知,經過多目標優化之后選取的最優折中解的方案1,既能保證系統遭遇嚴重事故時避免暫態低頻減載的發生,又能保證儲能運行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圖8 對應配置方案1的儲能SOC變化曲線Fig.8 SOC curve under energy storage configuration scheme 1
為了驗證所提方法的準確性,將求解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得到的系統頻率變化曲線與將儲能配置方案作為Simulink仿真系統參數得到頻率仿真曲線進行對比,結果如圖9所示。其中用于對比的方案為最優折中解的配置方案。

圖9 采用仿真模型與計算模型得到頻率變化曲線對比Fig.9 Comparison of system frequency-response curves from simulation and calculation model
從圖9可以看出,采用仿真模型得到的系統頻率變化曲線與采用多目標優化計算模型得到的頻率變化曲線吻合的精度較高,驗證了多目標動態優化計算模型的準確性。
5 結 論
本文基于電力系統等值頻率響應模型提出了適合儲能容量配置的具有分段函數約束的多目標動態優化模型,同時考慮了儲能配置成本和暫態頻率調節性能2個相互沖突的目標,重點解決了如何將其轉化為多目標混合整數二次規劃模型。
通過IEEE 24節點系統的仿真分析,結果表明,采用本文提出的儲能容量配置多目標動態優化方法,在400 MW的發電機脫機時,通過配置255.3 MW/4.931 MW·h的儲能后,頻率最低點提升了0.55 Hz,頻率變化率提升了0.4 Hz/s,在電網遭遇較大的事故時,可以有效地避免暫態低頻減載的觸發,并且保留了一定的暫態頻率安全裕度,上述結果驗證了所提多目標儲能配置模型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