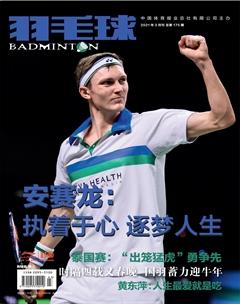盧聰聰:熱愛,以文字的力量
麥延

獨立成長 依賴球隊
盧聰聰是廣西人,家在柳州,但在河池長大。盧聰聰的父母都是數學教師,父親雖不教體育,但酷愛體育,在學校里還帶過籃球隊訓練,所以一心希望盧聰聰也能愛上體育。6歲那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讓盧聰聰正式開始接受羽毛球訓練。
練了大概3年時間,盧聰聰便自己背起行囊,提著收拾好的行李,坐上了從河池前往南寧的火車。正是在9歲這一年,盧聰聰來到南寧體校,開始了全寄宿的生活。那段時間,他上午訓練,下午上課,晚上晚自習,生活起居全部自理,不滿10歲的他過著大多數同齡孩子都還沒開始體驗的離鄉背井的寄宿生活,況且那還是體校。
習慣嗎?“說不上抗拒。”
喜歡嗎?“說不上討厭。”
這是盧聰聰今時今日的回答。現在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時光,盧聰聰還是對這些問題心存猶豫。沒有幾個孩子會希望9歲就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也沒有很多孩子會真的享受在體校邊吃苦、邊自立的節奏,可在盧聰聰眼里,他也沒那么不喜歡這里,他也沒那種迫切的想家情節。
這可能就是盧聰聰從小就培養起來的性格,他獨立,甚至被一些人說是“孤獨癖”,但他對球隊卻是萬般依賴的。從小時候在體校,到后來先后進了廣西隊和國家二隊,再到退役后當教練、帶隊伍、搞訓練,他這三十多年都生活在不同的羽毛球隊里。他喜歡待在球隊,也習慣了待在球隊,不管是什么角色。
曾經輝煌 卻遭打擊
14歲那年,盧聰聰順利進入廣西隊,為這個隊伍效力了12年。1998年,18歲的盧聰聰在福州參加了當年最后一期世青賽集訓,并通過集訓結束后的調賽進入國家二隊。盧聰聰當時的成績是男單第三名,同批的還有同是來自廣西的陳郁,他是當年世青賽的男單第三名。比賽的第一名是來自北京的張揚,他是當年世青賽男單冠軍。
當年,廣西男隊生力軍勢頭很猛,除了盧聰聰,還有如今的國家一隊男單主管教練陳郁,以及曾在1998年搭檔蔡赟奪得世青賽男雙亞軍的姜山。時至今日,全國青年羽毛球錦標賽的團體賽依然與當年一樣,由兩個單打和一個雙打組成。當年,盧聰聰和陳郁分別打一場單打,陳郁和姜山搭檔男雙,三個男孩曾連續三年奪得全國青年錦標賽的男團冠軍。
2000年,盧聰聰奪得全國青年錦標賽男單冠軍,他本以為這是又一個上升的臺階,卻沒想到在那之后遭遇巨大的傷病襲擊。因為腰傷,盧聰聰長時間缺席訓練,傷情最嚴重時,睡覺也受到影響,當時他的右側腰碰到床板就疼,人只能往左側身睡。
感嘆過往 推己及人
受傷后至2006年正式退役,盧聰聰感覺這段時光過得很沒有意義。他現在常會感嘆,如果當年球隊有一位職業生涯規劃師,或者是生活中有一位良師益友能跟他系統說說一位職業羽毛球員的發展該是怎樣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很多球員就會有更不一樣的人生。
受此啟發,盧聰聰如今在面對自己的隊員時,會經常跟他們說這方面的話題。比如說,10歲時需要練什么,15歲時會遇到什么機會,18歲時應該怎么沖,23歲時應該怎么保持,26歲時該怎么規劃未來,不一而足。其實,這也折射出時代的變化。現在的運動員退役時的選擇比以前多太多了,當年的盧聰聰正是那個沒有意識、沒有方向的迷茫少年。
盧聰聰說自己是幾乎沒有社交能力的人,因此有時會在無意中得罪別人或失去機會。所以,他在退役后選擇在南寧單干,自己當教練做業余培訓。現在,他來到了重慶渝北區,與張亞雯合作執教渝北區羽毛球隊。在盧聰聰現在的隊伍里,最大的球員才12歲,所以這更像一次重新再來的青訓機會,他很在意。
愛讀愛看 寫球評球
特立獨行和不善交際都是盧聰聰的標簽,不知何為因,何為果,但這兩點特質共同培養出他在羽毛球之外的愛好——寫作。
早在球員時代,盧聰聰就是一個用心想球、喜歡自己思考鉆研和探索的人。早在青年隊時,他就養成了寫作的習慣,可能也稱不上是寫作,只是把想到的東西一字一句地寫在筆記本上,包括訓練日記、比賽心得、觀賽體會、戰術研究等。
退役后,盧聰聰把這個愛好衍生為一項工作,在當教練的同時,為不同的平臺供稿,將他銳利的目光化作犀利的觀點,收獲了眾多讀者的支持。在國家隊時,盧聰聰閱讀了大量文學期刊,直到現在,閱讀和思辨成為他的一種習慣,看文史類的書,看紀錄片以及各種談話類節目,看各級別羽毛球比賽。
盧聰聰看球的量很大,今年1月的泰國三站比賽他看了全部比賽的2/3,他還當起了中國體育直播TV的兼職主播解說,在直播間里和球迷們分享觀賽體會。那三周里,只要不用訓練,他就一邊看主屏幕場地,另一邊開著平板電腦看另一場地的比賽,嘴上解說著,并用筆記錄著觀賽體會,堪稱“四核運作”。

五年前,盧聰聰開始兼職學習做媒體的工作。當讀者慢慢增加后,他的文風也有了些微變化,變得比以前克制了,“因為要考慮讀者的感受。不過,很多讀者還是喜歡刺激的文字,俗稱‘標題黨,很多人還是看熱鬧不嫌事兒大。”盧聰聰笑著說。
寫了三十年,進入媒體領域兼職了五年,盧聰聰的文筆越來越成熟和有風格了。他現在的自評是:寫作仍然屬于小學生級別,但觀點起碼是專業且直接的。今年,盧聰聰進駐《羽毛球》雜志,擁有了自己的“聰聰說球”專欄,期待著新一年彼此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