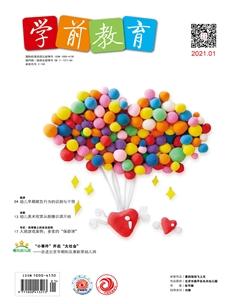基于“分析-學習-練習”的微教研
劉胤



教育活動目標是幼兒園目標體系中最具體、最底層、最下位的,其特點就是明確、具有可操作性,能具體指導、調控教師的教學過程。而在實踐中,發現很多老師,尤其是年輕教師,將《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要》)的目標作為具體的教育活動目標,甚至作為一學期、一學年皆通用的、籠統的、概括的大目標。其實,這些老師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我知道要考慮孩子的年齡特點和學習方式,結合《指南》《綱要》制訂具體明確、操作性強的、適合的教育活動目標,但是卻寫不出來,于是只好照搬照抄。”
這不禁引發我的思考:既然教師對于制訂目標的原則、要求等理念性的知識都明白,制訂出來的教育活動目標為什么“大而空”呢?究其原因是還沒有將理念真正轉化為實踐。當前一致的觀點認為,制訂目標的基石是行為目標理論,因為它能使目標可理解、可把握、可操作,能夠指導教師具體實施教育活動并評價其教育活動的效果。行為目標理論是幫助教師制訂具體可操作目標的有利途徑。于是,我基于行為目標理論設計、組織、開展了“分析-學習-練習”的微教研活動。
分析——發現行為目標的內涵
活動一開始我就直奔主題說明:本次教研活動要和大家一起學習一種“招數”,讓每個人制訂的目標變得具體、可操作,你們愿意嘗試一下嗎?話題一下子說到教師的心坎上,大家對此次教研充滿了期待。
接著,我依次拋出了三條不同領域、不同年齡班的教育目標,讓教師集體共讀。
例1:小班藝術活動“我笑起來真好看”目標之一:通過照鏡子觀察,能畫出自己臉上的眼睛、鼻子、嘴巴等主要部位。
例2:中班語言活動“我喜歡你”目標之一:通過自主閱讀、師幼共讀、完整閱讀,基本能讀懂畫面內容,初步了解故事的連環情節。
例3:大班社會活動“學做小學生”目標之一:通過看視頻、觀察討論的方法,了解小學生課堂的坐姿、站姿、舉手發言交流等基本規范。
讀了如上教育活動的目標,老師們有什么思考與想法?
教師1:我認為這三條目標都是很明確的、不籠統的,例如畫出自己的臉、讀懂畫面內容……
教師2:這些目標明顯體現出小、中、大班的年齡特點。
教師3:我看了這些目標就知道這個教育活動教師要做什么,孩子要干什么,以及教師的方法,比如看視頻、照鏡子等。
教師4:我還看到了孩子最終學到的程度,比如,畫出……了解……
教師5:我覺得這些目標是能特定于本班的活動,在其他班級,或許不一定適宜。
……
在教師針對三條目標進行頭腦風暴式的討論和碰撞中,我及時把她們的思考用表格歸類的方式,記錄在黑板上,讓老師們進一步看到:設計教學目標,還要思考、設計好幼兒要掌握的關鍵經驗到底是什么,分析我們班孩子可能學到什么程度,我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教……一條具體可操作的目標背后是有內涵的。那么,其內涵中有哪些因素?它們之間是怎樣的關系?背后有怎樣的理論支持?由此,自然引出了“行為目標”這個概念。
學習——了解行為目標三要素
之前的教研備課中,我對行為目標的理論以及三要素先學、先知、先覺,在接下來的學習環節中,就開始引著老師經歷像我一樣的學習過程。
學習開始,我并沒有把我搜索到的文獻發給老師,而是拋出“行為目標”這個關鍵詞,大家現場利用手機自行搜索學習5分鐘。
接下來,結合對上面三條目標的分析,分享自己的學習思考。
教師1:我查閱到,行為目標的定義是以兒童具體的、可被觀察的行為表述來設計目標,它指向的是通過教育活動兒童所發生的行為變化,目標設計中關注的是可觀察到的行為結果,行為目標具有客觀性和可操作性。結合之前的三條目標,我認為具體的、可操作的目標都是行為目標,我以后制訂目標也要以此為標桿。
教師2:我查閱到行為目標的三要素:一是做什么,即說明具體的行為;二是怎么做,即說明上述行為的條件;三是做得如何,即評定上述行為的標準。
教師3:根據X老師,我發現了咱們之前表格的第一列,就是做什么,即幼兒學什么內容;第二列是怎么做,即我們的教學形式;第三列說的是做得如何,即效果和程度。
基于教師的自主學習、討論、分享、發現,我們及時進行了總結,備課中一個教育活動的每一條目標都要思考三個要素。1.學什么(內容):學習者通過學習能做什么,以便教師能夠觀察學習者的行為,了解目標是否達到。2.怎么做(條例):這些行為在什么條件下產生。3.做得如何(程度):合格行為的最低標準。讓教師看到行為目標理論下產生的目標,確實是具體明確、可操作的。(見表1)
練習——運用三要素修訂目標
當教師從理論上理解了制訂一條具體、可操作的目標需要考慮的三要素之后,進入練習階段:以年齡班為單位,對照備課本,對任意一個活動的目標進行修訂。(見表2)
通過“分析-學習-練習”的教研,總結出具體、可操作的適宜目標是指向孩子的發展的、適合孩子的,這樣的目標我們認為有三看見:一是看見孩子在活動中做什么;二是看見符合本班幼兒的適宜的學習方式;三是看見活動的程度與結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行為目標理論對教師設計具體、可操作的教育活動具有指導作用,但并不是行為目標越具體越好,要在概括化與具體化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度”。同時,行為目標強調的是那些可以觀察的外顯的行為變化,但兒童的發展又有許多方面難以轉化為這些行為指標,所以還需要基于對孩子真實行為的觀察,對目標進行調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