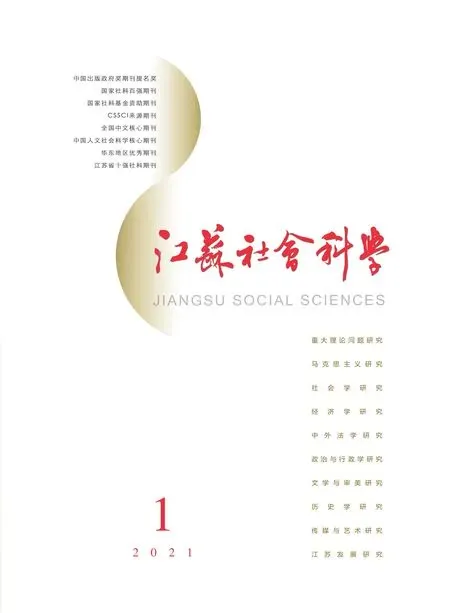孟京輝戲劇的國外演出、接受與反思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詳細梳理孟京輝戲劇在國外演出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分析國外觀眾對其戲劇的接受,呈現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語境下接受的內容,反思背后的緣由,挖掘戲劇與人的存在關系,以期在戲劇本質、戲劇本體、戲劇功能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啟示。本質上,戲劇是劇場中洋溢的渾然一體的戲劇精神,戲劇是所有的參與者——編劇、改編、導演、演員、舞美和觀眾等共同創造的集體性藝術作品;而功能上,筆者覺得戲劇可以創造劇場中共享的戲劇精神空間,亦可稱之為戲劇共同體。從孟京輝戲劇國外演出的具體接受情況可以看出,他的戲劇極具先鋒性和爭議性。
在中國當代劇壇,孟京輝是繼曹禺、老舍、林兆華等人之后又一位炙手可熱、舉足輕重的人物,其銳意創新的先鋒戲劇可謂獨樹一幟、獨領風騷。無論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紀初的轉型發展期,以及新世紀初直至現在的多元探索期,他的戲劇都極具沖擊性和爭議性。孟京輝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戲劇家,他執導的戲劇不斷走出國門,在世界許多國家演出并產生廣泛影響,在中外戲劇交流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本文試圖梳理孟京輝戲劇在國外演出的情況,在此基礎上呈現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語境下國外觀眾對其戲劇接受的內容,反思背后的緣由,挖掘戲劇與人的存在關系,以期在戲劇本質、戲劇本體、戲劇功能等方面提供有益啟示。
本文探討的孟京輝戲劇作品,主要指孟京輝改編、執導的戲劇。其中,有些孟京輝親自參加表演。它們都有著明顯的孟氏戲劇風格,體現了孟京輝戲劇深刻的人性關懷、普世的戲劇精神和靈動的戲劇表演。
一、孟京輝戲劇的國外演出
時間層面上,可以把孟京輝戲劇的國外演出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20 世紀90 年代、2000 年到2009年、2010年到2019年。
整個1990年代,孟京輝一共攜作品出國演出三次,所演出的三部戲劇分別是1993年赴德國演出的《等待戈多》、1994 年赴日本演出的《思凡》以及1995 年赴日本演出的《我愛XXX》。其中,《等待戈多》和《我愛XXX》都是比較敏感的戲劇作品,有心人會讀出作品濃烈的政治意味。
與前一個十年戲劇的政治性相比,2000到2009年,走出國門的孟京輝戲劇具有以下兩個特征:首先,這些作品更加中國化了。無論是《琥珀》《關于愛情歸宿的最新觀念》,還是《鏡花水月》,都在舞臺上呈現當下中國的面貌。即便《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盡管改編自達里奧·福的作品,但其百分之八十的戲劇元素都是原汁原味中國的。其次,這些戲劇以參加戲劇節演出為主,商業巡演很少。不過,《關于愛情歸宿的最新觀念》是出于康開麗與孟京輝的友誼,得以在美國演出。孟京輝只是編劇身份,康開麗才是該作品在美國演出的導演。
2000年,應“都靈藝術節”組委會邀請,孟京輝遠赴意大利,執導演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取得了巨大成功,榮獲“2000年度意大利都靈藝術節最佳戲劇作品”。當時,“在都靈,達里奧·福攜夫人一起觀看了演出,并給予非常高的評價,演出在當地也引起轟動,不少評論表示驚訝,稱孟京輝賦予這個戲更強烈的人民性”[1]張爽:《孟京輝戲劇展演〈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2014年10月31日,http://news.hsw.cn/system/2014/10/31/052041052.shtml。。2005年5月,《琥珀》劇團來到新加坡,作為新加坡藝術節的開幕大戲,于5月26日~5月29號在新加坡艾斯普拉納德國家大劇院上演。演出前,新加坡媒體充滿期待,因為“孟京輝和廖一梅是中國當代戲劇的搖滾巨星”、“該劇是新加坡藝術節、香港藝術節與中國國家大劇院合作出品”、“金馬獎影帝劉燁與資深演員袁泉聯袂演出”[2]Hong Xinyi,“Heart 2 Heart-The rock stars of Chinese Theatre Liao Yi Mei and Meng Jinghui Share a Passion for the Arts and Each other”,The Straits Times,2015-05-21.。新加坡官方對于該劇期待值很高,新聞、通訊及藝術部長李文獻,總理公署部長、財政部兼交通部第二部長陳惠華以及國家藝術委員會主席劉太格,都參加了演出前的雞尾酒會,也在場觀賞了整個演出[3]Clara Chow,“Art Fest Opens with Splendid Colors by the Bay”,The Straits Times,2015-05-27.。2006年,美國戲劇學者和導演康開麗把孟京輝的戲劇作品《關于愛情歸宿的最新觀念》引入美國,《萊克辛頓民兵報》(Lexington Minuteman)刊發“萊克辛頓居民執導中國戲劇”(“Lexington Resident Directs Chinese Play”)一文,“作為塔夫茨大學教授,居住于萊克辛頓的克萊爾·康開麗本周帶來了與眾不同的作品,她將執導英文版的《關于愛情歸宿的最新觀念》,該劇將于四月八日(周六)在塔夫茨鮑爾奇競技場劇院上演”[4]Lexington Minuteman,“Lexington Resident Directs Chinese Play”,Lexington Minuteman,2006-04-06.。盡管《關于愛情歸宿的最新觀念》在國內演出并不成功,但是,經過康開麗的執導,在美國演出很成功,成功的原因在于“英文版的《關于愛情歸宿的最新觀念》有著實驗性的對話、獨特的美學風格和完美的舞臺設計”,這些形式上的創新“給觀眾留下很好的印象”[5]Kate Drizos,“Commentary:From Vampires to Vaudeville,Variety Graced Tufts’Stages”,Tufts Daily,2006-06-01.。2007年10月18日至10月20日,中國國家話劇院出品、由孟京輝導演的中國當代多媒體音樂話劇《鏡花水月》在墨西哥瓜納華托市塞萬提斯藝術節主會場主題劇場演出,這是中國文化部第一次派國家級戲劇團體參加拉丁美洲的藝術節,也是拉美觀眾有史以來欣賞到的第一部來自中國的當代戲劇作品。到了墨西哥后,當地媒體對于該劇非常感興趣,“2007年10月17日,《鏡花水月》的新聞發布會在塞萬提斯藝術節新聞中心召開,原本只約請了五家媒體的新聞會議廳被來自十五家媒體的將近20名新聞記者塞滿,記者們對來自中國的當代戲劇表現出極大的好奇,導演孟京輝、文學策劃廖一梅攜全體演員和樂隊成員參加了新聞發布會,這個來自中國的充滿青春氣息和實驗藝術色彩的戲劇吸引了各界媒體的關注”[1]新浪娛樂:《孟京輝新作〈鏡花水月〉縱橫拉美 中國戲劇遠航》,2008 年1 月15 日,http://ent.sina.com.cn/j/2008-01-15/15231877622.shtml。。
2010年到2019年,孟京輝戲劇的國外演出再次贏得了當地觀眾的接受和歡迎。《戀愛的犀牛》《兩只狗的生活意見》等經典戲劇作品演出場次不斷創造新紀錄,不斷更新所覆蓋的世界版圖。其中,《戀愛的犀牛》更是令人矚目。首演至2017年,“《戀愛的犀牛》在全世界89個城市累計達約1900場演出,巡演里程487,800公里,觀眾人次達70萬。它的劇本被翻譯成韓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羅馬尼亞文”[2]孟京輝工作室:《中國當代戲劇向歐洲劇壇吹響先鋒號》,2017 年2 月5 日,http://mt.sohu.com/20170205/n479972476.shtml。。眾多戲劇作品在國外的成功演出,不僅僅為孟京輝自己和他的戲劇團隊,也為整個中國當代戲劇贏得了榮譽。2014年,孟京輝執導的《活著》“是中國當代戲劇首次進入德國主流戲劇界的一次成功的演出”[3]中國國家話劇院:《〈活著〉赴德演出》,2014 年6 月16 日,http://www.ntcc.com.cn/hjy/gjpxhjl/201406/3ba046be010a44d99424218afa53d38a.shtml。;2015年,“由中國知名話劇導演孟京輝執導,廖一梅編劇的話劇《琥珀》日前在德國漢堡最負盛名的塔利亞劇院連續上演兩場。這是孟京輝繼2014年攜話劇《活著》首次亮相萊辛戲劇節后,再次進入德國主流戲劇界,展現中國當代話劇的風采”[4]陳磊:《中國話劇〈琥珀〉驚艷德國戲劇節》,2015年2月6日,http://www.xijucn.com/huaju/20150206/65755.html。。2017年,“孟京輝戲劇最新作品《九又二分之一愛情》受邀參加開羅國際當代實驗戲劇節,這是中國當代實驗戲劇首次進入阿拉伯語主流戲劇界,向非洲觀眾展示中國當代戲劇實力”[5]藝海劇場:《不看不知道有多耀眼的〈九又二分之一的愛情〉》,2017 年11 月1 日,http://www.sohu.com/a/201742038_778822。。2011年,孟京輝戲劇進入世界最負盛名的戲劇節之一——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不過,只是在OFF單元演出;到了2019年,有了質的飛躍,“由孟京輝執導的話劇《茶館》于去年烏鎮戲劇節首演,隨后受到阿維尼翁IN戲劇節的官方邀請,成為73年來第一部在阿維尼翁IN戲劇節公演的中國大陸劇目”[6]劉臻:《孟京輝〈茶館〉“開”進法國,年底北京首演》,《新京報》,2019年7月14日。。
可以說,從2010年到2019年,孟京輝戲劇完成了中國當代戲劇走出去的很多“零的突破”,也為他個人贏得了國際聲譽。2017年,孟京輝榮獲“埃及戲劇成就金獎”。“戲劇節開幕當天,開羅國際當代實驗戲劇節頒獎給了世界一流的劇院藝術,以表彰他們對世界戲劇的創新運動的貢獻,導演孟京輝從埃及文化部長的手中接過獎杯。”[7]藝海劇場:《不看不知道有多耀眼的〈九又二分之一的愛情〉》,2017 年11 月1 日,http://www.sohu.com/a/201742038_778822。2018年10月,“俄羅斯副總理塔季揚娜·戈利科娃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向孟京輝頒發俄羅斯‘普希金獎章’……普希金獎章為俄羅斯國家級獎章,專門頒發給在文化、藝術、教育、人文科學及文學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8]新浪新聞中心:《俄媒:中國著名戲劇導演孟京輝獲俄羅斯“普希金獎章”》,2018 年10 月30 日,https://news.sina.com.cn/o/2018-10-30/doc-ifxeuwws9559856.shtml。。
二、孟京輝戲劇的國外演出接受
孟京輝戲劇走出中國,登上國際戲劇舞臺,最能打動人的,是其作品內蘊的人的存在方式。就像著名戲劇學者譚霈生所說:“舞臺是一座‘實驗室’,藝術家把各種各樣的人物送進這座實驗室,以測定他(她)們是什么樣的人,從而探討人生的真諦。”[9]譚霈生:《譚霈生文集:戲劇本體論》,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頁。劇場和舞臺就是一個實驗室,可以創設一個逼真的社會語境,實驗的是人如何生存,關注的是個人如何堅守屬于自己的存在?這些在舞臺上如何呈現?
孟京輝戲劇刻畫了很多看似病態的人物,而事實上,正是這些看似病態的人物苦苦堅守自己的生存,也正是這樣的堅守打動了觀眾,給了他們自己堅守的動力和理由。比如《戀愛的犀牛》中的馬路。在劇中,馬路的話語刻骨銘心、深入骨髓:“什么東西讓我確定我還活著?——這已經不是愛不愛的問題,而是一種較量,不是我和她的較量,而是我和所有一切的較量。我曾經一事無成這并不重要,但是這一次我認了輸,我低頭耷腦地順從了,我就將永遠對生活妥協下去,做個你們眼中的正常人,從生活中攫取一點簡單易得的東西,在陰影下茍且作樂,這些對我毫無意義,我寧愿什么也不要。”[1]孟京輝:《先鋒戲劇檔案(增補版)》,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頁。從馬路的坦白中可以看出,重要的不僅僅是愛情,而是自我和萬物之爭。如果他放棄,他就會失去自我意志、自我感覺,即便過上正常日子,也沒有任何意義。馬路拒絕情感資本主義,拒絕自我異化,拒絕膚淺生活,通過擁抱感官和孤獨,他英勇地向情感資本主義宣戰。這也是他從明明身上感到的品質。明明和馬路一樣,執著而孤獨,堅持追求得不到的愛情。在馬特·伯恩看來,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戀愛的犀牛,因為“犀牛視力不好,身體高大、強壯、皮厚,雄性都有很大的犀牛角,但是,犀牛內心很柔軟、脆弱。犀牛可以是對戀愛中人的闡釋,脆弱,而且盲目,故事抵達人們心靈的黑暗深處。戲劇能打動人,因為我們人類都是戀愛中的犀牛”[2]Matt Byrne,“Chinese Director is Hoping to Win Over a New Audience Down Under”,Sunday Mail,2011-08-21.。
《活著》中的福貴,經歷人生種種,最后家人都離他而去,形影相吊,孤苦伶仃,卻又似乎與生命達成了某種和解。這種隱含的悲壯是一個人的,也可以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底。孟京輝覺得,“小說的情節只是理解這部作品的第一步,而我們在排演的時候更想突出人和命運交朋友的過程”。對于德國觀眾,他“希望大家在看完后不去說‘中國人活著很艱難’,而是‘人活著很艱難’”[3]王雨晨:《〈活著〉赴德國兩地演出 展中國當代戲劇魅力》,《中國文化報》,2014年2月11日。。作為主演的黃渤也很好地理解了作品的深刻人性內涵,領會了導演的意圖:“最根本的東西是余華原著的序里面‘這不是在講述一個悲慘的故事,而是在講述一個與命運為友的故事’。”[4]劉虹妤:《孟京輝話劇〈活著〉在柏林德意志劇院上演感動德國觀眾》,2014 年2 月10 日,http://news.cri.cn/gb/42071/2014/02/10/5931s4417145.htm。此劇在德國演出后,無論是戲劇呈現的故事、思想、觀念,還是呈現故事、思想、觀念的舞臺表演,都贏得了德國普通觀眾以及戲劇界知名人士的首肯,認為該劇表現的不僅僅是一個普通人在中國的歷史遭遇,也是一個普通人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經受的遭遇:“當一個人生活在底層,不斷地受到傷害,但是又一次次地站起來,獲得新的力量,并且愿意繼續活著繼續抗爭。我們都知道過去的這段歷史,我覺得這部戲非常有意思。”[5]劉虹妤:《孟京輝話劇〈活著〉在柏林德意志劇院上演感動德國觀眾》,2014 年2 月10 日,http://news.cri.cn/gb/42071/2014/02/10/5931s4417145.htm。民族性與世界性在這部戲劇作品中交融,而中國人溫柔的堅韌,通過這部戲劇的演出,觸動了德國人的心弦。所以,柏林德意志劇院院長烏爾里希·庫翁在演出后表示:“感謝中國國家話劇院帶來《活著》這樣一臺戲劇盛宴。觀眾在演出結束后集體起立鼓掌,標志著他們對于該劇有著非常高的評價。要知道在德國能讓觀眾衷心感謝一部戲劇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這部戲通過一個人的命運講述了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我們認為這部戲表述出的這段歷史是可敬的、真實的,也是觸手可及的。”[6]王雨晨:《〈活著〉赴德國兩地演出 展中國當代戲劇魅力》,《中國文化報》,2014年2月11日。
《兩只狗的生活意見》中,旺財和來福生存于無限擴張的城市世界,這樣的世界等級森嚴、潛規則盛行。底層的出路在哪?安得烈·富爾曼認為,這是一部現實的荒誕劇,“這是一個荒誕的故事,兩只狗顛沛流離,被關,被警察通緝,被黑幫欺辱,最后被毆打”。他看得比普通觀眾更為深入,“在瘋狂娛樂的下面,潛藏著嚴肅的悲哀的故事,用一種隱含的方式,呈現中國民工的生活,他們離開農村,到城里打工,經常被看作低等公民。在這個層面,戲劇里縈繞的痛苦讓人想起卓別林的《城市之光》”[7]Andrew,Fuhrman,“Two Dogs,Dark Chorus,and Lady Eats Apple”,https://www.australianbookreview.com.au/abr-arts/3627-melbourne-festival-two-dogs-dark-chorus-and-lady-eats-apple?tmpl=component&print=1,2016-10-14.。
戲劇的世界,除了故事、情節、動作和沖突等,還必須有合適的舞美和表演,這些是觀眾可以直接看到、聽到、感受到的,也是戲劇接受的重要載體。孟京輝的早期戲劇作品《思凡》,粘合了古今中外的越界情愛故事,加上新穎的舞臺演繹形式,“綜合了形體、啞劇、說唱、音樂、舞蹈、敘述、裝置、音響、燈光等表述手段”[1]胡星亮:《當代中外比較戲劇史論(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頁。。在很多研究者看來,它幾乎可以被看作是孟京輝的巔峰之作:“在1990年代,演出場次超過任何一部其他中央實驗話劇院的作品,為孟京輝贏得了最多關注,其戲劇儀式技巧成為孟京輝后來作品的典范。”[2]Bettina S.Entell,“Post-Tian’anmen:A new era in Chinese theatre,”Experimentation During the 1990s at Beijing’s China National Experimental Theatre/CNET,University of Hawaii,2002,p.173.《琥珀》在新加坡演出時,觀眾和學者們一致公認,該劇一方面直擊社會現實,另一方面,又能以精致的舞臺表現傳達能夠切入社會現實的戲劇藝術能量,“該劇具有MTV風格,場景自由切換,在兩個平行的故事間穿行,對話和意象完美融合,舞臺上展現的不僅僅是演員的身體動作,還有不斷閃現的搖滾、說唱以及中國武術”[3]Cheah Ui-hoon,“Provocative class act from China”,The Business Times,2005-05-28.。難怪琦巫宏認為,“中國國家話劇院的《琥珀》激蕩人心,引人入勝,才華橫溢,發人深省”,因為“它的都市感,可以在亞洲、北美或者歐洲的任何一個舞臺上演,與今天的后現代觀眾產生共鳴”[4]Cheah Ui-hoon,“Provocative class act from China”,The Business Times,2005-05-28.。《琥珀》赴澳大利亞演出后,它的舞美和表演同樣贏得了贊譽。佩姬·穆霍蘭深度欣賞《琥珀》的戲劇形式,認為其在寫實主義與寫意主義之間自由切換,“表演和舞臺的情緒一樣,變幻多端,忽而是深沉的現實主義筆觸,忽而是布萊希特的間離,直接向觀眾訴說,中間沒有任何過渡。盡管難以捉摸,演員們的表現很精彩”[5]Paige Mulholland,“Amber”,https://aussietheatre.com.au/reviews/ozasia-festival-amber,2015-10-03.。如此,舞臺上的《琥珀》已經不單單是一部話劇作品,而是有著戲劇靈魂的綜合藝術作品,各式各樣的技術與藝術技巧融合一起,試圖共同營造戲劇的質感和靈韻。
《戀愛的犀牛》赴澳大利亞演出后,很多觀眾和學者非常欣賞該劇的舞美和表演,認為這是一部“史詩般、有獨特中國風格的先鋒、實驗、狂熱的戲劇作品,把戲劇藝術推向極致。可以說它輕松、清澈,也可以說它厚重、繁復,舞臺設計有著半工業風格,懸著金屬框架的立方體,多面鏡子,升起的跑步機,堅硬的木制椅。戲劇后期,舞臺上空出現實質的水,高潮處,傾盆而下,形成壯美的暴雨情景”[6]Samela Harris,“Ozasia Festival-Animal Attraction on Grand Scale”,Advertiser,2011-09-16.。在這樣的舞臺上,演員可以自由進出戲劇情節,向觀眾傳遞內在的戲劇精神和藝術能量。莫里·布拉姆韋爾非常欣賞該劇靈活的表演形式以及舞臺上洋溢的自由精神,“演出過程中,不斷穿插合唱,評價愛情,形成強烈對照,馬路的朋友們取笑他的困境。同時,插入社會諷刺片段,比如電視評比文化和強行推銷的消費主義。戲劇有著緊張的節拍和情緒,彌漫于集體舞、太鼓式鼓點和不時的甜膩流行音樂”[7]Murray Bramwell,“Modern China as Seen by a Lovesick Rhino”,Australian,2011-09-19.。
近三十年來,孟京輝攜眾多戲劇作品走出國門,登上世界各地戲劇舞臺,向世界觀眾展示了當下中國戲劇的風采。演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重要的原因就是戲劇自身的定位——呈現和反思“人的生存”,讓戲劇舞臺和劇場成為人類世界的微型實驗室,呈現各種社會語境中人該如何生存。孟京輝的戲劇實踐,尤其是其人性關懷的深刻性、戲劇精神的普世性以及表演形式的靈動性,對于中國當代戲劇走出去,有著極大的借鑒價值。
三、孟京輝戲劇國外演出接受的反思
孟京輝覺得他的戲劇不僅僅是講故事,更重要的是靈魂的表演,戲劇精神的傳遞:“戲劇需要眼睛觀察審視現代生活,戲劇需要耳朵感覺聆聽世間萬籟,戲劇需要鼻子嘴巴呼吸時代之氣息,戲劇需要舌頭發出演講之辭,褒貶演繹人生狀態,戲劇需要身心體味擁抱劇場舞臺之瞬息萬變。”[8]孟京輝:《先鋒戲劇檔案》,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頁。二十世紀以來,戲劇有一種向精神轉向的趨勢,“無論是殘酷戲劇、質樸戲劇,還是環境戲劇、機遇劇……藝術家們一次次地回視戲劇的源頭,希望從祭奠儀式、民間節會、游藝雜耍中撿回戲劇藝術失落的生命力,尋找戲劇之所以成為戲劇的獨特本質”[1]林克歡:《戲劇表現的觀念與技法》,北京聯合出版社2018年版,第72頁。。這樣的轉向,在于尋找原初的渾整狀態,“在祭奠儀式中,演員與觀眾是渾然一體的,這就是戲劇活動的本質特征”[2]林克歡:《戲劇表現的觀念與技法》,北京聯合出版社2018年版,第73頁。。也是就說,戲劇的本質在于“戲劇共同體”的構建。劇場中,所有參與人員——編劇、導演、演員、工作人員和觀眾等都在戲劇之中融為一體,這樣的融合才是戲劇的本質。因此,能夠真正觸動人心的,必然是戲劇傳遞的藝術情感和能量。赴國外演出的孟京輝戲劇,讓觀眾震撼的,也只能是強烈的戲劇精神。正因如此,《等待戈多》在德國演出后,演員們得謝幕七八次,激動地在后臺來來回走動;《鏡花水月》在墨西哥演出后,觀眾們久久沉浸于戲劇之中,透過戲劇,看到當下世界每個人的精神真相;《活著》在德國演出后,觀眾感受到的是一個人在歷史的凄風苦雨中如何無奈而又不得不堅強;《戀愛的犀牛》在澳大利亞演出后,讓人回味的是商品社會中個人深層次追求的困難;《四川好人》在澳大利亞演出后,有些觀眾離開劇場后仍向天呼喊,那種好人難做的情緒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如果說戲劇的本質是劇場中洋溢的渾然一體的精神,那么,這樣的戲劇精神何以表現出來?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得回到戲劇本體。戲劇具有文學性和劇場性雙重特征,文學性主要與編劇和改編有關,劇場性與戲劇在舞臺上表演時劇場中發生的一切有關。因此戲劇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集體性藝術,是所有的參與者——編劇、改編、導演、演員、舞美和觀眾等的共同創造。從孟京輝戲劇國外演出的接受,能看出戲劇生發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其中最為普遍的問題是:戲劇表演有沒有固定程式或者形式?
戲劇表演有沒有固定程式或者形式?有沒有沒有形式的內容?有沒有沒有內容的形式?應該說,任何形式都表達或者表現了一定的內容。林克歡就認為:“面對藝術作品中形式與內容的關系這一命題,卻有共識,亦即:否定傳統的‘二元論’,持形式內容‘一元論’,強調內在的不可分性。”[3]林克歡:《戲劇表現的觀念與技法》,北京聯合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頁。在筆者看來,即便探討形式,問題的內核其實還是戲劇精神問題,戲劇形式與戲劇內容是不可拆分的。
在表演層面,孟京輝和另一位戲劇家賴聲川有類似理念,都強調即興表演。只是,賴聲川的即興表演是有指導的、事先有要求的,演員得即興取得什么樣的效果,“所謂集體即興創作,是指在沒有劇本的前提下,根據大綱和導演的情景設定,由演員即興發揮,導演在一旁指導,當演員找到了對的感覺之后,再加以歸納、成形。正因為如此,賴聲川所有的作品,排練時間都需要幾個月”[4]搜狐娛樂:《賴聲川舉行“戲劇開放日”請觀眾即興表演》,2008 年3 月24 日,http://yule.sohu.com/20080324/n255876127.shtml。。談到《四川好人》在澳大利亞的演出,孟京輝在接受采訪時提及自己的執導方式、演員特點和戲劇導向。這三個方面以常規的視角看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正反映他一直在營造的戲劇作品的“召喚結構”。執導方式上,孟京輝沒有明確演員該做什么或者如何做,甚至鼓勵“誤讀”,“我跟演員的一些交流需要一些誤讀,通過翻譯,演員就會問我很多問題,每次都會說yes,沒有必要回答對還是不對,我就貌似全聽懂了,因為他們說得很深,一大堆有關節奏、表演方式的,我說對,全是你對,你先做再說”。演員方面,背景和經驗經歷都不同,“合作的演員有不同的狀況,有的演員是19歲,剛剛從戲劇學校畢業,然后參演很多戲,很有能量;也有經驗非常豐富的;也有經常拍電影、電視劇的演員”,但是“他們都非常熱愛舞臺,有一種不怕失敗的感覺”。戲劇導向上,孟京輝表現出相當大的隨意性,他沒有給大家一個明確的答案,“中國導演,在澳大利亞,用英語導演了一個德國戲劇,需要有國際視野,想象的四川,造成了一個普遍性,大家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三個神靈到四川找好人,我想把好人概念模糊化”[5]Australia Plu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4V5JEP3Q8&t=158s,2014-07-06.。
關于孟京輝戲劇表演的先鋒性和實驗性,存在較大爭議。美國戲劇學者康開麗覺得孟京輝很“牛逼”,并且仔細總結了孟京輝的“牛逼”之處:(一)他的語言使用。在戲劇中,洋溢著俚語、冒犯語、雙關語和很多看起來無止境的互文關聯;(二)工作時,孟京輝完全不顧及別人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的“牛逼”在于先鋒精神和名人光環的結合,他支持潮流、設定潮流、成為潮流。他敢于指責同行和批評家的言論;(三)“牛逼”對于孟京輝而言,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生活上,他抽煙、喝酒、說臟話、開玩笑,整個人很有趣,很給力,很酷。同時,他沒有瞧不起“大眾”,而是“啟蒙且逗他們”,“熱愛他們”,既挑戰,又娛樂[1]Claire Conceison,“China’s Experimental Mainstream:The Badass Theatre of Meng Jinghui”,The Drama Review,2014(1),pp.66-70.。
倫敦大學的羅賽拉·法拉利非常欣賞孟京輝戲劇的形式感,感受到舞臺上活生生肢體表達的巨大戲劇能量:“孟京輝的劇場是一個擬人化的有機體,有著具體的感覺和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舌頭還有大腦。這樣的實驗戲劇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活人在舞臺上創造戲劇感、釋放戲劇能量”,這樣的戲劇不能完全用理性和邏輯衡量,因為“孟京輝的戲劇充分借助通感,更加強調表演性和肢體性”[2]Ferrari,Rossela, Pop Goes the Avant-Garde:Experimental Theatre in Contemporary China,Calcutta,India:Seagull Press,2012,pp.117-120.。澳大利亞學者蔡莘莘同意法拉利的觀點。她覺得,孟京輝的戲劇乍看起來,“觀眾的第一印象就是紛亂的情節、獨特的怪異的臺詞、即興的表演和新穎的舞美,這些可以衍生無限的意象和多種多樣的情緒”[3]Shenshen Cai,“Meng Jinghui and His Contemporary Avant-Garde Drama”,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14(1),pp.75-92;p.77,p.90.。她認為,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孟京輝的先鋒實驗戲劇是中國當代戲劇史的分水嶺,他創造性地使用多元化的戲劇語言,大膽使用流行文化元素,展示了實驗戲劇的后現代主義精神”。這樣做的目的在于“質疑并且挑戰現代主義認識論和元敘事——理性、道德、二元對立等,這樣,顯得更為不同尋常,更有挑戰性和批判力度,絕不向世俗屈服”[4]Shenshen Cai,“Meng Jinghui and His Contemporary Avant-Garde Drama”,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14(1),pp.75-92;p.77,p.90.。
不過,在一些中國戲劇學者看來,孟京輝的一些戲劇卻有故弄玄虛之嫌,造成戲劇形式大于內容。這樣的后現代先鋒戲劇,“總是以非常規的、讓人難以理解、共鳴的獨特方式表達,就往往使其戲劇表現讓人只看到現實人生的外在表層而難窺其里”,使人感到“少有藝術創造”,“難以表現出形而上的探詢人的命運、拷問人的靈魂的精神內涵,因此,也就不能深刻地反映現實人生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不能使戲劇具有那種照亮和強化人的精神的審美力量”[5]胡星亮:《當代中外比較戲劇史論(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377頁。。
有關孟京輝戲劇國外演出的接受,帶來更多討論的可能還是戲劇的功能,也就是戲劇何為的問題。很多人以為,藝術作品應該呈現,而不是判斷,判斷可以留給讀者、觀眾和學者。這樣理解沒有問題,詩歌、繪畫、雕塑、音樂、戲劇、影視等似乎都是如此,不過,有個深層問題,藝術呈現什么?如何呈現?藝術可以只呈現問題不提供答案,但問題是這樣的藝術品和我們生存的世界本身有什么區別?如果不能指出一條可能的出路,藝術作品有何用?林克歡認為,“自古以來,任何一部真正的戲劇作品,不管它是什么體裁,說到底,都是人的命運的表現,也可以說,都是通過個人命運探索人類的命運”[6]林克歡:《戲劇表現的觀念與技法》,北京聯合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頁。。而在董健教授看來,對于一部戲劇,說到底,還是其戲劇精神至關重要,“戲劇是公開表演的藝術,因此,戲劇精神是貫穿在編、導、演的全過程之中的,并由劇場與觀眾共同體現出來的。人們在‘觀’與‘演’公開、直接的交流中,集體地體驗生命、體驗生存,超越環境,批判成規,熱烈地追求自由與幸福,這就是戲劇精神。它擴大了人類的精神空間,最高境界就是人在‘自由狂歡’中進行的靈魂‘對話’。”[7]董健:《董健文集卷一·戲劇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頁。筆者覺得,對于一部戲劇的欣賞或者批判,戲劇精神或者藝術燭照的強弱相當重要。這樣,再來審視孟京輝戲劇演出的國外接受,一切都顯得更為清晰了。
孟京輝執導的《活著》在德國演出,基本零差評,普通觀眾、演藝界人士、學者和中德官方都表示贊賞,這些當然和全體演職人員的精彩演繹分不開,而最關鍵的恐怕還是劇末和解的畫面。盡管福貴的親人們一個個離他而去,最后他依然能夠和老牛相伴,在無垠的大地上勇敢生存。這樣的畫面讓人想起庫切的小說《恥》,盧里的女兒露西被黑人輪奸、懷孕,而她還能勇敢地活著,“和煦的太陽,靜謐的午后,在花叢中忙碌的蜂群;而在這幅畫面的中央站著一位年輕的女子,剛剛懷孕,戴著頂草帽”。這中間體現出的與命運的頑強抗爭精神震撼人心,更可以給人們指出可能的生存之路。
而孟京輝執導的《四川好人》在澳大利亞演出后,則被認為整體混亂、渙散,缺少聚焦的戲劇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孟京輝只想拋出問題,而不是明確批判什么,也沒有明確提出如何解決問題。澳大利亞戲劇評論家赫伯特之前一直對孟京輝期望值很高,但看過《四川好人》演出后,他覺得“盡管才華橫溢的演職人員盡力了,分崩離析的戲劇就是無法形成一個整體,最終,戲劇演出顯得混亂、老套、難以讓人滿意”。他批評說:“讓才華橫溢的演員看起來如此平庸,簡直就是罪過,劇中,演員沒有任何亮色,《四川好人》讓人失望,沒有具體形式,沒頭沒尾,也沒有展示布萊希特所想要表達的人性的腐敗和貪婪。”[1]Kate Herbert,“Shambolic Brecht”,Herald Sun,2014-07-04.澳大利亞的著名演員博伊德也和赫伯特持相同的看法。在他看來,演員和舞美工作人員都很盡力,做得非常好,但是對戲劇整體,他的評論是:“整體?太鬧,沒有戲劇聚焦,戲劇能量散發得無影無蹤”[2]Boyd Chris,“Ripping Yarn From Brecht Gets Messy Despite an Outstanding Cast”,Australian,2014-07-04.。
孟京輝的藝術表現手法似乎說明,藝術只需提出問題,呈現問題,而不需直接提供答案,這是孟京輝藝術倫理的核心所在。但是,這樣的看法,在戲劇表現和呈現時往往因為形式的紛亂而影響了對觀眾和受眾提供啟蒙的可能,就會引起觀眾以及學者們的反感。筆者認為,這是《四川好人》被差評的最主要原因。
結語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孟京輝攜很多作品遠赴世界各國,登上異國他鄉舞臺,向世界觀眾展現中國當代戲劇風采,對于中國文化藝術走出去以及中國國際文化軟實力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研究這些演出被國外觀眾的接受,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反思人性關懷和戲劇精神的普世性特征,進一步追問世界范圍內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可能。
在當下中國文化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的背景下,作為中國當代最具爭議性并且有影響力的戲劇人,無論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等待戈多》,還是2019年進入阿維尼翁IN戲劇節單元的《茶館》,孟京輝將極具辨識度的孟氏戲劇帶出國門,多次打破中國現當代戲劇“零”的局面。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上,孟京輝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強調:“中國戲劇想要真正走出去,首先需要一個共同的國際語境,其次是彰顯自身文化辨識度,而辨識度的建立則需站在全球視野的高度。”[3]張曼:《專訪:中國戲劇走出去應在國際語境彰顯文化辨識度——訪北京青年戲劇節藝術總監孟京輝》,https://www.sohu.com/a/240275630_267106.2018-07-10.而這種辨識度在孟京輝看來正是“人類的辨識度”,強調人類辨識度的戲劇作品,也正是一把打開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需要像孟京輝這樣的當代戲劇人將民族性、民間性與世界性融為一體的戲劇作品搬上世界戲劇舞臺,減少國家、民族、文化之間存在的差異,共建戲劇層面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