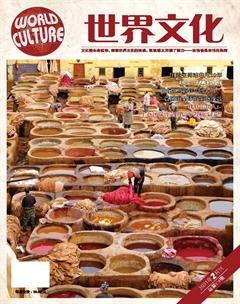王韜:早期中英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賴某深
晚清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國,從閉關鎖國被迫對外開放,從農耕文明被迫面對工業文明。面對西方的挑戰,開始有先行者將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遙遠的國度,開始用審視的眼光看向西方,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奔赴西方試圖探索富國強兵之道。繼岳麓書社出版《走向世界叢書》,收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先進的中國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設立專欄,陸續推出系列文章,以紀念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國救民之道、不遺余力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驅。
近代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以外交官或者地方督撫所派官員為最多,以私人身份走向世界的則較少,留下深刻文化記憶的則更少。而王韜則是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其考察筆記《漫游隨錄》是中國文人以私人身份赴歐的最早、最全面的記錄,也是近代中英文化交流的生動見證。
王韜(1828—1897),原名王利賓,字蘭瀛,后改名為王瀚,字懶今、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論家、文學家。他與理雅各合作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經典》,至今仍是歐美人士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最權威版本。王韜于1874年在香港創辦了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循環日報》。
同治六年(1867年),聘請王韜翻譯中國經典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回國,招王韜西行。王韜遂于11月20日從香港啟程前往歐洲,歷時兩年多。《漫游隨錄》即記其早年經歷與在歐洲的所見所聞。
重點記述在英觀感
王韜在英國待的時間最長,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均曾涉足,故所記以英國為多。英國政治、司法、軍事、風俗、娛樂、科技、教育等均有所記載。
關于英國政治,他介紹了議院:“有集議院……國中遇有大政重務,宰輔公卿、薦紳士庶,群集而建議于斯,參酌可否,剖析是非,實重地也。”
關于司法,他參觀了一處新建監獄,“獄囚按時操作,無有懈容”,“居舍既潔凈,食物亦精美。獄囚獲住此間,真福地哉”。
關于軍事,著墨不多,在愛丁堡時,觀看了“團丁(民兵)”“海濱演炮”,“其法以廢舶置海中,上張旗幟。自海濱距海面,約遠二三里或四五里,而后以炮擊之,觀其中否”。這樣的演習每月舉行四次。王韜的評論是“此民間于晏安之際,武備不弛,先事講求之一道也”。
關于風俗:男女交際,自然謹嚴,“名媛幼婦,即于初見之頃,亦不相避。食則并席,出則同車,觥籌相酬,履舄交錯,不以為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潔其心,秉德懷貞,知書守禮,其謹嚴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這與中國男女授受不親形成鮮明對照;“國中風俗,女貴于男。婚嫁皆自擇配,夫婦偕老,無妾媵”,這與中國男尊女卑,結婚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迥然有別;人死之后,“葬于官地,不祭墓。思念所及,則詣墓一觀,掛鮮花一圈于碑碣而已”,這與中國重死輕生、葬禮隆重絕然不同。
關于娛樂,他記載了馬戲、魔術表演、跳舞,記述馴獸表演最為精彩:
獸人入虎、豹、獅、熊之房,令其躍圈環繞作諸戲劇,不肯前者以鞭笞之。各獸或有怒目張牙咆哮作搏噬狀者,獸人即出手槍向空迅發,火焰震烈,諸獸無不悚伏,然后前后馴擾,惟所指揮。獸人于是履虎尾、捋虎須、攀虎牙、探首于虎口吻間,虎涎淋漓滿面,博觀者笑樂。于獅、豹房亦然,獅、豹無不弭耳搖尾,狎之幾如貓犬。
用幾個生動準確的動詞,將馴獸師的勇敢、猛獸的表情和動作刻畫得活靈活現。
關于英國的科技,工業革命后的英國,新技術、新發明層出不窮,他記載了“懸橋”,有如“長虹”飛渡,“工制獨創,尤為中土所稀”;談到火車在英國初創時,阻力重重,久而久之,人們才認識到火車開通促進了貿易,增加了稅收,“實為裕國富民之道”,更重要的是可以迅速調運兵力——王韜是特意寫給頑固反對修鐵路的人士看的,須知當時中國還沒有一寸鐵路;觀看了“輕氣球”放飛;記載了日新月異的“軍營渡水之具”;贊嘆英國制造“無一不以機器行事”,“幾神妙不可思議矣”。而英國科技之所以如此發達,重要原因是國家鼓勵發明創造,建立了專利保護制度。所謂“西國之例,凡工匠有出新意制器者,器成上稟,公局給以文憑,許其自行制造出售,獨專其利,他人不得仿造。須數十年后乃弛此禁,其法亦良善也”,這可能是中文文獻中最早介紹西方專利制度的。
關于教育, 他贊譽英國學校學習和考試的內容“非止一材一藝已也”,要廣泛學習歷算、兵法、天文、地理、書畫、音樂、各國之語言文字,“如此,庶非囿于一隅者可比”,“故英國學問之士,俱有實際”。這與中國只注重誦讀儒家經典,選拔人才只考試四書五經,以致士人不務實學形成了鮮明對照。
《漫游隨錄》有兩段對英國的總體評價,值得注意。一段載卷二《風俗類志》:
英國風俗醇厚,物產蕃庶。……人知遜讓,心多愨誠。國中士庶往來,常少斗爭欺侮之事。異域客民族居其地者,從無受欺被詐,恒見親愛,絕少猜嫌。無論中土,外邦之風俗尚有如此者,吾見亦罕矣。


一段載卷三《游博物院》:
蓋其國以禮義為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為基,而不先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歐洲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余亦就實事言之,勿徒作頌美西人觀可也。
在贊美英國的同時,指出了英國乃至歐洲各國的立國之道是以禮義為教、以仁信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以往那種視西方各國為“化外之邦”,認為西方人“性等犬羊”“專恃甲兵”,只知“圖利”“ 尚詐力”的錯誤觀念自然不攻自破。
中英文化交流的生動見證
在《漫游隨錄》卷二《倫敦小憩》王韜寫道:“三百年前,英國人無至中國者;三十年前,中國人無至英土者。”在《漫游隨錄》自序中,王韜自豪地說:“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無論學士大夫無有至者,即文人勝流亦復絕跡。”王韜是中英文化交流的“先路之導”,這并非夸張。他到英國很久,中國才向西方派出第一個外交使團;比郭嵩燾駐扎英國,更早了整整7年。并且,他出色地充當了中英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首先,王韜是第一個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的中國人。受牛津大學校方邀請,王韜以華言(漢語)講學,而且講的內容是“中外相通之始”,講述了中英交往的歷史,并希望中英兩國加深交往、發展友誼,寄語聽演講的學生成為有用之才。演講的效果是:“一堂聽者,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墻壁為震”。 演講結束后,學生向他請教東方的孔子之道與“泰西所傳天道”有何同異,王韜的回答是:“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還說:“東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
其次,王韜在英國多次以吟唱的方式傳播古典詩詞,推廣中國文化。說其是將中國文化推廣到世界的第一人,并不為過,但這一點還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一次是為少女愛梨吟哦白香山(居易)《琵琶行》一篇,“抑揚宛轉,曲盡其妙”,“愛梨為之嘆賞弗置,而更使予逐字度之”,“明日歌曲亦能作哦詩聲,且響遏行云,馀音繞梁,猶能震耳”,說明即使是外國人,也能欣賞和傳唱中國古典詩詞。另一次是在富商司蔑氏太太召集的上百人的聚會場合,“為曼聲吟吳梅村《永和宮詞》,聽者俱擊節”。還有一次是受理雅各邀請,在“會堂”“宣講孔孟之道”兩個晚上,即將結束時,“諸女士欲聽中國詩文,余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華《吊古戰場文》,音調抑揚宛轉,高亢激昂,聽者無不擊節嘆賞,謂幾如金石和聲、風云變色”。“此一役也,蘇京士女無不知有孔孟之道者”。蘇格蘭的士女算是領略了孔孟之道和中國詩詞的魅力。
再次,王韜本人就是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的一個很好的載體,他以其可見可感的形象和舉止向西方社會傳遞了中國文化的信息。他的穿著打扮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和濃厚興趣,時常發生一些有趣的誤會。在游英國亨得利時,就被兒童認作女性:
西國儒者,率短衣窄袖,余獨以博帶寬袍行于市。北境童稚未睹華人者,輒指目之曰:“此載尼禮地也。”或曰:“否,詹五威孚耳。”
“載尼禮地”是中國太太(Chinese Lady)的譯音;“威孚”是妻子(wife)的譯音;“詹五”則是流落到英國的一個高個子安徽人。寫到此處,王韜哭笑不得:“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識者,竟欲雌之矣!”
在游法國馬塞時,一家酒館的年輕女服務員“見余自中華至,咸來問訊。因余衣服麗都,嘖嘖稱羨,幾欲解而觀之”,令人忍俊不禁。
以上是王韜剛到西方的情形。等到他待了較長時間后,通過接觸英國友人,參加一些社交活動,為圖書館題詞,公開場合講演及辯論等等形式,進一步宣傳和弘揚了中華文化。
首次介紹了世界博覽會
王韜親歷了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他將世博會稱為“博物大會”。書中記述, 巴黎世博會場館起建于1864年,落成于1867年,“開院之日,通國民人,列邦商賈,遐邇畢集,均許入而瀏覽,來往無禁”,“法駐京公使伯君,于其中創設聚珍大會,凡中外士商有瑰奇珍異之物,皆可入會,過關許免其稅”。陳列的物品美不勝收,“皆當世罕覯之物,或有莫悉其名者”。歐洲各大國君主光臨者,除法國國王外,還有俄羅斯、普魯士、土耳其的君主。這屆博覽會中國并未參展,卻有一個廣東戲班子在世博會上演出:“有粵人攜優伶一班至,旗幟新鮮,冠服華麗,登臺演劇,觀者神移,日贏金錢無算。”后來法國某伯爵還花費重金將廣東戲班子的“裝束”全部買去。

王韜還多次參觀1851年英國舉辦首屆世博會的場館水晶宮。水晶宮建在倫敦南部,以鋼鐵為骨架,以玻璃為主要建材。在《漫游隨錄》中他描寫道:
……地勢高峻,望之巍然若岡阜。廣廈崇旃,建于其上,逶迤聯屬,霧閣云窗,縹緲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漢。北塔凡十一級,高四十丈。磚瓦榱桷,窗牖欄檻,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精瑩。其中臺觀亭榭,園囿池沼,花卉草木,鳥獸禽蟲,無不畢備……
由于水晶宮實在很大,王韜一共參觀了4天,“尚未能遍”。
書中對中國人在英國的情況有所反映。從中可知,在中國派出幼童留美之前,就有兩個中國學生韋寶珊、黃詠清在英國讀書,不過這兩人是公派還是自費,在何校求學,書中未作交待,這是研究中國留學史的重要材料;王韜在英國見到了浪跡歐美多年的“長人詹五”夫婦,詹五曾為英國人樓頂大書“天下太平”;在蘇格蘭,王韜遇到一個在當地娶妻生子的華人胡某,看到其經濟困難,便給予了資助,胡某“感激涕零,幾哭失聲”。
《漫游隨錄》收錄了王韜在英國作的一些詩詞,抒發了一個報國無門的不得志書生的抑郁和憤懣之情,像“異國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風塵。可憐獨立蒼茫里,撫卷聊看現在身”,不過他的愛國激情依然洋溢,“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馀肝膽肯輸人”。充分反映了一個走向世界的先行者的孤獨、蒼茫的心路歷程。
書中有些記載,可看出王韜多情的一面。像在蘇格蘭時,某女士讓出閨房,供其歇宿;一起出行時拿出手帕為女士擦拭汗珠;女士游玩累了“扶余肩不能再行”;之后“余代為掠鬢際發,女士笑謝焉,覺一縷清香沁入肺腑”等等,是文人墨客真情的自然流露,并非像某些人所批評的“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