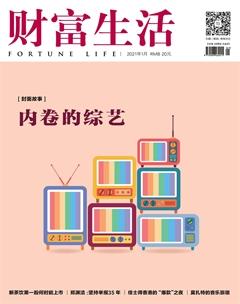娛樂的價值
2021-03-22 02:34:50本刊編輯部
東方企業家 2021年1期
本刊編輯部
娛樂,與人類文化發展伴隨而生,20世紀的著名荷蘭文化學者約翰·赫伊津哈認為,正是“娛樂”這種生命活動方式,塑造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多種重要形式:“儀式產生于神圣的游戲,詩歌誕生于游戲并繁榮于游戲,音樂和舞蹈則是純粹的游戲……”
從消遣的角度看,娛樂是人類游戲本能的自然宣泄,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人們傾向于觀看或刺激、或激烈、或搞笑、或新奇的綜藝節目消磨時間。
然而,如今這種在綜藝里唾手可得的“自然宣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卻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國內電視綜藝誕生之初,以春晚為代表的晚會型綜藝風光無限,在給當時貧瘠的文化生活帶去一抹亮色的同時,也以集體主義的審美抹去了個體化的渴求,對后者的追求甚至往往會被打上“自由主義”的標簽。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以《超級女聲》為起點的現象級綜藝開始表達個性,滿足人們對“游戲”的本能。現在無論是打開電視還是點開視頻網站,既有連播幾季的常青綜藝,也有層出不窮的新節目。文化、音樂、演技、辯論、旅游、競技、美食……可以說是“萬物皆可綜藝”。不過,隨著綜藝節目“人到中年”,打造一檔“爆款”綜藝越來越難:原創力不足、同質化凸顯等問題制約綜藝發展,“娛樂至死”的綜藝也在內卷中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
從一開始寓教于樂的合家歡,到如今益發垂直細分的小眾取向,綜藝早已與商業和社會文化難舍難分、唇齒相依。回到赫伊津哈的“游戲論”,既然游戲也是一條人類文明產生的通路,那么綜藝做為游戲的視聽表達形式,或許也可以在極度娛樂的外衣之下,就多元的價值觀做嚴肅、真誠而開放的探討。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遭遇內卷的綜藝,愿它依然能承載起每一位觀眾和從業者的渴望……
猜你喜歡
大科技·百科新說(2021年6期)2021-09-12 02:37:27
少兒美術(2021年2期)2021-04-26 14:10:14
文苑(2020年9期)2020-09-22 02:33:24
好孩子畫報(2020年5期)2020-06-27 14:08:05
天天愛科學(2019年8期)2019-09-10 07:22:44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6期)2019-07-24 08:13:50
初中生學習·低(2016年10期)2016-11-25 04:51:34
飛碟探索(2016年11期)2016-11-14 19:34:47
作文大王·笑話大王(2016年8期)2016-08-08 11:28:22
奧秘(2015年2期)2015-09-10 07:2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