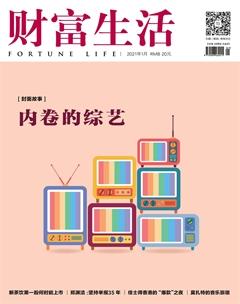春晚還是“新民俗”嗎?
仲富蘭

圖/ 中國(guó)殘疾人藝術(shù)團(tuán)
那天,去電視臺(tái)做節(jié)目,休息的時(shí)候,我與上海一位著名的節(jié)目主持人聊了起來,當(dāng)聊到電視節(jié)目收視率時(shí),誰料想他無奈地告訴我,還“收視率”呢,現(xiàn)在恐怕你應(yīng)該問我“開機(jī)率”幾何了。我頓時(shí)無語。
20年前我在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教過傳播學(xué),那個(gè)時(shí)候網(wǎng)絡(luò)媒體已經(jīng)急起直追,我知道,當(dāng)時(shí)如日中天的電視節(jié)目總會(huì)由盛而衰的,但不知道電視衰落得如此之快。于是,我想到了曾經(jīng)大紅大紫的電視綜藝節(jié)目,情況可能也大致如斯。比如中國(guó)人過年看春晚,這類節(jié)目應(yīng)該算作“綜藝”或“泛綜藝”的晚會(huì)型節(jié)目吧,作為最受觀眾歡迎的電視節(jié)目類型之一,從20世紀(jì)80年代就一直以星火燎原之勢(shì)迅猛發(fā)展。節(jié)目形態(tài)從最開始的綜藝晚會(huì)節(jié)目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真人秀節(jié)目,發(fā)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jié)舌,以至于人模人樣的藝人都想法設(shè)法要朝春晚里鉆,為什么呀,吸引注意力啊!要紅要紫,混個(gè)臉熟,非得這樣的平臺(tái)來造就。平心而論,三十多年來這個(gè)綜藝平臺(tái)確實(shí)也造就、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了不少人才。
前些年老是有人問我,春晚能否算作中國(guó)人的“新民俗”?我說,叫不叫“新民俗”可以討論,因?yàn)榇和磉@類綜藝節(jié)目還在發(fā)展變化中,而民俗是千百年來的人們物質(zhì)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積淀,不敢妄下結(jié)論。不過,我從不否認(rèn)三十多年來,春晚從一臺(tái)早期“茶座式”的晚會(huì),發(fā)展成為如今億萬中國(guó)人知曉度最高的節(jié)目樣式,不僅為廣大觀眾帶來精神愉悅和藝術(shù)享受,也為改革開放40年留存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一臺(tái)春晚的變化,可以說就是近幾十年來一部中國(guó)人民精神生活的發(fā)展史。春晚以“綜藝”的形式,承載了幾代人的集體記憶,這是不容置疑的。
那些年,還有一檔叫《正大綜藝》的節(jié)目,也是火得一塌糊涂。記得在那個(gè)信息匱乏的年代,一家人圍坐在熒屏前,“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吸引了無數(shù)如饑似渴獲取知識(shí)的受眾的青睞,那個(gè)節(jié)目告訴公眾諸多域外的風(fēng)土人情和民間文化知識(shí),從芬蘭的“午夜太陽”到亞馬孫河流域的“口嚼酒”……應(yīng)有盡有,它還引進(jìn)了海量的海外優(yōu)秀影片,大大豐富了當(dāng)時(shí)人們的精神生活,節(jié)目片尾歌曲《愛的奉獻(xiàn)》也因此火遍大江南北。
電視綜藝節(jié)目走過三十多年,《正大綜藝》節(jié)目多次改換節(jié)目?jī)?nèi)容與形式,后來據(jù)說銷聲匿跡了;“春晚”呢,還會(huì)辦下去,因?yàn)樗休d的內(nèi)容越來越多:新一年的家國(guó)之夢(mèng)、新一年的個(gè)人期許,近年來隨著觀眾審美水平的不斷提高,精神文化需要越來越豐富,我想,春晚這種綜藝節(jié)目會(huì)越來越難辦。
說到底,億萬民眾就是一座大山,做綜藝節(jié)目的人,要順應(yīng)這個(gè)大山,因地制宜,而不是相反。社會(huì)發(fā)展如同疾風(fēng)驟雨,民眾的娛樂生活和審美需求明顯變化。在注意力經(jīng)濟(jì)時(shí)代,使用明星是吸引眼球的最便捷的方式,明星資源成為眾多綜藝節(jié)目競(jìng)相追逐的對(duì)象,結(jié)果綜藝節(jié)目捧紅了眾多流量明星,而明星嘉賓的片酬胃口也越來越高。大投資、大制作、大明星的成本日趨升高,而節(jié)目質(zhì)量不見提升,操作模式上缺乏創(chuàng)新,漸趨保守,同質(zhì)化和過度娛樂化等問題隨之而來,少數(shù)明星霸占屏幕,過度曝光,也造成觀眾的審美疲勞。
老話說:“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shí)移,時(shí)移則俗易”。如今,社會(huì)的主體消費(fèi)人群與傳媒條件都變化了,再堅(jiān)持以往那種大呼隆式的“綜藝”玩法,恐怕就有“刻舟求劍”、“守株待兔”之嫌了。前幾年對(duì)于一些大型或超大型的晚會(huì)型綜藝節(jié)目,我曾經(jīng)留意一些年輕朋友的注意力,他們對(duì)這類節(jié)目顯然已經(jīng)不甚了然,甚至興趣全無,味同嚼蠟了,他們寧可參與網(wǎng)絡(luò)綜藝,或者喜歡做自己感興趣的活動(dòng),這難道不是“雞肋”嗎?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所以我在本文發(fā)出了春晚還能不能成為“新民俗”的疑問,而我的這種憂慮絕非危言聳聽。
那些熱衷于大投資、大制作、大明星的綜藝節(jié)目操作模式的才子導(dǎo)演,自我感覺不能過于良好,因?yàn)樯鐣?huì)已經(jīng)變化了,老百姓的民俗生活樣式也在不停變化,有人曾經(jīng)以動(dòng)物舉例,不甚恰當(dāng),卻也形象:改革開放前人是“螞蟻”,勤勉地勞動(dòng),換取自己的生活資料;幾十年改革開放,許多人成為“孔雀”,總想“開屏”,顯示自己的美的存在;如今信息文明時(shí)代,人們已經(jīng)變成“蜘蛛”了,忙著編織自己的網(wǎng)絡(luò)和朋友圈,愉快地或是艱難地生存,不太迫切需要“注意”或是“被注意”,更重視自己的“意圖”能否實(shí)現(xiàn),自己的IP能否放大,所以,娛樂文化市場(chǎng)再搞“注意力”經(jīng)濟(jì)那一套就有點(diǎn)捉襟見肘了,若是綜藝類節(jié)目還是靠那些只搞噱頭、不對(duì)內(nèi)容加以賦值的話,那么很可能是無人搭理、顆粒無收。
事實(shí)上,隨著社會(huì)的進(jìn)步,人們對(duì)于綜藝節(jié)目,還是會(huì)關(guān)注的,但這種關(guān)注不僅僅是“笑過就完”“娛樂至死”的短暫體驗(yàn),人是一種精神的社會(huì)存在,并非只是滿足于衣食住行這樣的物質(zhì)需求,還有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如何找到心靈歸屬的精神追求,更值得人們追求。
就綜藝節(jié)目的看點(diǎn)而言,創(chuàng)制者的眼界與格局應(yīng)該更廣闊一些,重視節(jié)目?jī)?nèi)容價(jià)值的放大與人性的關(guān)懷,節(jié)目才能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眼下,應(yīng)該放大網(wǎng)絡(luò)綜藝的體量和細(xì)分受眾市場(chǎng)需求,技術(shù)和資本向網(wǎng)絡(luò)綜藝傾斜,弱化傳統(tǒng)電視綜藝的操作模式。注意力經(jīng)濟(jì)還是要的,明星的身體意義與符號(hào)意義只有在情感結(jié)構(gòu)、價(jià)值觀念、文化認(rèn)同上與當(dāng)下的普通觀眾更為貼近,綜藝節(jié)目才能獲得持續(xù)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