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拾穗
聶還貴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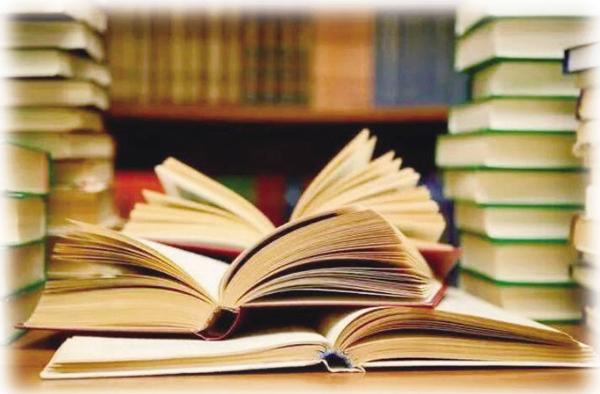
中藥“遠志”,別名“小草”。《世說新語》載,東晉大臣謝安,初隱居東山不出,后下山做了桓宣武的司馬官。一天,有人給桓公送來一味中藥“遠志”,桓宣武遂問謝安,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藥兩名?在場的郝隆搶答:“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以詼諧反喻譏笑謝安。
清·龔自珍曾賦詩《遠志》,抒發抱負遠大而不被重用的心境和憤世之情:“遠志真看小草同”,“青燈夜雪阻山東。”
二
東漢名臣楊震,為官數載,公正廉明,人以“楊震四知”廣而頌之。
一次,楊震因差途經昌邑縣,縣令乃舊交王密。王密獲知楊震到此,念及楊震當年給予的知遇之恩,遂懷揣什,乘了朦朧夜色,前往館驛相贈,卻遭到楊震嚴拒。
王密急切道:“此時深夜,無人知矣。”
楊震正顏厲色說:“豈可暗室虧心!舉頭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
元代學者許衡,有“義不摘梨”的故事,為世人稱道。
一年暑夏,許衡與人途徑河陽田野,烈日炎炎,焦渴難耐。恰好道路一旁有梨樹果熟。眾人一哄而上去摘。“道有梨,眾爭取啖之”,唯許衡獨自一人正襟危坐于樹下,安然自若。
有同行者問許衡:“何不摘而食之?”
許衡回答:“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
同行者聽了不以為然地說:“世亂,此無主。”
許衡一字一頓地回應道:“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蘇軾《赤壁賦》直言:“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禮記·中庸》有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三
事物的個性特征,是事物的本質屬性,也是其瑩亮的辨識度。個性越鮮明,辨識度越高。有時候,越是個性的便越是美的。
在大合唱中聽不到自己的聲音,若要找回自己,一是獨唱,二是領唱。我想到了中國的大宋王朝,年輕的宋朝人看一眼身后華盛媚艷的唐人,意識到不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而必須另辟蹊徑,彰揚個性。你寫句式齊整、合轍押韻的唐詩,我賦錯落雜陳的牌名宋詞;你崇尚富貴牡丹,我推崇清雅梅花;你感性繪絢爛唐三彩,我理性燒單色宋瓷,造一個不喧不鬧、幽然澄靜的“雨過天青”。
中國五大名瓷以宋代汝瓷最為珍美,“似玉非玉卻勝玉”,遂有“五窯之魁”盛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汝瓷傳世僅存60余件,其身價在今日世界拍賣場最為昂貴,炫為財富與榮耀的象征與注釋。“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件”。
初,五代后周世宗柴榮令工匠燒制茶器。什么顏色?世宗皇上看一眼剛剛下過雨的天空,驀然來了靈感,說,就燒一個雨過天晴的顏色吧。“雨過天青云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
雨過天晴?雨過天睛那該是什么顏色。帶了沉甸甸的疑難,工匠反復觀察天象,虔心揣摸,但見雨霽放晴,天色青中有藍,藍綠相間,端的是碧空萬里,粉青月白,“千峰碧波翠色來”。
與柴榮一樣篤信道教的宋徽宗,不喜歡定瓷白色有“芒”,而獨愛“青如天,面如玉,蟬翼紋,晨星稀”的汝瓷,詔令將其移植到開封官窯發揚光大。汝瓷遂異彩大放,聲名遠播。
汝瓷釉面質感密致,幽邃溫潤;釉色神秘迷離,氤氳一境空靈夢幻,令人欲看不透,欲罷不能。“天真獨朗,從藍而青”的汝瓷,以宋代官窯的巔峰之作,被尊為宮廷御用珍物。“識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明代曹昭留一聲百年感慨:“汝瓷窯,出北地,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
汝瓷,出神入化地載動著宋朝的時代特質,標志著宋代審美理想與藝術趣味的別樣與新異,雅然成為另一個辨識宋朝的美學符號。
選自《坐看云起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