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人格
鄭欣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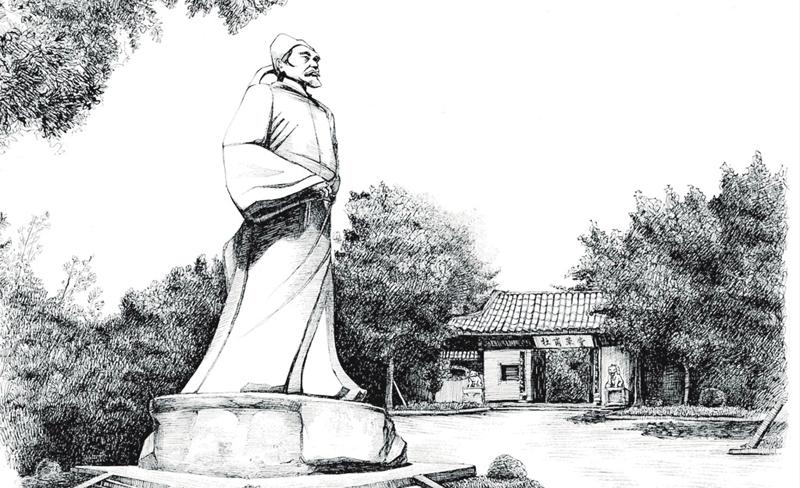
公元748年,杜甫第三次向曾為河南尹的尚書左丞韋濟呈詩,請求其向朝廷推薦自己,這就是著名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中陳述自己入仕無門、困居長安的境況,政治抱負不能施展,慨嘆道:“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表示雖然困頓艱蹇,但仍且行且歌,決不是避世的隱士。這兩句既是詩人此前蹭蹬失意、騎驢長安的寫照,也是此后20余年漂泊歲月、歌吟人生的預示,似成“詩讖”。
杜甫留給我們的1400余首詩歌,記錄了歷史的風云,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狀況,抒發了自己的心聲;人們也從這些篇什中認識了杜甫,看到他的詩歌的不朽價值,并且深刻地感受到貫穿其中的精神,這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和對天下蒼生的赤誠之心,就是對社會的責任與理想的履踐。這種精神,也就是杜甫的人格精神,它是一種巨大的力量,成為杜甫精神遺產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所謂人格,指的是個體特有的特質及行為傾向的統一性,又稱個性。中國古代雖然沒有“人格”的概念,但“人品”一詞卻大體具有“人格”的某些含義,有時甚至被當作“人格”來使用的。中國傳統理想人格核心是儒家人格,原初的儒家人格理想,是以“內圣外王”、“孔顏樂處”的圣賢氣象,重義輕利、安貧樂道、自強不息的君子之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為主要內容組成的,統馭著千百年來人們的精神追求和人格踐履。當代人格學研究,有兩種為大多數學者所共同認可的參照系:一是社會生活,二是文化影響。理想人格的構成,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三種人格力量都得到長足的發展且形成協調的互補共生的格局,對于文學家、藝術家等文化人來說,審美力量的考察則顯得更為重要和更具有現實意義。這些理論和觀點,對于認識杜甫的人格精神,也是很有幫助的。
人格的形成,先天的氣質稟賦為不可忽視的基礎,后天的環境為決定的因素。杜甫人格精神的形成,與其家世有著深刻的關系。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儒學影響、詩歌傳統與個人幼年遭遇。
杜甫很為自己的家世所自豪,所謂“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家聲與令聞,時論以儒稱”。他從小受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對孔孟宣道的憂患意識、忠恕之道、仁愛精神、惻隱之心等都有著深刻的理解并能身體力行,而對功名的渴望與對國家民族命運的強烈關注,也與其儒學觀念有著內在的聯系。儒家思想富于人文精神,對“人”特別重視,尤其是人格的完成與完美,而這又特別地集中于對“士君子”人格的認識上,《論語·述而》對此作了概括:“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知識、道義與美的追求,人格完成、文化使命與社會責任,是渾然一體的,也就是真善美的統一。應該重視儒家思想在杜甫人格塑造中的積極作用。
杜甫在接受儒學教育的同時,又深受家庭詩歌傳統的影響。他的祖父杜審言,其文才在當時享有盛名,少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齊名,稱“文章四友”,晚年與沈佺期、宋之問唱和,對今體詩的形成與確立多有貢獻。杜甫對這位自己并未見過的祖父推崇備至,不無夸大地稱其“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他把杜審言的詩學成就看成是家庭傳統:“吾祖詩冠古”,又諄諄教道其子:“詩是吾家事。”他又說:“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認為詩歌創作法則早在先秦的儒家就有了,自己從小作詩寫文章都是以儒家典籍為依據的。人們普遍認為,杜甫的詩藝與杜審言一脈相承。儒家精神影響著杜甫的人格,而終生不輟的詩歌創作又充分體現著這一人格特征及其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杜甫幼年,母親去世,由其二姑母撫養。二姑亦有一襁褓中的兒子。有一次兩個孩子同時患病,求問女巫,女巫說讓孩子睡在廳堂前柱的東南方向比較好。二姑的孩子原就睡在那個地方,可是二姑卻讓杜甫睡在那里,把自己的孩子抱到別處睡。后來二姑的孩子不幸夭折,杜甫活了下來。杜甫長大后知道了此事,也常向朋友訴說,賓朋無不感動,把二姑呼為“義姑”。“義姑”精神對杜甫一生影響頗大。
杜甫的人格特點,大致可概括為四點:“竊比稷與契”的使命意識、“白首甘契闊”的士君子之風、“窮年憂黎元”的仁者情懷和“素練風霜起”的審美理想。
杜甫的人格范型,是個體的天賦氣質,持久不懈的努力,并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精神綜合作用的結晶,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格理想的楷模。他的各項人格力量,都得到了突出且均衡的發展。比較而言,他的“窮年憂黎元”的仁者情懷,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和系念天下蒼生,更是凝聚和發揚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具有歷史和現實的意義。杜甫被稱為“詩圣”,這個“圣”,既是對他詩歌成就的最高評價,也是對他偉大的人格精神的最高褒揚。
選自《中華詩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