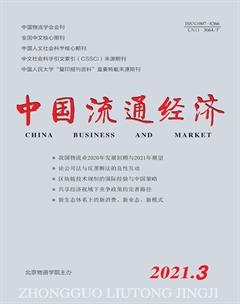論公司法與反壟斷法的良性互動
摘要:公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共同保護和規范的重要市場主體。但在法學研究和執法實踐中仍存在碎片化和孤島化的現象。在兩法雙雙迎來修改之際,立法者應推動兩法的無縫對接、有機銜接、同頻共振、相輔相成。兩法和而不同,都致力于提升公司活力,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都遵循民法基本原則。公司并購反壟斷執法應秉持包容審慎、處罰謙抑、服務能動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有效保障公司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公司并購反壟斷審查應采取“原則放行、例外禁止”的政策。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繼續保持法治定力,堅持反壟斷執法的常態化、法治化與專業化;新《反壟斷法》基于“誰主張、誰舉證”的理念,確立由反壟斷執法機構就公司并購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從公司并購限制性條件的適用范圍而言,應確立“可限可不限的,堅決不限”的立場。反壟斷處罰措施的選擇和使用應體現過罰相當的公平原則和比例原則。建議《反壟斷法》專章規定“壟斷行為的預防”,增加執法機構事先預防和事中監管的法定職責。落實《反壟斷法》的治本之策是激活公司治理機制。公司并購反壟斷中的控制權認定規則應盡量對標對表《公司法》。自我預防壟斷應成為大型公司的核心社會責任。
關鍵詞:公司法;反壟斷法;公司生存權和發展權;公司自治;公司社會責任
中圖分類號:F27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66(2021)03-0009-12
基金項目: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2019年度重點課題“公司法修改研究”(2019K20205)
一、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分別出臺于1993年和2007年。兩部法律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雖各有千秋,但均致力于增強企業活力,鼓勵企業做大做強做優,扶持中小微企業健康成長,維護自由公平充分競爭的法律秩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為囊括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合作社企業等不同市場主體,《反壟斷法》雖規制公司壟斷行為,但使用了外延更廣的“經營者”概念。從實踐看,公司制企業是反壟斷執法的主要對象。因此,公司是《公司法》和《反壟斷法》共同保護和規范的重要市場主體。但因《公司法》與《反壟斷法》各有分工,出臺時間和歷史背景各異,《公司法》未提及“反壟斷”,《反壟斷法》未提及“公司”,致使兩法自說自話、井水不犯河水,在法學研究和執法實踐中都存在碎片化和孤島化的現象。
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1 ]此后不久,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局就阿里巴巴投資收購銀泰商業、騰訊控股企業閱文收購新麗傳媒、豐巢網絡收購中郵智遞3起未依法申報經營者集中案件做出了行政處罰。[ 2 ]這三個案件都圍繞公司并購而展開。無獨有偶。在《公司法》即將迎來第六次修改之際,《反壟斷法》也將迎來第一次修改。在公司并購日益成為反壟斷執法焦點的新時代背景下,推動《公司法》與《反壟斷法》聯動修改,整合兩法制度資源,實現兩法良性互動和同頻共振,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二、《公司法》與《反壟斷法》的立法使命和規制理念和而不同
《公司法》第1條開宗明義地明確立法宗旨為“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反壟斷法》第1條明確立法使命在于“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兩相比較,兩法追求的立法目標既有共性,也有個性。
第一,就宏觀目標而言,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是兩法的共同追求。唯一的文字表述差異在于,因《反壟斷法》出臺時間晚于《公司法》,立法者目睹了我國市場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商業壟斷和行政壟斷的危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具備的自由公平的本質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因而特意在“發展”前面增加“健康”二字。義利兼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符合全球市場經濟的一般發展規律,是中國國情與國際慣例有機融合的偉大創造,應予長期堅持。要實現民富國強的中國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心無旁騖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當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已基本建立,但市場體系還很不完善。在土地、人才、資本、技術、數據、知識和管理等要素市場存在著發育不均衡、不充分、不統一的碎片化、孤島化現象,更存在著要素資源價格被扭曲、要素使用效率不高、要素配置不公平、要素市場壁壘林立、要素流轉不暢、要素獲取成本較高等體制機制性短板。[ 3 ]因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包括: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公司法》和《反壟斷法》的完善和落實都必須服從并服務于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大局。
第二,就中觀目標而言,《公司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目標和《反壟斷法》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目標具有同質性。經濟運行效率離不開穩定、透明、公平和可預期的法律秩序。《公司法》維護的社會經濟秩序包括投資秩序、競爭秩序和交易秩序三大秩序。其中,公平投資秩序有助于鼓勵投資興業,持續提升投資者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不斷增加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公平競爭秩序有助于造福中小競爭者,讓中小微企業脫穎而出、鯉躍龍門;公平交易秩序有助于造福廣大債權人和消費者,預防風險外溢,加速商事流轉,維護交易安全。而《反壟斷法》維護的社會公益(包括中小競爭者利益和消費者利益)恰系《公司法》第5條要求公司守法合規、遵守公德和商德、承擔社會責任的題中之義。
第三,就微觀目標而言,《公司法》規范公司組織和行為以及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權益的目標和《反壟斷法》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目標具有兼容性。《公司法》是企業法、主體法和組織法,旨在鼓勵和規范投資興業,完善公司治理,保護三類主體權益。但權利有邊界,自由有底線。公司和股權保護、公司并購和資本擴張不能超越理性自治邊界,不能觸碰《反壟斷法》作為秩序法和競爭法劃定的制度底線。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公平競爭秩序,有助于保護新興企業和中小微企業茁壯成長、免受壟斷行為之苦,督促大企業創新進取、免于因懈怠而落后,促進大小公司公平競爭、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提升股東投資價值,增強公司償債能力,維護交易安全。可見,《公司法》與《反壟斷法》的微觀立法目標并不相斥,而是相輔相成,無縫對接。
第四,《公司法》與《反壟斷法》宏觀目標的同一性、中觀目標的同質性和微觀目標的兼容性統一于提升公司活力的基礎之上。公司是創造就業、促進增長、創新科技、增加稅收的永動機,是落實“六穩”“六保”工作的生力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強調,“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到2019年年底,我國已經有市場主體1.23億戶,其中企業3 858萬家,個體工商戶8 261萬戶。[ 4 ]但我國企業競爭力總體不強,僵尸企業數量眾多。原國家工商總局于2013年7月30日發布的《全國內資企業生存時間分析報告》顯示,在我國2000—2013年的新設企業中有半數企業“年齡”不到5歲。[ 5 ]新設企業夭折的原因很多,但與大企業濫用壟斷優勢、排除和限制新興企業進入市場不無聯系。“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公司法》和《反壟斷法》的實施與修改都應致力于促進大企業見賢思齊,并為新興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開拓生存和發展空間。
第五,《公司法》與《反壟斷法》雖各有側重,但均一體遵循民法的九項基本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2020年5月22日于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中指出,我國民事法律制度建設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傳統,把許多商事法律規范納入民法之中。[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是一般法,《公司法》與《反壟斷法》是特別法。《民法典》的一般法功能體現為具體制度的補充適用和基本原則的一體遵循。《民法典》第4條至第9條分別規定平等、自愿、公平、誠信、公序良俗和綠色的六項原則。筆者認為,《民法典》第128條關懷弱勢群體的規定、第132條禁止權利濫用的規定和《民法典》限制公權、保護私權的理念也具備民法基本原則的本質屬性。以上九項原則均普適于公司法律關系和反壟斷法律關系。例如,基于平等原則,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內外資公司、國企和民企、大中小企業必須一碗水端平,不能見客下菜。又如,《反壟斷法》第3條禁止的三類公司壟斷行為(達成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企業集中)本質上都是《民法典》第132條禁止的權利濫用行為。《公司法》與《反壟斷法》既遵循公轉規則,也有自轉規則。《公司法》的四大核心原則是尊重公司生存與發展權、弘揚股權文化、維護交易安全、賦能社會責任。《反壟斷法》的四大核心原則是禁止壟斷行為、鼓勵公平競爭、促進合理集中、確保競爭政策中性。
鑒于和而不同的《公司法》與《反壟斷法》都致力于促進公司可持續發展和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且都遵循《民法典》確立的九項基本原則,立法者應促進兩法聯動修改,實現兩法無縫對接、有機銜接、相互支撐、同頻共振。不能把兩法割裂、孤立甚至對立起來,更不能以《公司法》抑制《反壟斷法》,也不能以《反壟斷法》窒息《公司法》。
三、公司并購反壟斷執法權應保持謙抑性,尊重和保障公司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我國《民法典》第206條第3款首次確認了市場主體的發展權:“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此處的“市場主體”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市場主體僅指企業尤其是公司,廣義的市場主體還包括消費者、勞動者、農民和投資者等民事主體。公司并購反壟斷執法應秉持包容審慎、處罰謙抑、服務能動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有效保障公司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第一,從制度設計目的看,《反壟斷法》的目的是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優化自由公平充分競爭環境,鼓勵公司創新,促進公司可持續健康發展,而促進公司發展的法律邏輯就是尊重和保護公司的自治權、生存權和發展權。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7月21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載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千方百計把市場主體保護好,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為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反壟斷法》應當將充分尊重與有效保障公司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促進公司生存維持與可持續發展明確為反壟斷執法的底線規則。現行《反壟斷法》第5條明確了尊重公司自治、鼓勵公司并購的理念:“經營者可以通過公平競爭、自愿聯合,依法實施集中,擴大經營規模,提高市場競爭能力。”這種與人為善的立法理念應予以繼承和發展,建議將允許型態度改為鼓勵型態度,保護有益社會的公司創新,促進公司并購市場的繁榮與發展。
第二,公司并購反壟斷審查應采取“原則放行、例外禁止”的政策。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必須弘揚契約精神。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強化全社會的契約精神”。契約精神包括契約自由、契約正義與契約嚴守三大元素。契約自由的核心是法無禁止即自由,法無禁止即可為。行政法的主旋律是建設法治政府,規范公權,保護私權。法治政府建設必須恪守主體法定、職權法定與程序法定的三大理念。對反壟斷執法機構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違法作為必問責。對公司而言,只要不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任何公司并購都應受到尊重、保護和鼓勵。《反壟斷法》禁止和限制的公司并購僅限于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例外情形。我國公司并購反壟斷實踐也印證了這一點。據統計,自《反壟斷法》實施以來,反壟斷執法機構審結經營者集中案件超過3 000件,其中禁止2件,附加限制性條件批準48件。[ 7 ]可見,被禁止并購案例尚不及審結案件的千分之一。為明確違反《反壟斷法》的公司并購的民事法律效力,建議《反壟斷法》修改時嚴格區分民事法律規范和行政法律規范,精準甄別強制性公法規范中的效力性規范和管理性規范。[ 8 ]為增強反壟斷執法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繼續保持法治定力,堅持反壟斷執法的常態化、法治化與專業化,不能推行“運動式”“刮風式”執法。要堅守包容審慎、法治理性的理念,預防忽左忽右、忽冷忽熱的執法搖擺現象。
第三,從舉證責任的配置看,建議新《反壟斷法》基于“誰主張、誰舉證”的理念,確立由反壟斷執法機構就公司并購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在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是一般原則,舉證責任倒置是例外規則。在刑事訴訟中,嚴格恪守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控方舉證的理念。在行政執法中,也應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理念。但我國現行《反壟斷法》第28條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作出禁止經營者集中的決定。但是,經營者能夠證明該集中對競爭產生的有利影響明顯大于不利影響,或者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作出對經營者集中不予禁止的決定”。據此,即使經營者集中僅存在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可能性,反壟斷執法機構亦可作出禁止決定,除非公司并購當事人能自證清白,證明自己實施的公司并購利大于弊或符合公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020年1月2日公開征求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反壟斷法〉修訂草案》)第32條延續了該態度。鑒于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可能性不等于現實;鑒于可能性的認定帶有很強的自由裁量特點,由被調查公司自證清白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利弊參半:在降低了執法者舉證負擔的同時,加重了公司的舉證責任,與“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私法自治理念和控方舉證的程序正義理念似有不合。根據私法自治原則,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乃至全社會對民事法律行為都應采取“有效推定”(而非“無效推定”)的態度。為保持反壟斷執法權的謙抑性、提升執法公信力,建議新《反壟斷法》將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改為由反壟斷執法機構就公司并購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這亟需全面提升反壟斷機構的執法能力,也需強化公司配合執法機構調查的義務。但這種配合調查義務不同于自證清白的舉證責任。
第四,從公司并購限制性條件的適用范圍而言,應確立“可限可不限的,堅決不限”的原則立場。我國現行《反壟斷法》第29條既規定了紅燈型禁止或綠燈型放行的處理結果,還增設黃燈型的第三種處理結果:“對不予禁止的經營者集中,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決定附加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條件。”相較于寬松的放行和嚴格的禁止,反壟斷執法機構對公司并購附加限制性條件堪稱溫而不火的中庸之道。但“是藥三分毒”,附加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條件在客觀上會限制商事自由,天然具有一定副作用。為興利除弊,建議從三方面預防限制性條件的濫用:一是嚴格適用范圍。僅對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公司并購附加限制性條件,但不將其適用于不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公司并購。建議《反壟斷法》第29條修改為:“對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決定附加減少集中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限制性條件。”二是嚴格落實反壟斷執法機構的舉證責任規則,并同步夯實公司并購當事人的協助調查義務。三是在確需附加限制性條件時,反壟斷執法機構和并購各方當事人要誠信合作、對等談判和理性博弈,確定可供并購各方自由選擇的多套限制方案。這樣既有助于并購各方合理選擇既能造福其他競爭者、也不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多贏共享方案,也有助于預防損人利己的零和游戲,杜絕損人不利己的多輸同損方案。
第五,反壟斷處罰措施的選擇和使用應體現過罰相當的公平原則和比例原則,確保每份處罰文書經得起法律的檢驗、社會的檢驗、歷史的檢驗乃至國際社會的檢驗,真正取得法律效果、道德效果、政治效果、經濟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處罰阿里巴巴投資收購銀泰商業、騰訊控股企業閱文收購新麗傳媒、豐巢網絡收購中郵智遞的3起未依法申報案件,體現了嚴格精準執法和促進企業發展兼顧的理念,值得肯定。在第一起案件中,設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阿里巴巴投資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通過認購新股和可轉換債券的方式,認購了銀泰商業9.9%的新股股權和可轉換債券。2016年6月,阿里巴巴投資將可轉換債券轉成股份,轉股后持股比例升至27.83%。2017年3月,銀泰商業進行私有化并于2017年6月完成股權交割,阿里巴巴投資持股比例增至73.79%,成為控股股東。2016年阿里巴巴投資的全球營業額為人民幣1 011.43億元,中國境內營業額、銀泰商業的全球和中國境內營業額均達到《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第3條所定申報標準,但阿里巴巴投資未按《反壟斷法》第21條履行申報義務。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經評估市場競爭影響后認為該項經營者集中不會產生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遂依《反壟斷法》第48條對阿里巴巴投資處50萬元人民幣罰款。[ 9 ]由于該條規定的罰款上限是50萬元人民幣,該項處罰已是頂格處罰,鑒于該罰款對大企業的教育效果有限,建議新《反壟斷法》適度提高該條款中的罰款上限,并增設信用責任。[ 10 ]又如,《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的公司違法達成并實施壟斷協議的兩項處罰措施包括“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但在很多案件中,被處罰企業并非指生產和經營涉案產品,而往往同時生產或經營多種產品或服務,而涉案產品違法所得僅占涉案公司年度所得的極小比例。因此,對“違法所得”和“上一年度銷售額”只能做限縮解釋,限定解釋為“涉案產品的違法所得”以及“上一年度涉案產品的銷售額”,而不應擴大解釋為“公司全部違法所得”和“公司上一年度全部銷售額”。限縮解釋符合文義、目的、整體、誠信和習慣的解釋方法,有助于體現因果關系的法治思維,實現精準執法和靶向執法,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四、落實《反壟斷法》的治本之策是激活公司治理機制
就本質而言,中外公司巨頭的壟斷行為無論是達成壟斷協議,還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抑或排除、限制競爭的公司集中,都是公司價值觀和財富觀嚴重扭曲的結果,也是公司治理失靈的結果。壟斷行為往往是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或經營層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深思熟慮的決策結果。有些壟斷行為還是公司重金購買的“錦囊妙計”。解鈴還須系鈴人。睿智的立法者和監管者要善于激活公司治理機制的反壟斷功能。
第一,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法律角色不應該僅僅局限于事后處罰者。其扮演的法律角色應以事先預防者和事中監管者為主,事后處罰者為輔。現行《反壟斷法》第1條揭明的首要立法宗旨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遺憾的是,如何預防壟斷行為并未成為該法的重點內容。實際上,立法者不僅對預防壟斷行為的具體制度設計語焉不詳,而且在列舉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法定職責時也沒有納入行政指導和事中事后監管的職責。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020年1月2日公開征求意見的《〈反壟斷法〉修訂草案》仍偏重于反壟斷案件的事后調查和處理,并未規定事先預防和事中監管制度。市場會失靈,監管者不應失靈。“放管服”改革一個都不能少。“放”的本質是積極不作為,目標是無為而無不為;“管”的本質是審慎執法,目標是管好市場秩序,實現活而有序;“服”(服務或扶持)的本質是積極作為,目標是提升市場活躍度與市場主體活力。其中的“管”包括事先監管、事中監管與事后監管。而行政處罰僅是市場監管工具箱中的一項監管工具,不能取代其他監管職責。為從源頭預防壟斷、實現標本兼治,建議《反壟斷法》專章規定“壟斷行為的預防”,增加執法機構事先預防和事中監管的法定職責。
第二,事先預防和事中監管職責的主要制度抓手是行政指導。在許多案例中,只有在反壟斷執法機構向被調查企業發出調查通知書以后,雙方才正式開始在《反壟斷法》的軌道上正面接觸。為將壟斷行為徹底消滅在萌芽狀態,必須抓早抓小,激活反壟斷行政指導機制。執法機構應針對不同產業和商業模式的公司及其不同的反壟斷法律風險,量體裁衣,提供建設性的規勸與建議,及時為公司扯扯袖、咬咬耳,令其紅紅臉、出出汗、照照鏡、洗洗澡、治治病。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對行政指導意見,被指導公司應從諫如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行政指導有助于構建新型親清政商關系,建設法治政府和有限權力政府,預防公權力不當干預公司生活,避免“父愛主義”越俎代庖的非理性沖動。執法機構應以落實2020年9月11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印發的《經營者反壟斷合規指南》為契機,督導所有規模以上的大中型公司建立反壟斷合規管理制度,弘揚自由公平競爭文化,防范反壟斷合規風險。
第三,行政指導的核心是弘揚公司理性自治精神。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強調,堅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這里的“自治”當然包括公司自治。公司自治精神意味著,公司有權為追求營利目標并承擔社會責任而在不違反強行法和公序良俗的限度內,對內自我設定治理規則,對外自由實施法律行為,理性行使權利,誠信履行義務,獲取商業利益,自擔法律風險。公司自治包括賦能型自由,也包括約束型自律。公司自治精神體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公司作為私法人和營利法人的本質屬性。公司自治精神普適于民營公司和外資公司,也普適于國有公司和混合所有制公司。為在公司自體植入反壟斷基因,立法者、監管者和裁判者應尊重和保障公司的反壟斷自治權。為確保公司理性自治,也要預防和救濟公司自治異化現象,實現公司自治權和監管權、裁判權之間的無縫對接。
第四,大公司應主動將反壟斷合規管理全面納入公司治理體系。反壟斷合規不僅是邏輯縝密的理念,也是系統完善的制度設計,更是自覺自愿的動態實踐。《經營者反壟斷合規指南》鼓勵具備條件的公司建立反壟斷合規管理部門,將反壟斷合規管理納入現有合規管理體系。但因未配套理順反壟斷合規管理部門和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等公司治理機構之間的法律關系和工作流程,有可能導致《經營者反壟斷合規指南》陷入空轉。大公司既要將反壟斷合規基本要求融入公司章程,也要自我加壓、出臺嚴于法定要求的反壟斷自律政策。鑒于大公司反壟斷風險的密集型特點,大公司應在董事會下設反壟斷委員會。由于管理層天然存在追求財務業績最大化的不理性沖動,反壟斷合規部門不宜直接對管理層負責,而應該對董事會及其反壟斷合規委員會負責并報告工作。
第五,建議新《反壟斷法》在借鑒國際慣例和總結我國執法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完整系統的反壟斷受托人制度。商務部2014年發布的《關于經營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條件的規定(試行)》導入了受托人制度,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2020年發布的《經營者集中審查暫行規定》對此予以完善。截至2020年8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附加限制性條件批準的48起案件中有40起委任了受托人。[ 7 ]受托人作為執法機構的“千里眼”和“順風耳”,有助于降低執法成本;受托人作為附加限制性條件義務人的反壟斷“醫生”,有助于督促和提醒義務人守約踐諾,及時履行限制性條件,避免失信風險和行政處罰。但既然委托人是義務人,受托人的報酬亦由義務人支付,就難以確保受托人的獨立性,難以避免受托人被義務人俘虜。《經營者集中審查暫行規定》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遂設立受托人問責機制:一是增加針對受托人的罰款;二是規定受托人在受罰后5年內不得擔任受托人。但客觀而言,這兩項違法成本未必超越受托人的失信收益。為預防受托人道德風險,確保受托人對執法機構和公共利益負責,建議借鑒《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中有關破產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的做法,改由反壟斷執法機構采取輪候、抽簽、搖號等隨機方式指定管理人,報酬依然由義務人負擔,義務人對受托人提供服務時是否誠實守信和勤勉盡責享有監督權,并對受托人的選任行使罷免建議權、報酬酌減請求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
五、公司并購反壟斷中的控制權認定規則應盡量對標對表公司法
控制權是《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下稱《證券法》)和《反壟斷法》都涉及的核心概念,分屬于公司治理、上市公司收購和經營者集中審查。現行《反壟斷法》第20條限定列舉了經營者集中的3種法定情形:①經營者合并;②經營者通過取得股權或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③經營者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其中,后兩種情形都離不開“控制權”的關鍵詞,第一種情形實際上代表著控制權的極致,只不過兩家公司合二為一無須控制權概念而已。由于《公司法》和《反壟斷法》的立法目標、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各有側重,兩法中的“控制權”概念和而不同,既有共性,也有個性。
第一,《公司法》中的控制權概念立足于公司組織體內部,旨在落實控制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和其他股東的義務和責任,確保公司及其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證券法》中的控制權概念立足于資本市場,旨在提高控制權流轉的透明度,激活公司控制權市場,保護公眾投資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維護公眾投資者權益;而《反壟斷法》中的控制權概念立足于產品市場尤其是消費品市場,旨在確定經營者集中的構成標準,確保精準識別、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因此,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局認為,“反壟斷法中的控制權與公司法或者證券法所稱的控制在內涵和外延上均有所不同,是指經營者對其他經營者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重大經營決策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權利或者狀態,包括直接和間接、單獨和共同、積極和消極的控制權,也包括控制的權利和事實狀態。”[ 7 ]由于合同法和交易法范疇的約定控制權與公司法范疇的法定控制權都會成為反壟斷執法的重點,《反壟斷法》關注的控制權的外延要廣于《公司法》中的控制權。例如,特許經營協議、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和資產轉讓協議有可能會約定兩家或者兩家以上公司之間的控制與從屬關系,進而導致經營者集中和產品市場份額的變動,但并不屬于嚴格《公司法》意義上的控制權。
第二,在《公司法》和《反壟斷法》中的控制權存在交叉的情況下,《反壟斷法》原則上應盡量對標對表《公司法》中的控制權概念,不宜疊床架屋地推出兩套不同法律概念。例如,《公司法》第216條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和關聯關系的界定共同構成了控制權的認定規則。其中,“控股股東”是指出資額占有限責任公司資本總額50%以上或持股占股份公司股本總額50%以上的股東;出資額或持股比例雖不足50%,但依其出資額或持股所享表決權已足以對股東會決議產生重大影響的股東。“實際控制人”是指雖非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關聯關系”系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可能導致公司利益轉移的其他關系;但國家控股企業之間不僅因為同受國家控股而具有關聯關系。可見,《公司法》中的控制權人實際上包括兩類主體:控制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反壟斷執法機構審查經營者集中時若涉及控股股東、實控人和關聯關系的概念,應盡量援引《公司法》中的同名概念和法律邏輯。當然,新《公司法》也應與時俱進,拓寬控制權人的外延,確認股權結構高度分散的公司尤其是公眾公司(含上市公司和新三板公司)中的內部控制人(董監高尤其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和總經理等)掌握公司控制權的事實。另外,鑒于控股股東未必享有控制權、控制股東未必擁有多數股份,“控股股東”應易名為“控制股東”。
第三,在傳統公司法中的公司決議規則和控制權規則之外,現代公司法發展出來的新型控制權規則亦應引起反壟斷執法機構重視。就傳統控制權規則而言,股東會決議實行一股一票的資本多數決規則,將直接或間接擁有多數表決權的特定股東的意思表示擬制為公司意思表示;董事會決議實行一人一票的人頭多數決規則,將持有多數表決權的特定董事的意思表示擬制為公司意思表示。但不少科技創新公司開始導入AB股結構為代表的差異化表決權架構。據美國機構投資者理事會(CII)統計,截至2020年12月,277家美國上市公司采取的差異化表決權架構不僅有AB雙重股權結構,也有ABC三重股權架構。有些公司的ABC架構又深入細分,如A系列一股一票,B系列內部分別是一股十票與一股十分之一票,C系列均無表決權。[ 11 ]在我國,《國務院關于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第26條,倡導推動完善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和資本市場相關規則,允許科技企業“同股不同權”。2020年1月20日,在深交所科創板上市的優刻得公司率先推行差異化表決權。根據其章程第77條,除特定事項由AB兩類股東按一股一票規則表決外,就所有股東大會決議案表決時A股每股可投5票,而B股每股可投1票。共同實控人季某等3人本次發行前直接持股僅占26.8347%,而通過設置特別表決權持有64.712 6%的表決權。[ 12 ]對控制權制度的最新演變趨勢,立法者和反壟斷執法機構不可不察。
第四,《經營者集中審查暫行規定》認定控制權的酌量因素應予充實。根據該暫行規定第4條,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判斷公司是否通過交易取得對其他公司的控制權或能對其他公司施加決定性影響時應考慮八大因素:①交易的目的和未來的計劃;②交易前后其他公司的股權結構及其變化;③其他公司股東會表決事項及表決機制以及歷史出席率和表決情況;④其他公司董事會或監事會組成及表決機制;⑤其他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免等;⑥其他公司股東、董事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委托行使投票權、一致行動人等;⑦該公司與其他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商業關系、合作協議等;⑧其他應考慮因素。遺憾的是,上述酌量因素清單忽略了現實生活中許多為規避法律而設計的復雜而非典型的控制權計劃,如借助多層次股權代持和稻草人董監高而遙控公司集團的實際控制人等。建議新《反壟斷法》采取概括列舉和兜底條款的方式,增加實際控制人、隱名控制股東、股權代持、股權質押、“老三會”(如黨委會、工會和職代會)的運營實態及可變利益實體(VIE)一攬子協議(如融資協議、技術支持協議等)等控制權因素。
第五,新《反壟斷法》中的控制權立法定義應盡量與《公司法》同頻共振。《〈反壟斷法〉修訂草案》第23條維持現行《反壟斷法》對經營者集中的三分法,并做了加減法。“減法”系指刪除了第三類中“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的情形,有助于增強控制權識別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避免因“決定性影響”和“控制權”相提并論而導致執法者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加法”是指增加了“控制權”定義:“經營者直接或者間接,單獨或者共同對其他經營者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重大決策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權利或者實際狀態。”按照該定義,“決定性影響”不再和“控制權”比肩而立,而僅系認定控制權存在與否的重要參數。從邏輯上看,該定義較為周延,但因缺乏定量指標,致使控制權認定的執法自由裁量余地較大,對執法公信來說是嚴峻挑戰。建議新《反壟斷法》對控制權的立法定義盡量吸收《公司法》第216條的合理元素,并參酌《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84條,明確控制權的多元化認定指標:持股50%以上的顯名股東和隱名股東;非上市公司可實際支配公司股份表決權超過50%的控制股東或上市公司持股單獨或聯合超過30%的第一大股東;通過實際支配表決權能夠決定公司董事會半數以上成員或董事長、總經理和法定代表人任免的實際控制人;依其可實際支配的表決權或影響力足以對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和管理層的決議產生決定性影響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
六、自我預防壟斷應成為大公司的核心社會責任
公司社會責任已成為現代公司法體系中的新興制度板塊。《公司法》第5條要求公司從事經營活動時遵守法律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公眾監督,承擔社會責任。該條款兼具道德義務的倡導性與法律義務的強制性,具有統率公司法分則規定、指導法律解釋、引導公司經營之效,是《公司法》解釋與適用的價值引領和根本遵循。
主動擔當社會責任已成為主流企業在全球化時代和數字化時代的社會共識與商業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企業既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有社會責任、道德責任。任何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都是社會的企業。社會是企業家施展才華的舞臺。只有真誠回報社會、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家,才能真正得到社會認可,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企業家。”[4]2020年11月12日,他在江蘇調研時又高度評價了清末民初的實業家張謇興辦一系列實業、教育、醫療、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責任擔當。[ 13 ]
筆者認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本質就是增進公益,既要為股東創造投資價值,也要善待勞動者、債權人、供應商、消費者、社區居民、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與公序良俗。樂善好施、修橋鋪路是社會責任,預防壟斷更功德無量。主動自我預防和消除壟斷不僅惠及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及其投資者和勞動者,而且造福廣大消費者,更會優化自由競爭、誠信經營和公平交易的營商生態環境。因此,自我預防壟斷應成為公司主動踐行社會責任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預防壟斷不應消極依賴反壟斷執法機構的高壓監管、公眾輿論的口誅筆伐和市場競爭的淘汰擠壓。
第一,公司要徹底實現反壟斷自覺,必須在內心深處始終保持對全社會的感恩之心。公司要對全體利益相關者(如消費者、投資者、勞動者、中小競爭者、新興企業、科技創新者、債權人、供應商和社區等)常懷感恩之心,全面履行法定義務、約定義務與道德義務。每個利益相關者都是幫助企業生存、成長與壯大的貴人。沒有自由公平成分競爭的檢驗,就沒有真正的優秀企業。回顧其前世今生,中外壟斷企業大都由草根企業經歷自由市場競爭的大浪淘沙而鯉躍龍門。為回報市場與社會,中小企業在轉身成長為一言九鼎的大企業之后不應關閉自由競爭之門,而應繼續擁抱自由公平競爭,自覺抵制狹隘偏執的壟斷沖動。基于新興企業友好型的自由競爭邏輯,大公司必須充分尊重其他企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弘揚競爭精神和契約精神。[ 14 ]企業只有飲水思源、尊老(夕陽產業)愛幼(朝陽產業)、包容新興競爭者,才能展示商業良知、責任擔當和人性光輝。懂得感恩的公司才愿意主動遠離壟斷行為,才敢于繼續通過自由公平競爭而獲取旺盛的生命力與發展力。
第二,大公司要拋棄難以為繼的壟斷暴利最大化思維,確立細水長流的利潤合理化思維。“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公司既具有營利性,也具有社會性。攫取壟斷暴利源于對公司營利性的片面執念,而缺乏對公司社會性的深刻感悟和自覺踐行。市場有眼睛,法律有牙齒。追求壟斷暴利最大化必然會攪亂公平競爭秩序,損害競爭者和消費者權益,觸碰法律底線和商業倫理的紅線。結果,既會招致反壟斷處罰,也會被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和消費品市場的消費者用“腳”和訴狀淘汰。2020年下半年,公眾關注的某些社區團購平臺通過巨額補貼開展低價傾銷的策略值得反思。就專業人才儲備、資本渠道、品牌推廣、大數據分析手段和對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的駕馭能力而言,社區團購平臺和中小菜販相比完全不在同一量級。在擊敗中小菜販后,大平臺有望控制對農產品供給側的全鏈條,進而有能力在壓低產品收購價的同時抬高售價,攫取壟斷暴利。而在獲得壟斷利潤后,平臺企業又會用同樣套路壟斷下一目標產業。公眾輿論之所以強烈譴責社區團購巨頭的補貼套路,主要是由于部分超級大平臺在沒有清除大數據殺熟、二選一、“霸王條款”的情況下,就重操“跑馬圈地”的套路來搞社區團購:先低價傾銷、圈占流量、將中小競爭者“趕盡殺絕”,然后再“磨刀霍霍割韭菜”。這種套路背后追求的依然是壟斷暴利。一些大企業“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教訓極為深刻,不可不察。
第三,大公司的商業模式設計必須植入反壟斷基因。商業模式設計既堅持營利性原則,也恪守合法性底線;既遵循商業邏輯和市場規律,也遵循法律邏輯和法治規律;既堅持包容審慎原則,也堅持法律底線思維,確保商業模式符合公開透明、誠實信用、公平公正、多贏共享、包容普惠、安全可靠、可驗證、可持續、可復制、可推廣的基本要求。商業模式創新也必須堅持誠信和創新并重,更加注重誠信;安全和快捷并重,更加注重安全;公平和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合規和發展并重,更加注重合規;品牌利益和財產利益兼顧,更加注重品牌利益。例如,有些大企業的主要利潤來源是不公平的格式條款(霸王條款),壟斷企業單方自我賦權、單方免除或減輕壟斷企業責任、加重對方責任、剝奪或限制對方主要權利。壟斷企業僅片面強調“契約自由”,而忽視了契約正義;即使談及契約自由,也僅強調單邊的形式意義上的契約自由,而忽視了雙邊的實質意義上的契約自由。許多壟斷企業將“契約自由”理解為形式上的契約自由,尤其是消費者與經營者“簽字”的自由。鑒于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和《民法典》第496條至第498條嚴格規制格式條款,鑒于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機制的逐漸激活,壟斷企業繼續濫用“霸王”條款的商業模式已經變得不可持續。
第四,大公司要以海納百川之心,自覺鼓勵中小企業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及其利益代言人參與公司治理,建立協同共治的公司反壟斷治理體系。例如,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主要定位于中小股東的代言人。鑒于《反壟斷法》旨在遏制壟斷行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既要對公司與中小股東利益負責,也要關懷中小競爭者等其他利益相關者對自由公平充分競爭秩序的利益訴求。這就需要《公司法》擴大獨立董事作為受托人的受益人范圍,確保獨董獨立履職,免受公司控制股東、實際控制人等機構或個人的不當影響。又如,為確保中小競爭者有效制衡壟斷企業的公司決議,建議立法者允許利益相關者對違反《反壟斷法》的公司決議提起決議無效確認之訴、撤銷之訴及不成立確認之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第1條規定:“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等請求確認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無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此中的“等”字應當包括權益遭受壟斷公司決議侵害的中小競爭者。因此,壟斷行為的受害者都可依法提起公司壟斷決議效力之訴。再如,《公司法》和《反壟斷法》應當授權董事會在作出涉及壟斷行為的重大決策時充分考慮并增進中小競爭者、職工、消費者和社區等利益相關者利益。即使董事會決策否決了壟斷行為或者降低甚至取消了壟斷利潤,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也無權推翻董事會決議或者罷免參與決議的董事。
第五,互聯網平臺企業尤其是超級互聯網大平臺企業應率先垂范,爭當自我反壟斷的模范公司。互聯網再大也大不過法網。互聯網平臺企業不應成為《反壟斷法》的法外之地和特權公司。互聯網商業模式項下的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和內容都是真實而具體的,而非虛無縹緲的虛擬世界。平臺企業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締結與履行合同的特殊居間機構,是電商市場存續發展的必需中樞。互聯網平臺企業是編織電商網絡的巨型“蜘蛛”,既搭建網絡交易設施,也制定交易規則與格式條款,更遴選交易伙伴,還提取眾多消費者和企業的交易大數據,并直接受益于消費者與經營者的交易成果。因此,平臺作為市場開辦者與自律監管者,有權也有義務從源頭上杜絕壟斷行為。[ 15 ]《〈反壟斷法〉修訂草案》第21條第2款把超級互聯網大平臺納入立法規制范圍,強調在認定互聯網領域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要考慮網絡效應、規模經濟、鎖定效應、掌握和處理相關數據的能力等因素。這些核心特征抓住了互聯網經濟與數字經濟最核心的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有很強的針對性。建議平臺企業強化問題導向意識,虛心聽取監管者、競爭同行和消費者的合理化反壟斷建議,及時整改商業模式創新中的疑似壟斷行為。平臺企業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徹底清除損害消費者權益的“霸王”合同現象,拋棄為排擠中小競爭者、剝奪電商選擇權、損害消費者公平交易權而強迫電商選邊站隊的“二選一”潛規則。
第六,建議對大公司確立反壟斷信息披露制度。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燈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傳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只強調股東與債權人關注的財務信息,很少涉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關注的社會信息,包括企業反壟斷自律的態度與行動。以信息披露為基礎的反壟斷自律機制與市場競爭機制、政府獎懲機制之間的同頻共振有助于激濁揚清。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出臺《公司反壟斷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指導大公司充分披露反壟斷自律信息,尊重和保障中小競爭者和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和監督權。信息披露要真實、準確、完整,簡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為扭轉“好人受氣、壞人神氣”,劣幣驅逐良幣的不正常現象,政府要善用“胡蘿卜”政策,鼓勵公司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建議政府優先采購自覺預防壟斷供應商提供的貨物、服務和工程。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允許政府采購人優先采購自覺預防壟斷的供應商提供的貨物、服務和工程,并在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中細化優先采購的操作標準(包括優惠幅度)。政府與公司簽訂其他商事合同(如BOT合同、PPP合同和授予特許經營權的其他合同)時也應采取類似政策。對嚴格實行反壟斷自律的公司,監管者應降低對該公司的行政監管成本,放松行政監管要求,合理減免行政處罰。
七、結論
公司是《公司法》和《反壟斷法》共同保護和規范的重要市場主體。但長期以來,在法學研究和執法實踐中仍存在著碎片化和孤島化現象。在兩法雙雙迎來修改之際,立法者應推動兩法的無縫對接、有機銜接、同頻共振、相輔相成。兩法和而不同,都致力于提升公司活力,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都遵循民法基本原則。
公司并購反壟斷執法應秉持包容審慎、處罰謙抑、服務能動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有效保障公司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公司并購反壟斷審查應采取“原則放行、例外禁止”的政策。建議反壟斷執法機構繼續保持法治定力,堅持反壟斷執法的常態化、法治化與專業化,不能推行運動式執法。要堅守包容審慎、法治理性的理念,預防忽左忽右、忽冷忽熱的執法搖擺現象。從舉證責任的配置看,建議新《反壟斷法》基于“誰主張、誰舉證”的理念,確立由反壟斷執法機構就公司并購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需強化公司配合執法機構調查的義務。但這種配合調查義務不同于自證清白的舉證責任。從公司并購限制性條件的適用范圍而言,應確立“可限可不限的,堅決不限”的原則立場。反壟斷處罰措施的選擇和使用應該體現過罰相當的公平原則和比例原則。
睿智的立法者和監管者要善于激活公司治理機制的反壟斷功能。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法律角色應以事先預防者和事中監管者為主、事后處罰者為輔。為從源頭預防壟斷、實現標本兼治,建議《反壟斷法》專章規定“壟斷行為的預防”,增加執法機構事先預防和事中監管的法定職責。事先預防和事中監管的主要抓手是行政指導,行政指導的核心是弘揚公司理性自治精神。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強調,堅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這里的“自治”當然包括公司自治。建議新《反壟斷法》在借鑒國際慣例和總結我國執法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完整系統的反壟斷受托人制度。
公司并購反壟斷中的控制權認定規則應盡量對標對表公司法。由于合同法和交易法范疇的約定控制權與公司法范疇的法定控制權都會成為反壟斷執法的重點,《反壟斷法》關注的控制權的外延要廣于《公司法》中的控制權。例如,特許經營協議、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和資產轉讓協議有可能會約定兩家或者兩家以上公司之間的控制與從屬關系、進而導致經營者集中和產品市場份額的變動,但并不屬于嚴格《公司法》意義上的控制權。但在《公司法》和《反壟斷法》中的控制權存在交叉的情況下,《反壟斷法》原則上應盡量對標對表《公司法》中的控制權概念,不宜疊床架屋地推出兩套不同法律概念。在傳統公司法中的公司決議規則和控制權規則之外,現代公司法發展出來的新型控制權規則(尤其是科技創新公司導入的AB股結構)亦應引起反壟斷執法機構重視。《經營者集中審查暫行規定》認定控制權的酌量因素應予充實。新《反壟斷法》中的控制權立法定義應盡量與《公司法》同頻共振。
自我預防壟斷應成為大公司的核心社會責任。公司要徹底實現反壟斷自覺,必須在內心深處始終保持對全社會的感恩之心。大公司要拋棄難以為繼的壟斷暴利最大化思維,確立細水長流的利潤合理化思維。大公司的商業模式設計必須植入反壟斷基因。大公司要以海納百川之心,自覺鼓勵中小企業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及其利益代言人參與公司治理,建立協同共治的公司反壟斷治理體系。互聯網平臺企業尤其是超級互聯網大平臺企業應率先垂范,爭當自我反壟斷的模范公司。建議對大公司確立反壟斷信息披露制度。
法行天下,德潤心田。法律不是萬能的。嚴格自律,才能鑄造商業公信。為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大公司既要履行法律義務,也要敢于自我加壓,自覺履行道德義務,擔當社會道義。例如,2017年修改前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曾禁止大中小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為擠垮同行競爭對手而低價傾銷。遺憾的是,該條款在2017年修法時被刪除,主要理由不是因為立法者有意允許和鼓勵傾銷,而是《反壟斷法》第17條第2項也明文禁止企業將傾銷作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手段,因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在禁止傾銷問題上存在不必要的重復性規定。筆者對此難以茍同。首先,原《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能周延地將壟斷企業和非壟斷企業的傾銷行為一網打盡,即使新興的未來壟斷企業在誕生和成長階段也不得傾銷。因此,以“先燒錢圈流量、后割韭菜”為主要競爭策略的新興互聯網企業認為該條款是阻礙其快速崛起的最大制度障礙,規定重復僅是立法游說的理由而已。其次,兩法之間并不存在不必要的重復性規定。《反壟斷法》第17條第2項禁止傾銷的企業外延遠遠窄于原《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因為該款僅適用于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但不適用于雖采取低價傾銷策略、但尚不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成長中企業。從立法的周延性角度看,一方面,原《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禁止非壟斷企業尤其是新興企業傾銷的條款被刪除;另一方面,《反壟斷法》又力不從心,無法調整非壟斷企業尤其是新興互聯網企業的傾銷行為。從企業的競爭策略看,壟斷企業在崛起之前完全不受《反壟斷法》第17條第2項的規制,而一旦崛起為壟斷巨頭也就不再需要實施傾銷策略。可見,2017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刪除傾銷條款留下了巨大的法律漏洞。這也客觀上使得一些新興互聯網企業通過“燒錢”補貼、低價傾銷的不正當競爭手段而迅速獨霸市場、崛起為互聯網巨頭。希望成長中的互聯網企業在崛起之前自愿放棄低價傾銷的厚黑之術。誠如是,既能有效填補《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間的制度盲區,也能徹底蕩滌互聯網經濟領域的壟斷潛規則,更能真正贏得全社會的尊重與信賴,進一步增強企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畢竟,市場有眼睛,法律有牙齒。
參考文獻:
[1]周程程.中央要求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N].經濟日報,2020-12-14(2).
[2]陳和華.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局主要負責人就阿里巴巴投資收購銀泰商業、騰訊控股企業閱文收購新麗傳媒、豐巢網絡收購中郵智遞三起未依法申報案件處罰情況答記者問[N].中國市場監管報,2020-12-15(1).
[3]劉俊海.論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法治保障體系[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5):28-38.
[4]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0-07-22(2).
[5]成慧.半數企業“年齡”不到五歲[N].人民日報,2013-07-31(10).
[6]王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EB/OL].(2020-05-22)[2021-01-09]. http://www. npc.gov.cn/npc/c30834/202005/50c0b507ad32464aba87c2e a65bea00d.shtml.
[7]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局.健全反壟斷審查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經營者集中審查暫行規定》解讀[J].競爭政策研究,2020(4):27.
[8]劉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權簽署的擔保合同效力規范的反思與重構[J].中國法學,2020(5):225.
[9]反壟斷局.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阿里巴巴投資收購銀泰商業股權未依法申報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行政處罰決定書[EB/OL].(2020-12-14)[2021-01-19].http://www.samr. gov.cn/fldj/tzgg/xzcf/202012/t20201214_324334.html.
[10]劉俊海.信用責任:正在生長中的第四大法律責任[J].法學論壇,2019(6):5-17.
[11]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Dual Class Companies List[EB/OL].(2012-12-20)[2021-01-09].https://www.cii. org/files/Formatted%20Dual%20Class%20List%2012-14-20.pdf.
[12]北京市君合律師事務所.關于優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之法律意見書[EB/OL].(2019-10-10)[2021-01-09].http:// www.csrc.gov.cn/pub/newsite/fxjgb/kcbzczl/kcbzcsqwj/2019 10/P020191010346126719899.pdf.
[13]何聰.實業報國實干興邦[N].人民日報,2020-12-02(5).
[14]劉俊海.論新時代的契約精神[J].揚州大學學報,2018(4):29.
[15]劉俊海.增強電子商務法可訴性優化電子商務生態環境[J].人民司法(應用),2019(1):6.
責任編輯:林英澤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rporate Law and Anti-Monopoly Law
LIU Jun-hai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Corporations are the important market players that are jointly protected and regulated by both Corporate Law and Anti-Monopoly Law. However,Corporate Law and Anti-Monopoly Law are fragmented and isolated each other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legal enforcement. It is advised that the legislature should reform Corporate Law and Anti- Monopoly Law in a harmonious,interactive,inter-connected,coherent and balanced way. Both Corporate Law and Anti-Monopoly Law,guided b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aim at promoting corporate vitality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legal enforcement,the anti-monopoly agencies should be inclusive and prudent in regulation,moderate in imposing penalties,and active in service,so as to fully respect and guarantee the corporate right of surviv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nti-monopoly censorship should follow the policy of general permit and exceptional forbiddance. The author advises the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keep strong willpower based on rule of law,adhere to the normalization,rule of law and professionalismin legalenforcement. Based on thephilosophy of theonus of proof on theclaimant,itis suggested thatthenew AntiMonopoly Law should establish the general principle that the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agencies shall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e fact tha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the effect of excluding and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As far a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concerned,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should be avoided whenever it is not necessary. The choice and use of anti-monopoly penalties should reflect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proportionality in terms of fault and penalty. It is suggested that a special chapter of prevention of monopoly behavior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nti-Monopoly Law to empower the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prevent the monopoly ex ante and supervise the monopoly in progress. The key strategy of the enforcement of Anti-Monopoly Law is to activat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rule on determining corporate control right in cas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s the company law as far as possible.Self-preventionofmonopolyshouldbecomethecoresocialresponsibilityofgiantcorporations.
Key words:corporate law;anti-monopoly law;corporate right to survive and develop;corporate autonomy;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