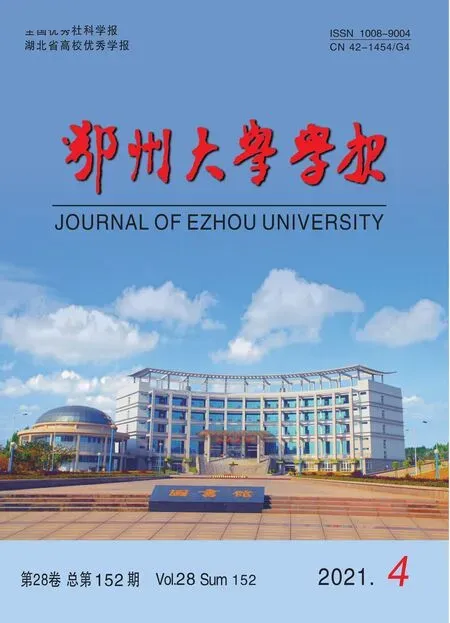論違法性認識是否必要
張秀玲,吳宏丹
(內蒙古大學法學院,內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一、問題的提出
(一)司法案件對不要說的質疑
1.案件詳情
2019 年4 月,案件當事人吳某從陳某經營的養殖場中,收購蘇卡達陸龜共計20 只。經鑒定,蘇卡達陸龜屬于《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物種,2019 年5 月10 日被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6 月13 日海口市秀英區人民檢察院以吳某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判決吳某構成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①,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中,吳某辯護律師稱吳某所收購的蘇卡達陸龜是從取得出售蘇卡達陸龜經驗許可的養殖場購買,養殖場內的蘇卡達陸龜屬于人工馴養繁殖動物而非自然環境下的野生動物,被告人吳某缺乏認識行為觸犯法律的可能性。吳某存在違法性認識錯誤難以避免,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該辯護意見并沒有被二審法院采納。
2.爭議焦點
案件判決后引起軒然大波,行為人確實不知關于違法行為的相關規定,不知違法卻要嚴格追究其刑事責任違背公平原則。該案中,首先吳某所收購的蘇卡達陸龜是從取得出售蘇卡達陸龜經驗許可的養殖場所購買,吳某出于對政府的信任,產生了不可避免的違法性認識錯誤。其次,吳某所購買的蘇卡達陸龜是人工馴養繁殖而非自然環境下的野生動物,吳某不能認識到人工馴養繁殖的陸龜屬于野生動物。最后,蘇卡達陸龜屬于《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所規定的野生動物,吳某是農民,其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決定其難以認識國際條約的相關規定。因此,吳某存在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極低,不具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但是法院所作出判決中并沒有考慮該因素。
近幾年,天津擺射擊攤案、深圳鸚鵡案、河南農民逮癩蛤蟆案等相關涉及違法性認識錯誤問題的案件越來越多,并不斷出現于公眾視野中引起公眾的討論,公眾普遍從自身出發對該類案件進行激烈討論并有部分公眾質疑法院的最終判決。但事實上,該類案件經過公眾討論的是其中一部分,還有很多案件并未得到公眾的關注。在該類案件中,訴訟被告人及辯護人都以違法性認識為依據進行抗辯,認為因此行為具有違法性認識錯誤,應當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針對該類案件,法院的態度則不盡一致,一部分法院對該理由默示,認為其不構成抗辯理由,也有一部分法院在判決中明確回應認為違法性認識錯誤不應當影響犯罪的成立。對于這類判決,公眾認為其不符合社會常識,由此對此類判決產生強烈的不滿及對抗情緒。公眾普遍認為,在被告人不具有違法意圖時,僅因為觸犯其根本不知道的法律規定便對其進行嚴苛的判決,有違公平性、合理性原則。由此引發社會各界對于違法性認識是否影響定罪以及量刑的關注。
(二)理論上不要說的動搖
根據古羅馬法“不知法不免責”的原則,行為人不具有法的認識與其是否構成犯罪無關。曾經,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刑法典都明確規定行為人即使具有違法性認識錯誤也不影響其刑事責任的承擔。乃至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國家遵循這一古老的法律原則和規定。我國自開啟法制建設以來,一直明確對“不知法不免責”進行規定,直至1979 年才將其規定刪除。但法條的相關刪除卻并不意味著司法實踐的改變,時至今日,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仍偏重結果認為其只有具備危害社會的損害結果同時具有危害社會結果的認識便應當對其追究刑事責任,對于行為人的違法性認識因素則不納入考慮。[1]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社會的發展,傳統社會的相關觀念勢必已經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而與現代社會產生沖突。現代社會相對于犯罪人的處罰相比更為重視“人”所具有的基本權利,即“人權”。因此,很多國家出于保護人權的目的更加傾向適用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改變了對于“違法性認識不要說”的堅持。我國司法實踐雖一直堅持“違法性認識不要說”,但隨著當前刑事立法中法定犯數量的增多以及公眾及輿論對其的質疑,促使“違法性認識必要說”逐步得到了越來越多刑法學者的接納及認同。可以說,“違法性認識必要說”相比“違法性認識不要說”更順應時代的需求與社會的需要。
二、必要說的理論上合理性
(一)重新審視違法性認識不要說
違法性認識不要說是指,在認定是否應當追求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時,無需考慮其是否具有違法性認識或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該因素不影響犯罪的成立。日本學者大塚仁認為,判斷行為人認識的主觀認識時,只要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具體事實就可以,不必須認為其行為的違法。[2]
世界曾普遍認可違法性認識不要說,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違法性認識不要說其本質是知法推定。立法只是將社會中最基本的倫理道德以法律的形式呈現,社會公民一旦認識其違反社會基本倫理道德,便可以認識其可能觸犯法律,缺乏認識是基于其未履行注意義務或疏于學習基本社會倫理道德。第二,國家統治地位的需求。傳統社會認為,國家的功能是統治及管理民眾,而非現代社會追求的維護公民的權利及利益。國家為了樹立其權威性的地位以達成統治的目的,將知法的義務強制分配至公眾,要求其應當乃至必須知法以達成統治的目的。此外,形勢政策內在要求應當認同違法性認識不要說。有學者認為,違法性認識不要說的提出是為了避免在司法實踐中一些犯罪分子以其不具有違法性認識為借口來逃避法律的制裁。
自清末我國開啟法制建設進程以來直至1979年頒布《刑法》,我國在《刑法典》以及《刑法修正案》中均明確體現了不知法不免責的思想,這一思想也逐漸成為了刑法學中的基本思想。但是,隨著人權運動的興起,既有觀念不斷隨著現代社會的變化而受到沖擊。該思想也逐漸與現代社會的需求相違背。我國刑事立法觀念不斷發生變化,發生了從自然犯到法定犯的轉變。在自然犯時代背景下,違法性不要說認為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只需具有社會危害性認識,而無需具有違法性認識,不知法容易成為犯罪分子鉆“法律空子”的借口。這一觀點與當時社會需求相匹配,當時我國處于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嚴厲的刑事制裁更易維護社會穩定,這也與當時我國的法治發展水平相適應。隨著時代的變化,先進的刑法更加注重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市場經濟犯罪等法定犯領域,我國逐步進入法定犯時代。法定犯時代其中重要表現之一便是法條的增多,對于犯罪事無巨細的規定。一些法條的規定超出公眾的倫理認知,法律的專業性增強,“法盲”增多。突破不知法不免責的“知法推定”,不知法不免責已經不再適應法定犯時代。
此外,違法性認識不要說不符合人權保護的要求。在傳統社會中,國家為維護其統治地位和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因此更加支持違法性認識不要說。陳興良教授認為,違法性認識不要說本質是“國家權威主義”的體現,通過將不懂法產生不良后果的風險轉移到個人,進行 “人人都當知法”的推論。[3]勞東燕教授指出,該種觀念本質是將風險全部分配至公民,從而回避國家應當承當的風險,是一種顯示公平的分配方式。[4]現代社會要求尊重以及保障人權,堅持違法性認識不要說顯然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違反罪刑法定主義與責任主義的要求,不適用刑法謙抑性的趨勢。再堅持適用“違法性認識不要說”已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因此,刑法學界逐步呈現在法定犯時代下逐步接納違法性認識必要說的趨勢,違法性認識不要說已不再適應我國發展及法治建設的需求。
(二)提倡違法性認識必要說
違法性認識必要說認為違法性認識應當成為構成要件之一,在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之時,除應認識到犯罪事實還應具備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不具有違法性認識可能性不應當構成犯罪。我國刑法學者也逐步呈現支持違法性認識必要說的趨勢。首先,違法性認識必要說體現了責任主義的要求。責任主義提出應當限制國家權力保護公民權利,只有行為人擁有主觀過錯才可對其施加責任,客觀歸責顯示公平。馮軍教授認為,只有在違法性認識支配下的行為,才能對人進行譴責。[5]國家不應當將知法的義務強制分配給個人,要求每個人均對繁雜的法律熟知,這本質上是國家霸權主義表現。國家不應不受限制的將知法的義務強制分配給公民,應當受到責任主義的制約。因此,為了更好地貫徹責任主義,也應該堅持必要說。
其次,必要說順應了刑法謙抑性的趨勢。刑法謙抑性是指限制刑法的嚴苛適用,通過對刑罰清緩化的適用,保護人權,注重保護人的基本權利。當前,刑法謙抑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主流趨勢。近年來,我國的刑事立法大幅增加法定犯的規定,再進行知法推定顯然與現實不符。因此,將違法性認識必要說也納入犯罪構成要件之一顯然是有必要的,不能僅出于打擊犯罪的目的而僅考慮適用違法性認識不要說。最后,堅持違法性認識必要說是出于維護法律權威的要求。近些年來,違法性認識相關案件被追究刑事責任因與大眾認知不符被大眾及公眾輿論抨擊,產生質疑司法公正的趨勢,也由此挑戰了法律的權威性。提倡違法性認識必要說顯然更符合社會公眾的認知,容易被社會公眾所接納,有助于樹立法律的權威性。
三、“必要說”司法實踐性
現今,我國刑法犯罪構成四要件中故意及過失均是以社會危害性認識為規定的,導致司法實踐中我國法院在進行判決時,并不會將違法性認識納入考慮因素。正因如此,相關案件出現后,公眾不能理解法院的相關判決,逐漸引起輿論的爭議,司法權威性遭到破壞。我們應當理解,法律的演進與轉化是一個緩慢且長久的過程,從完全認知到掙脫束縛,需要一個過程。當出現新的理論之時,首先需要學界的廣泛討論,最終形成一套最適應中國的理論方針,其次需要在實踐中對此不斷進行適用。這正是法律安定性及穩定性的體現。正如車浩教授認為,犯罪論及刑法學的演進和多元化,是一個從既有觀念中掙脫束縛的緩慢過程。[6]當前,刑法學界應當首先解決適用違法性認識是否會輕縱犯罪的疑問,其次應當由此提出實踐層面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僅在理論層面對該問題進行爭議。理論的發展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司法實踐問題,堅持違法性認識必要說在司法實踐的運用上是可行的,筆者主要從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兩方面加以論述。
(一)司法解釋
當前我國并未完全接納 “違法性認識必要說”,其中一個因素是“違法性認識”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運用中的復雜性。“違法性認識”如何判斷,是基于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對主觀認識進行客觀判斷本就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違法性認識必要說”作為我國理論界提出的新刑法理論,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對其適用進行具體規定,以解決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難題。
首先,可以通過司法解釋規定,當可能需要適用“違法性認識必要說”時,認定方法可以采取主客觀相結合的方法。第一,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知法的可能性,而不進行一味地“知法推定”。知法可能性的判斷首先可以通過判斷其是否有知法障礙來判斷,如是否行為人的行為是突然由于出臺新法而難以認識到其行為是犯罪的。比如在前文的案件中,飼養行為是公民認可的日常行為規定,但我國由于保護環境以及保護珍貴瀕臨滅絕的動植物的需求將飼養某類動物規定為犯罪,而這類動物也并不是大眾所熟知的瀕臨滅絕的動植物。此外,在該案件中爭議焦點的龜是人工繁殖龜類,一般群眾也難以認為其應當是法律所保護的珍貴瀕臨滅絕的動植物。因此,可以推定客觀上被告人確實不具有知法的可能性。因此,筆者認為在判斷此類案件時,應當將知法客觀可能性納入定罪及量刑的考慮因素中來。其次,應當判斷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否主觀上有想要知法的努力。例如行為人在不知自己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通過向權威機構咨詢的方式,出于對國家機關的信賴利益作出違法行為也應當認可其不具有知法的可能性。學者趙星提出,在判斷行為人是否可能具有違法性認識時,應當根據教育程度、家庭背景、職業、經歷等因素綜合進行判斷。[7]
其次,可以通過司法解釋規定,在涉及違法性認識問題判斷時,應當以“行為人認識為主,一般人認識為輔”為判斷依據。具體而言,行為人由于不知法或對法律規定產生重大誤解產生違法性認識錯誤之時,應當認為這種錯誤是行為人綜合因素所決定。因此,對其是否進行違法性認識問題進行判斷時,除應當考慮其客觀條件及主觀思想條件以外,還應當納入一般人的認知作為參考標準,以避免不被大眾所理解,損害法律的權威性,引起公眾的誤解。
最后,司法解釋可以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證明方法,通過將違法性認識錯誤的舉證責任歸于行為人的方式,來解決該問題的證明問題。如何認定以及判斷違法性認識錯誤的證明在司法實踐中非常復雜難以判斷,甚至一度司法機關認為這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也正因如此,司法機關對該問題進行刻意回避乃至直接對該問題進行忽略,而不對其進行認定以及判斷。站在實踐角度,要求司法機關對每一案件逐一證明確實將極大增加司法機關的工作量,當前我國司法機關出于我國人口眾多的壓力本身工作量便超越普通工作,再加入該問題勢必會導致司法機關的無效率問題。因此,筆者認為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司法機關通過要求行為人對所提出的抗辯舉證,司法機關僅承擔對其提交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判斷的工作,如果行為人確實能夠證明其存在不具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且已經完全盡到注意義務時,可以認為其阻卻犯罪成立。
(二)指導性案例
現有各國的司法判例已經出現突破刑事立法規定的趨勢,采用違法性認識期待可能性說作為裁判依據。如日本“羽田機場大廳示威實踐”一案中,日本最高法院便認為“在違法性認識錯誤上,具有相當的理由時就可以不成立犯罪。”[8]
美國刑法學界以及司法實踐也逐漸產生與以往“不知法不免責”的觀念相反的觀點,認為法律認識錯誤可以成為抗辯的立場之一。[9]如美國案件“藍波特案”被告人藍波特夫人違反了洛杉磯市規定作為受刑人在洛杉磯逗留5 天以上卻并未向警察局報告而被判處250 美元罰金和3 年緩刑的案件,被告人認為自己不知其法律規定不應被追責為抗辯理由進行上訴,最終導致聯邦最高法院對原判撤銷。
我國雖然不是判例法國家而是成文法國家,判例并不是我國法律的正式淵源。但是我國可以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對該類案件進行指導,以避免同一情況適用不同法的爭議。違法性認識錯誤類案件,我國可以通過對典型案件進行收錄指導的方式,對司法實踐提供實踐辦案指導。如此可以解決一些同案不同判的爭議性案件,提高司法公信力。
注釋:
①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9)瓊01 刑初166 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