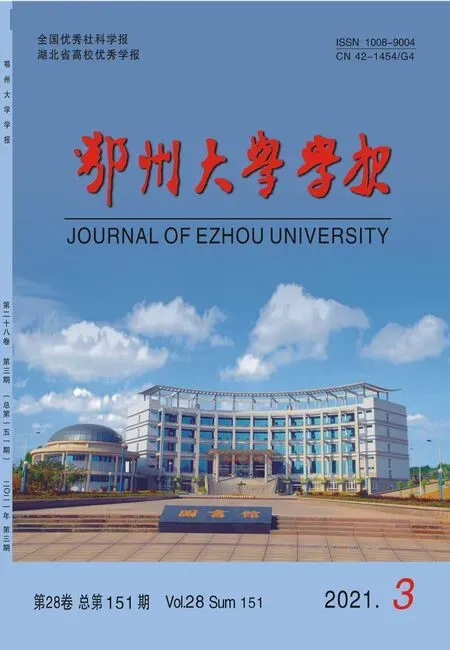《枕中記》的三復(fù)結(jié)構(gòu)與《莊子》“攖而后成”的寓言精神
張宏
(上海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上海 201620)
一、《枕中記》主旨在“窒欲”
唐李肇說“沈既濟(jì)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枕中記》因為有“夢”被認(rèn)為來自于《莊子》,再就是《枕中記》即《莊子》哲學(xué)觀世俗方式的體現(xiàn)。
沈既濟(jì)寫《枕中記》的目的當(dāng)在“窒欲”。《莊子·大宗師》認(rèn)為“其耆欲深者,其天機(jī)淺。”[1]209盧生正是“天機(jī)淺”而“耆欲深者”,不是其寢不夢的“真人”[1]209。
《枕中記》文末直接點(diǎn)出“夫?qū)櫲柚溃F達(dá)之運(yùn),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窒欲”不是“無欲”,而是如魯迅先生說:“這是勸人不要躁進(jìn),把功名富貴,看淡些的意思。”[2]
但要“窒”的“欲”是什么樣子的,《莊子》作為哲理書,微言大義,不可能具體而微,何況過于具體也就有相應(yīng)的局限。《莊子》作為哲理書,雖已經(jīng)用“寓言”盡量闡述無上妙理,但總失之于抽象,所以“小說”作為情節(jié)具體而描摹細(xì)微者,便可借故事內(nèi)容,也就是“飾小說”。
在沈既濟(jì)的《枕中記》中,人生之樂,包括建功立業(yè),最終夢醒。即郭象言:“世有假寐而夢經(jīng)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作為“小道”的“小說”,就可以用各種世俗化的意象進(jìn)行演繹。如“寵辱之道”,《枕中記》就用“嘉謨密令,一日三接”和“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來表現(xiàn);“窮達(dá)之運(yùn)”,對應(yīng)的是“減罪死,投驩州。數(shù)年,帝知冤,復(fù)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
《枕中記》中的“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余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后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后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shù)”正對應(yīng)著《莊子·至樂》“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1]541世人所普遍追求的,如沈既濟(jì)同時代的權(quán)德輿《哭李晦群崔季文二處士》:“華封西祝堯,貴壽多男子”,在《枕中記》中也有所體現(xiàn)。如“年逾八十”“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shù)”“生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有孫十余人”,《莊子·天地》中否定的,都是《枕中記》盧生曾經(jīng)追求的。
二、“窒欲”的方式“攖而后成”
莊子主張的并不是不被擾亂的寧靜,而是經(jīng)歷過的“攖而后成”。如果沒有經(jīng)歷“寵辱”“窮達(dá)”“得喪”“死生”,談不上“其出不欣,其入不距”。
盧生領(lǐng)悟到夢中經(jīng)歷是為了“窒”吾欲,《爾雅·釋言》釋“窒,塞也”,《疏》謂“堙塞”,又《廣雅》曰“窒,滿也”。可以看出“窒”有通過“滿足”而“堙塞”之意。也就是通過“攖”[1]231而達(dá)到“寧”。
人生如夢,夢也可以看作具體而微的人生,夢中經(jīng)歷,雖不如親歷,聊勝于無。盧生就這樣通過呂翁枕入夢,最大限度地“仿真”遍歷人生況味,包括大起大落,引發(fā)心神的激蕩,這就是所謂的“攖”,最終達(dá)到“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的狀態(tài),“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fù)之”[1]210的理想狀態(tài)。
盧生所說的“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在《易》中有相近說法:“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孔穎達(dá)疏:“君子以法此損道懲止忿怒,窒塞情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懲忿”,忿從何來?“窒欲”,欲是進(jìn)取之欲。往往是進(jìn)取的受挫。進(jìn)取過于熱切,卻不能收到相應(yīng)的回饋,受到打擊,該如何對待?這其實還是《莊子·至樂》提出的“奚為奚據(jù)?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1]540盧生意識到了“此先生所以窒吾欲”,既“息其既往”又“閉其將來”。
唐時風(fēng)尚并不鄙視“進(jìn)”,《隋唐嘉話》載“元超三恨”(“進(jìn)士及第”“娶五姓女”與“修史”),頗能揭示唐時讀書人對仕宦的追求。唐人對仕途的追求,不能看做庸俗化的求功名。盧生追求的并不是尸位素餐,游樂無度。他是有追求的,不能因文中“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就一概而論之,認(rèn)為是“祿蠹”。
“達(dá)則兼濟(jì)天下”本就是儒家認(rèn)可的正當(dāng)追求,建功立業(yè)也是“三不朽”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沈既濟(jì)生活的時代,不主張的是太過熱切的“躁進(jìn)”。如《舊唐書》 記載:“貶刑部員外郎舒元輿為著作郎。元輿累上表請自效,并進(jìn)文章,朝議責(zé)其躁進(jìn)也。”
《枕中記》中盧生的追求,不僅有享樂追求,還有建功立業(yè)的正面成分。寵辱得失,夢中皆讓他經(jīng)歷。夢中遇大難有反思,再加上夢醒(覺)時分的頓悟,終練就寵辱不驚。正如吳客在楚太子面前沒有說半句奉承獻(xiàn)媚的話,而是理直氣壯地告訴楚太子如何享樂,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從而證實了《七發(fā)》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療楚太子疾病的有效方法。
劉勰《文心雕龍·雜文》:“枚乘摛艷,首制《七發(fā)》,腴辭云構(gòu),夸麗風(fēng)駭。蓋七竅所發(fā),發(fā)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枕中記》中一切世人夢寐以求的,盧生都得到了,這也是《枕中記》“戒”之所在。
將抽象的哲學(xué)沉淀為小說精神,這一點(diǎn)不僅《枕中記》有非常明顯的體現(xiàn),后世蒲松齡《嬰寧》篇也是如此。[3]
三、三復(fù)結(jié)構(gòu)對“攖寧”的強(qiáng)化與升華
《焦湖廟祝》中湯林的夢中經(jīng)歷不過數(shù)載,而《枕中記》夢中部分長達(dá)五十余年,比《焦湖廟祝》之夢繁復(fù)得多,在情節(jié)安排上卻能做到委宛曲折,搖曳多姿,這得益于其“三復(fù)結(jié)構(gòu)”。
《枕中記》中盧生在夢中經(jīng)歷的人生可以看出是明顯的“三起三落”。
第一次“起”:枕而入夢——舉進(jìn)士——釋褐秘校——應(yīng)制———轉(zhuǎn)渭南尉——俄遷監(jiān)察御史——轉(zhuǎn)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陜牧,鑿河刻石——移節(jié)卞州,領(lǐng)河南道采訪使——征為京兆尹——除生御史中丞、河西節(jié)度使。立石于居延山以頌之——轉(zhuǎn)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第一次“落”:貶為端州刺史。
第二次“起”:三年,征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zhí)大政十余年,號為賢相。
第二次“落”:同列害之,復(fù)誣與邊將交結(jié),所圖不軌。制下獄。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dú)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
第三次“起”:數(shù)年,帝知冤,復(fù)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
第三次“落”:是夕,薨。
這樣,從入夢開始,起——落——起——落——起——薨,即出夢。
“三復(fù)”不僅是形式結(jié)構(gòu)上的,也是哲學(xué)意義上的。“三”在老莊哲學(xué)中,為“生萬物”和“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的臨界點(diǎn),也就是說,“三”為有限之極,又為無限之始,其為萬物生化之關(guān)鍵,是顯然的。[4]
一“攖”是很容易反復(fù)的,必須再而三,才可以真正“攖而后成”。就如杜貴晨言“三復(fù)情節(jié)本是古代中國人固有觀念和習(xí)俗的文學(xué)創(chuàng)造,自然合乎其審美理想。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的審美期待中,關(guān)于克服某一重大困難的故事,當(dāng)事人的努力重復(fù)到三次而取得成功,是最佳的境界,少于或者多于三次,都會是一種不滿足。”[5]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還有一個隱蔽的三重結(jié)構(gòu)。即心、人、旅這個三重結(jié)構(gòu)。
《莊子·德充符》中,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的回答是:“唯止能止眾止。”又曰:“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1]179
心寓于人,《枕中記》中人又寓于邸舍(逆旅),其實也是“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之意。
道士“呂”翁,也是作者筆弄狡獪。
呂翁并非“八仙故事”中“呂洞賓”。沈既濟(jì)寫《枕中記》時,呂洞賓傳說還未盛行,魯迅《古籍序跋集》《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云:“原文呂翁無名,《邯鄲記》實以呂洞賓,殊誤。洞賓以開成年下第入山,在開元后,不應(yīng)先已得神仙術(shù),且稱翁也。”
此翁被稱為“呂”,倒是頗值得注意的。“呂”,是“脊”的本字,本為兩個脊骨相連的形狀,東漢許慎《說文》有此解:“呂,脊骨也。象形。”
這不正是《莊子·至樂》中“空髑髏”的變相嗎?
“呂”又通“旅”,即邸舍。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就有:“自今以來,叚門逆呂,贅婿后父,勿令為戶,勿鼠田宇。”
所謂“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呂”翁就是在邯鄲道上的“旅”(邸舍),遇到了“旅”中少年盧生。
由此觀之,《枕中記》中之邯鄲道上“邸舍”也是虛實相生。這一點(diǎn),也是與《莊子》撲朔迷離的文風(fēng)一致。
《枕中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shù)水平,高出其他同類小說,除了出現(xiàn)的時間早之外,也有一點(diǎn)是因為敘事的撲朔迷離。
《枕中記》幻中出奇,幻中有幻,文章寫作時間在大歷年間或建中年間,寫“開元”“驃騎大將軍高力士”,頗有“閑坐說玄宗”的滄桑幻滅感。
唐李肇認(rèn)為:“沈既濟(jì)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也。”[6]55李肇認(rèn)為的“史才”,是指“紀(jì)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fēng)俗。”[6]3《唐語林》亦贊“沈既濟(jì)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7]唐傳奇眾多作品中,唯將沈既濟(jì)《枕中記》和韓愈《毛穎傳》相提并論,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