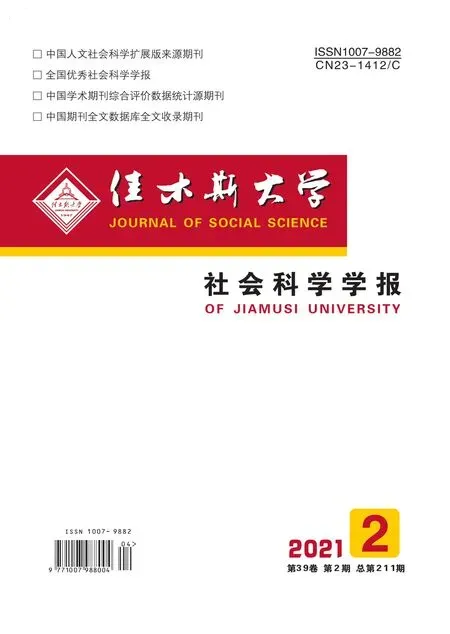大清相國清幾許*
——論《大清相國》的敘事策略及現實意義
李慧娟,彭在欽
(湖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
《大清相國》既是一部清朝反貪史,又是一部政治教科書和為官啟示錄。它的敘事策略相較于《張居正》《大秦帝國》等其他新世紀長篇歷史小說,其共性在于作家創作均重視史實和虛構關系的處理,以現代意識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審美觀照,不同之處在于《大清相國》小說敘事的戲劇化傾向更為明顯,體現在情節轉場、懸念設置、人物刻畫,敘事語言等方面,即故事性強于文學性。主人公陳廷敬宦海沉浮五十余年終由青年士子蛻變為帝國首輔,這一“完人”形象的塑造,不僅表達了作者對古代賢臣名相的景仰和敬佩之情,也寄托了作者濟世救民的理想主義情懷。
一、史實與虛構相結合的藝術化構思
歷史題材小說敘事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能把握好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關系。毫無根據的肆意虛構是對特定時代歷史文明的褻瀆,故作家在歷史小說創作過程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風俗以及典章制度等,都不能憑空捏造,相悖于歷史真實。如《大清相國》中陳廷敬這一原型人物的生平事跡便是取材于《清史稿·陳廷敬傳》、自隋朝以來的人才選拔機制科舉考試為主人公仕途生涯的開啟提供了契機、開明君主順治帝和康熙帝知人善任、虛心納諫,為陳廷敬屢次犯顏直諫提供了可能、康熙年間在云南各地實行大戶統籌符合歷史記載、以及在小說中所提及的除鰲拜、平三藩、收臺灣、征葛爾丹等重大歷史事件均在史料有所記載。
歷史小說敘事并非局限于對歷史細節的精細還原,還可在遵循歷史發展邏輯的基礎上進行合理化的延伸和有節制地想象虛構,運用多種藝術手段,將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轉換為形象生動的文學敘述。在《清史稿·陳廷敬傳》中只用寥寥數字記載了陳廷敬的仕途生涯以及功過是非,小說卻詳盡敘述了陳廷敬科考及第的過程。在小說開篇就介紹了陳廷敬因無辜卷入科舉賄賂所引發的幾樁命案而被推至風口浪尖處,險些仕途不保甚至喪命,可謂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此外,小說有意避開讀者所熟知的康熙王朝大事件,刻意選取了與陳廷敬有關的小事件來建構起他三起三落的一生,并在尊重基本史實的前提下,作者發揮想象的空間串聯了許多可讀性強的小故事,如擔任欽差大臣前往山西陽曲縣調查百姓自愿捐龍亭事件、整頓山東糧食上報的浮夸之亂、不惜違逆圣意揭穿云南巡撫王繼文虧空庫銀的真實面目等。臣子與皇帝之間復雜微妙關系的處理也值得一提,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因各自立場和話語權的不同,君臣關系絕非表面和氣地“你諫我納”這么簡單。小說對于君臣關系中緊張的心理拉鋸戰描寫十分真實細膩,這是讀者在史書上所不能直接窺見的。
二、敘事語言與故事情節的戲劇化傾向
劇本是影視藝術、戲劇創作的腳本,它常以代言體的方式展開故事情節,依靠人物對白和動作展現出來的畫面來講述故事。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消費文化和影視文化的影響,小說敘事開始借鑒視覺文化的表現方式,敘事語言追求視覺造型性,小說文本呈現出明顯的劇本化傾向。眾多現當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編為影視劇,例如,余華的《活著》、梁曉聲的《雪城》、蘇童的《妻妾成群》等。長篇歷史小說《大清相國》著重記敘了陳廷敬從科考至乞骸骨過程中的幾個重要案例,以講故事的形式進行事件拼接,故事之間的銜接又環環相扣,小說敘事呈現出戲劇化傾向,具體表現在人物塑造、敘事語言、情節轉場等方面。
首先是情節結構的設置。小說《大清相國》以陳廷敬遭遇科舉風波開篇,以衣錦還鄉、老死相位的結局收尾,主要講述了陳廷敬從政過程中經歷的五大事件,即山東百姓自愿捐糧案、山西陽曲自愿捐建龍亭案、太原寶泉局銅料虧空案、云南巡撫虧空庫銀案以及康熙皇帝南巡期間由陳廷敬精心謀劃的彈劾案。小說主要以講故事的形式來推進整體情節的發展,而情節又由許多視覺性明顯的小場面連綴而成。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雖采取邪惡分明的二元對立模式進行敘事,但人物形象依舊鮮明、活靈活現。主人公陳廷敬自覺秉持官員的良知與道義,是大忠大善的代表,作為對立面存在的官員群像也栩栩如生、丑態各異:見風使舵、八面玲瓏的高士其;道貌岸然、攬權自重的明珠;專橫跋扈、結黨營私的索爾圖……儼然一幅官場百態圖。出現在陳廷敬生命中的三個女人也各有千秋:原配夫人淑嫻賢德善良、二夫人月媛知書達禮、三夫人珍兒豪放不羈。遺憾的是,劇本化的小說敘事讓人物塑造的細節描寫缺失,它主要通過人物的神態、動作、語言來展現鏡頭感和畫面感,人物的心理描寫不夠細膩。最后是敘事語言追求視覺造型性,即通過語言來營造畫面視覺效果。劇本化的敘事語言,既不追求荒誕派般晦澀難懂的語言形式技巧,又不追求抒情式語言的意境美和詩意美。它更多的是說明性的文字,可以通過外形表現出來,成為視覺藝術。但敘事語言的戲劇化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學性。
三、歷史與現實雙重鏡像下的“完人”形象
大清相國陳廷敬清而不酷、好而不庸、能而不專、德而不柔。伴君五十余載,為官楷模、人臣范本、為人典范,老死相位,極盡榮耀。不同于王躍文現代官場小說系列中塑造的“不完美”主人公形象,如《國畫》中的朱懷鏡、《西州月》中的關隱達以及《蒼黃》中的李濟運等,陳廷敬這一人物形象,可以稱得上是“完人”,引康熙皇帝之評價:“寬大老成,幾近完人!”[1]474這既表達了作家對名臣賢相的景仰和敬佩之情,又開拓了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好官理念。可從兩方面去分析這一“完人”形象。一方面是近乎完美的外部條件,首先,陳廷敬出身于家境優渥的晉商之家,父慈妻賢,為官毫無后顧之憂,有別于以往窮書生寄托于科舉考試來改變人生命運的敘事圈套。其次,陳廷敬被標榜為科舉神童,學識淵博且才華出眾,這使他總能在充滿坎坷與未知的仕途際遇中化險為夷,且每逢生死攸關的緊急關頭,總有貴人相助,具有戲劇色彩。此外,是兩代皇上對他的知遇之恩,能得到擁有最高話語權的君王的垂青,無疑是他仕途最強有力的后盾。
另一方面是陳廷敬自身的修養和作為,其為官做人之道幾乎無可挑剔,達到了人品與官品的雙贏,這是“完人”形象在讀者心中之所以熠熠發光的關鍵所在。為友,他心地善良、樂于助人。他暗中拿走好友張汧所備硯臺里夾帶的《經藝五美》,幫其躲過科考舞弊一劫;主動為清貧如洗的書生李謹慷慨解囊,支付他在客棧的食宿費用;為素不相識的朱啟、珍兒等人打抱不平,排憂解難。為子,他孝敬父母,眷顧親友。雖遠在京城政務繁忙,但他時常感念親人,為母親抄佛經以祐平安;母親去世后,為老人披麻戴孝,守制三年,以彌補人子之孝;多次不厭其煩地嚴詞勸導初入官場的弟弟陳廷統不可急功近利,提防被居心叵測之人利用。為臣,他不朋不黨,清正廉潔。他始終以國事為重,冷眼旁觀明珠和索額圖兩黨的勾心斗角,不屑于依附其中任何一黨;不懼被他人牽連受累,義無反顧地向朝廷薦舉清廉愛民之士,“只要他們真是清官好官,連累了我又何妨?”[1]390臨危受命督理錢法,他當眾發誓不受毫厘之私,并親自盤點庫銀,打擊奸商、徹查貪污、理順錢法。為人,他精明能干,改革時弊。陳廷敬三次擔任欽差大臣整治地方浮夸之亂,分別揭發了山西百姓自愿捐龍亭事件、山東糧食上報作假事件以及云南巡撫王繼文私自虧空庫銀事件;他在其位謀其職,反對科場舞弊之亂、整治奢靡鋪張之亂以及扭轉貨幣投機之亂。治世思良才,透過這樣一位歷史先賢的厚重人生,讀者可穿越歷史長河近距離感受到一位飽學之士的清風亮節和能臣干吏的智慧練達,這正是作者塑造歷史“完人”的現實意義所在。
四、為官五字訣在當代的教科書式意義
小說主角陳廷敬以卓越學識和赤膽忠心在爾虞我詐、刀光劍影的官場里脫穎而出,深得封建君王的賞識和青睞,歷任工、吏、戶、刑四部尚書,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的宦海生涯雖波折起伏,甚至多次在腥風血雨地官場斗爭中命懸一線,卻仍得善終功成身退,這與其身處官場所遵從的“忍、等、穩、狠、隱”為官五字訣有著密切的聯系。“等”,是恩師衛向書告老還鄉時對陳廷敬的叮囑,不可急功近利,宦海無涯更須厚積薄發,等待有利政治時機的到來;“忍”,是岳父李祖望老先生對陳廷敬的教導,小不忍則亂大謀,應以大局為重,不可好大喜功、鋒芒畢露;“穩”,是陳廷敬為官多年自己參悟的保身之道和處世哲學,不依附索額圖或者明珠的任何一方派系,不參與朋黨之爭,拒絕拉幫結派,這是他縱橫官場而始終屹立不倒的為官秘訣;“狠”,是指面對貪官污吏肆意妄為時不可有婦人之仁,該耍手段的時候決不能心慈手軟,小說結尾由陳廷敬幕后精心策劃的連環參劾案讓眾多別有用心之人敗下陣來,不禁讓人拍手稱快;“隱”,是陳廷敬的夫人月媛點醒他的一個字,權位過重最終會招致災禍,人到暮年,適時隱退才是明智之舉。
天理昭昭,大道不變。這看似簡單的五個字不僅成就了一代名相陳廷敬,對新時代公職人員為人處世也具有教科書式的現實指導意義,正如王躍文在接受訪談時所說:“無論處于哪個時代,對公職人員來說,道德上的要求都是必要的,法治社會更是如此。”[2]
五、結語
歷史敘事對人物的闡釋不可避免會傾注敘事者的情感評價,完美人設陳廷敬作為古代好官文化的踐行者,寄托了作家王躍文重塑官場價值、弘揚官場正能量的理想主義情懷。為官五字訣則是主人公在特定歷史環境奉行的生存策略,于當代社會具有正面的借鑒意義,但它未能觸及和改變異化人性的官場制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又是人性妥協的無奈之舉。由此可見,畸形的官場制度和官場亞文化自古有之,如何對其進行根本性變革以改善官場環境,或許這才是《大清相國》向當代社會提出的更為深刻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