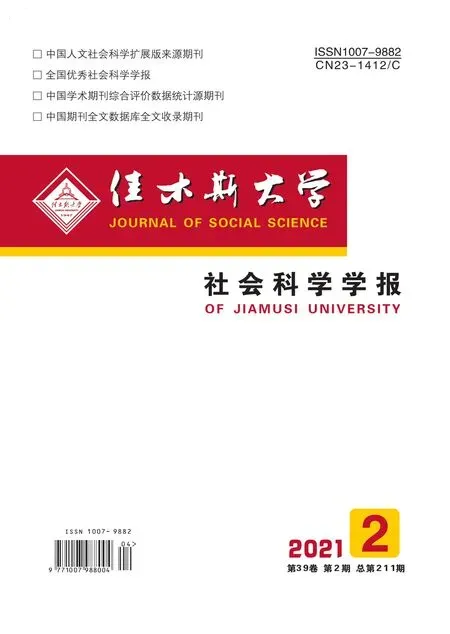解讀拉赫娜·里茹托《影孩》中的“影”之意象*
周漪颯
(浙江大學 外語學院,浙江 杭州310058)
一、 引言
拉赫娜·玲子·里茹托(Rahna Reiko Rizzuto)為當代美國著名的日裔作家,以書寫二戰后普通的日裔美籍人的生活狀況著名。她的筆鋒尤其聚焦于其中的弱勢群體——流民中的女性,以描寫她們的生存境況,作品中充滿了對女性力量的肯定及對未來的向往。這些流亡的女性不僅要經受戰爭帶來的身與心的雙重苦難,面臨種族歧視,更甚至可能受到來自本族人內部的排斥及家庭的拋棄。《她為何離開我們》(Why She Left Us)在2000年取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后,《影孩》(Shadow Child)更使她一舉成名,并成了她最負盛名的作品。故事敘述了自幼被美國養父母收養的棄嬰莉蓮,在沖動驅使的婚姻中被送入集中營,最后在遭受廣島之痛后回到美國,并獨身在夏威夷島生活的經歷。以及她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性格迥異的花子和景子在遭受了青春期的決裂后,是如何收獲和解、走向團聚的。
“影子”在文學中是一常用意象。一般認為,其多數情況下與消極情緒或“鬼怪”“幽靈”這種屬于神秘領域的關鍵詞聯系起來。例如在福克納的名作《喧囂與騷動》中,影的意象使故事往寂靜而沉默的方向發展,最終靜止在悲劇中[2]34-35。但像《影孩》這類由影之意象貫穿全書的作品卻并不多見,很少有作品能僅利用單一的意象將故事的內涵表達到如此極致。除了賦予了影之意象常用的消極內涵以外,里茹托也創新性地將影的內涵轉換成絢麗而積極的“守護者”的形象。此外,里茹托擅長敘寫內心深處的活動,她的字里行間充滿了散文般的抒情,這種筆觸也使一種淡淡的哀傷像影子一般游動在全書之間。
二、“影”的三重隱喻
雖然小說全文處處滲透著影子的意象,但標題《影孩》卻依舊存在理解空間。里茹托一般被認為是一位擅長描寫女性的作家,本小說的情節故事也基本只涉及女性,那作者為何不將小說直接命名為“影之少女”(Shadow Girl)或“被陰影纏身的女性”(Shadow Woman)呢?本文傾向認為,《影孩》中提出的問題是人類的共性問題,并沒有性別之分。
(一)“破壞之影”
影子首先象征著黑暗,與死亡、絕望及壓倒性的力量緊密相連。小說中提到的最直接的破壞力無疑來自于戰爭。流落于戰爭中的莉蓮時時遭受著死亡的威脅,可她本人卻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廣島化作焦土,唯一的好朋友死在她面前時,莉蓮才初次感受到深刻的痛苦和絕望,她才明白生活中的坎坷比起死亡根本不值一提。書中描寫莉蓮的部分基調陰郁。在她搭乘火車回到廣島時,所遇見的“亡靈隊列”(實則為原子彈落下后逃離廣島的人們)成了她永遠的噩夢:“有一團奇怪的熾芒燃燒在亡靈身后,這些亡靈好像完全籠罩在陰影之中……莉蓮看見了他們的皮膚,那是漆黑的。有些皮膚被燒掉了,外露著森森的白骨。有些皮膚則好像掛在他們的身體上”[1]201。這些逃生者的背后是漆黑的、已變成人間地獄的廣島;籠罩著亡靈的“陰影”就是死神的黑袍。其次,自然力量對人類及環境的破壞也不容小覷。在景子初次跟隨繼父去觀賞火山噴發時,她被自然力量的破壞力震懾,也領悟到某種力量是懂得厚積薄發的陰影才擁有的:“當他說到誕生這個詞時,你又退縮了,但周圍的空氣里的確彌漫著新生的氣息。有什么東西是真實存在著的,它正在轉化成別的形態:這是一種永恒不變的、黑暗又質樸的力量”[1]124。最后,漆黑的影子又代表了一種野蠻的欺凌。在埃迪等人故意將患有幽閉恐懼癥的花子引入巖洞時,他們還一邊拿著手電筒在黑暗的巖壁中制造陰影取樂。這時那些不斷浮動的陰影暗示了花子和景子即將遭受的傷害以及埃迪等人對這場探險的絕對控制權。
(二)“創傷之影”
過去的創傷化為一個人的影子或夢魘是本文中影之意象最明顯的內涵。從其詞源學來說,創傷(Trauma)本意是指外部力量給人的身體造成的物理性損傷。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創傷研究開始,基于社會歷史及現實的需要,創傷理論就一直在不斷豐富和發展。1995年,凱西·卡魯斯給予了創傷最為權威的定義:“對于突如其來的、災難性事件的一種無法回避的經歷,其中對于這一事件的反應往往是延宕的、無法控制的,并且通過幻覺或其它侵入的方式反復出現”[3]135。
由此可見,創傷帶來的后遺癥是無法逃避的,對于創傷受害者而言,創傷就像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影子。小說首先以姐姐花子為主視角開始了略顯凌亂的敘述。花子性格單純且有藝術天賦,但她的幽閉恐懼癥被人利用而遭到霸凌,全身留下丑陋的疤痕。這對一個年輕的女孩來說是一段噩夢般的記憶。她無法擺脫這些傷疤,更無法從過去的創傷中走出來。為了逃避“黑影”,她離開家鄉夏威夷,隱居在紐約一個洞穴似的出租房內,每天生活在昏暗的光線中,成了一個與社會脫節的人,并在時不時發作的夢魘中自暴自棄。布滿陰影的地方充滿了混沌與不可預料的危險,映射了花子一團糟的生活狀態和心境。同時,花子無法控制自己不去嫉恨羨慕著陽光開朗的妹妹景子,一邊覺得自己是“景的影子”[1]12,一邊又堅持認為景子是傷害自己的元兇,殊不知自己片面的回憶、對創傷和尋求真相的逃避態度才是這種劣等感的根源。在花子的自述部分,大量意識流獨白的涌入將時空及虛實界限模糊,為閱讀帶來了困難,也使讀者徘徊在花子的心境迷宮內。
經歷過廣島之痛的莉蓮則一生都在與過去的創傷陰影做糾纏。少女時期時的沖動婚姻將她拉入了無法挽回的深淵,又在經歷廣島之痛后費盡心思回到美國。雙胞胎這樣回憶她們的母親:“她(莉蓮),跪坐在……土溝邊,看起來是那般渺小,將要沉沒到無聲的大地中去了,幾乎都要與它融為一體,先是肩膀、再是頭。……她只剩一點身體露在地上了,鬼鬼祟祟的黑暗躡手躡腳地抱住了她,在某個瞬間,她被帶走了”[1]48-49。在這樣的一副文字畫面內,月下獨耕的母親自成了一副孤獨的景色,而與之對應的是躲在窗邊偷看母親的雙胞胎。這其中的距離暗示了兩代人之間的差異和隔閡,更象征了母親心中始終有塊不可揭露的傷痛領域是最親的親人也不能夠觸及的。
作者通過描寫花子和莉蓮的創傷之影,呈現了分別屬于兩代人的不同問題。這也是里茹托對人類遭遇及境況思考深邃的一種表現。莉蓮顛沛于戰爭中,從未被當作一個人看待。前夫唐納德將其視作所有物,在覺得她累贅后果斷拋棄了她。她在日本時因為美籍背景而被日本人排斥,而回到美國后她的身份卻是“日本來的流民”。因為兩個國家都不認可她,她只得在兩塊大陸中間那個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島生存下來。莉蓮在戰爭期間更名為美夜,后者只是她所依附的美國大兵隨口喊出的名字。在連一個生存問題都無法保障的環境中,尊嚴更顯得微不足道。而在生存問題得到解決后,作為下一代的花子并不能擺脫母親的創傷,就如暢銷書作家漢娜·廷蒂(Hannah Tinti)說的,這本書顯示了“創傷是如何遺傳”②的。母親的遭遇通過她在昏迷時的夢話傳遞給她的孩子們,使花子從小就無法樹立對回憶的正確態度,她通常都將小時候的可怕涂鴉鎖在箱子里。通過塑造兩位人物的創傷之影,作者實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類該如何處理創傷、正視回憶?接下來,本文將對該問題進行討論。
(三)“守護之影”
除了如影隨形的創傷以外,還有背后的守護。這一說法和日常生活中所說的“背后靈”有些類似。小說中的雙胞胎妹妹景子個性外向勇敢,一直在暗中保護姐姐和母親。因為不懂日語的兩姐妹在小時候一次對名字的誤讀,景子接受了“為影”③的命運,并下定決心要變得像火山女神佩蕾一樣堅毅勇敢,以保護自己的親人:“……它(影子)瞬息萬變,蘊藏無限可能。……絕不會受任何約束。它絕不總停駐于某處,更不會遭受堵塞。它永不孤獨……”[1]151-152。上文已提到,母親的創傷對孩子的“遺傳”尤為明顯,但在創傷被下一代繼承的同時,景子也繼承了母親那些啟發性的故事,并從中獲得從不逃避的勇氣和品質:“如果她能靜靜地站著,看著它的眼睛,一切就安然無恙”[1]122。為了替被歧視的母親出氣,景子想法設法反擊那些嘲笑母親的男孩,而不愿自己在學校做的事被母親和姐姐發現。作者對景子的塑造也安排在人物的愛好中,景子因向往自然的力量,渴望自由,而愛好游泳。水和影子一樣具有流動性。通過與水融為一體,她能夠化柔為剛、化險為夷。
景子是小說中擔負著“拯救職責”的人物,是身為“守護之影”的具體人物,但她也沒能守護住被困在巖洞內遭受霸凌的花子。作者意在指出,治愈創傷除了背后守護的具體行動以外,還需要其他的方法。當在景子初到紐約時遭襲、花子與景子間原本“被守護者”和“守護者”的身份得到迫不得已的轉換時,作者才開始鋪成自己對治愈過去創傷的看法。里茹托安排花子——一個背負著不堪回首的過去、擁有人格缺陷的被動者,去擔任主動的施救者角色,以表明生命中美好的過去及人際間的羈絆能帶給人多么強大的力量,能化作自我守護及抵御傷痛的鎧甲,而在日常生活中卻如影子一般潛藏著令人難以發覺。“創傷不能獨自面對,只有‘在關系中’才有康復的可能。創傷的復原首先應以恢復幸存者的權利和建立新關系為基礎”[4]136。面對病床上的景子,花子開始去建立新的人際關系,她試圖與醫生交流,同時事無具細地回憶起她們純真的童年,并向往著兩人能回到兒時那種心靈相通、以及與母親相親的狀態,由此開始重視起自己的妹妹及其他親人。最后決定直面自己最不堪回首的過去,并擱置誤會找出傷害景子的兇手。文中有一處細節是這樣描寫的:在母親因核輻射影響而昏睡時,雙胞胎就會嘗試著把夢魘中的母親所描述的鬼怪畫下來以達到“鎮邪”的目的,并用自己的方法將“被亡靈拽去另一個世界”[1]208的母親拽回現實世界。透過此處描寫,作者意在表明,當創傷和過去遺留的問題超出個人的解決能力時,也應該走出封閉的內心世界,去尋求外界的團結和幫助。
同時,里茹托并未著重將莉蓮所遭受的創傷經歷上升到二戰時期的日裔美籍人的整體層面。雖然作者描寫了曼扎納集中營中日裔美籍人的生活狀況、轉運日本人的輪船等等,但她依舊將重心放在莉蓮這個個體身上。從莉蓮被唐納德的家庭排斥與輕蔑開始,在美國長大的莉蓮就從未在日本人身上尋找過認同;而在經歷了廣島之痛以后,一直堅信自己是美國人的莉蓮也不再去爭取自身作為美國公民的權利。莉蓮意識到,她的傷痛和悲劇并非是由立場或選擇帶來的。莉蓮是創傷的隱忍者,同時也是反抗者。在毀滅性的打擊面前,過于渺小的她只能接受既定事實并盡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于是,依靠著對夏威夷島的向往以及對腹中一對雙胞胎的愛和責任,莉蓮用盡辦法前往了夏威夷。作者似乎意在表明,人應給予自身價值足夠的認可。在面對創傷時,自我的精神力量也非常重要。
三、結語
《影孩》的靈感來源于里茹托朋友遭受性侵害的親身經歷,這件事為她的創作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里茹托說:“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女人,一個人類,我一直在思考寫作如何能幫助我們治愈這個問題(創傷)。”④《影孩》顯然是她為解決該問題而做出的嘗試。綜上所述,通過從“破壞力”“創傷”及“守護”這三個層面賦予“影子”意象不同的內涵,我們會發現里茹托在文本中所編織的對“過去”及“創傷”的思考。一方面,人們應當正視回憶;另一方面,應給予自身個人價值足夠的重視,積極尋找生活的意義。在個體創傷無法得到解決時去積極尋求外界的聯系與幫助。
[注釋]
①該小說在國內已引進但尚未出版,所用引文皆為筆者自行翻譯。
②漢娜·廷蒂(Hannah Tinti)為知名暢銷書《好小偷》(The Good Theif)及《塞繆爾·霍利的十二種生活》(The Twelve Lives of Samuel Hawley)的作者。該評論見里茹托主頁:https://rahnareikorizzuto.com/shadowchild/。
③“景”(Kei),在日語中本就是“影子”的意思。這是從未受過日語教育的兩姐妹對“Kei”這個名字的誤讀,其實“Kei”讀音下還能表示其他很多漢字。
④見拉赫娜·玲子·里祖托在2018年7月15日發表于其主頁的博客文。https://rahnareikorizzuto.com/2018/07/fiction-and-the-chaos-of-tra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