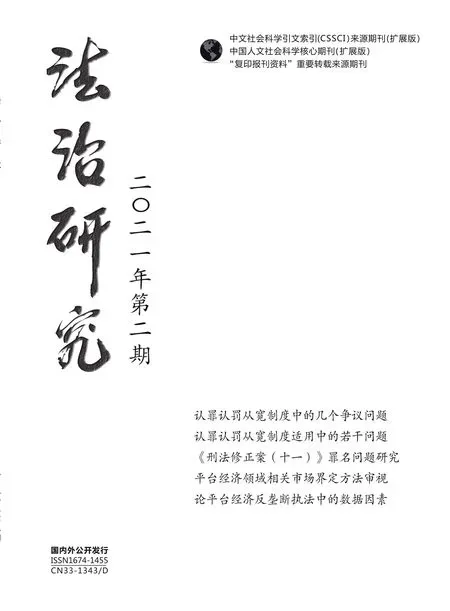數字市場初創企業并購的競爭隱憂與應對方略
方 翔
近年來,全球主要數字平臺掀起了一股針對初創企業(start-ups)和新生企業(nascent firms)的并購浪潮,引發各國反壟斷執法機構的競爭關注。傳統理論認為,對尚不具有一定市場規模的企業進行的并購,①我國《反壟斷法》關于企業合并、并購的控制制度,使用的是“經營者集中控制”的概念,其包括合并、通過取得股權或者資產的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通過合同等方式取得對其他經營者的控制權或者能夠對其他經營者施加決定性影響三類情形。為了論述的簡潔,本文統一采用“并購控制”的概念,如無特殊說明,其與反壟斷法中的“經營者集中控制”同義。并不會產生顯著的競爭損害和市場結構的變化,反壟斷法無需對此干預和控制。相反,此種并購可以促使更擅長運用技術的大企業獲得創新技術,從而實現協同效應和專業化,提高創新和社會整體福利。②See Eric Rasmusen, Entry for buyout, 36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81(1988).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本身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數字平臺持續并購創新型初創企業,并演化為一種旨在消除潛在競爭和創新,鞏固和維持數字平臺市場支配地位的策略手段時,反壟斷法應當及時予以規制。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2021 年2 月7 日印發的《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 (以下簡稱《平臺反壟斷指南》)中,傳遞出對數字市場初創企業并購問題的高度關注,其第19 條明確提出,當“參與集中的一方經營者為初創企業或者新興平臺”,即便未達到申報標準但其有可能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反壟斷執法機構仍可以主動調查。但在反壟斷法的制度框架下,如何識別并有效規制具有反競爭效應的初創企業并購,相關理論研究的步伐需要快步跟上,從而更好地指導反壟斷執法實踐。
一、全球數字市場初創企業并購的發展態勢
在全球數字經濟市場,數字平臺的并購活動一直處于活躍狀態。某種意義而言,并購已經成為數字平臺的發展戰略。以臉書為例,其在2004 年剛剛推出時,月活躍用戶數為100 萬人,2005 年只有7%的美國成年人參與該社交網絡,而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這個數字上升至65%。③Andrew Perrin, Social Networking usage: 2005-2015, Pew Research Center(Oct.8, 2015),http://www.pewinternet.org/2015/10/08/2015/Social-Networking-usage-2005-2015/.自2007 年開始,臉書對社交媒體市場的潛在競爭對手和鄰近市場的企業發起了一系列并購,這無疑推動了臉書的快速成長與發展。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曾在2019 年5 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僅在過去的六個月里,蘋果收購了約20 至25家公司,平均每兩到三周就收購一家公司。由于被收購公司規模很小,蘋果通常不會公布這些交易,其收購目的主要在于整合目標公司的人才和知識產權。④Lauren Feiner, Apple Buys a Company Every Few Weeks, says CEO Tim Cook, CNBC(May 6, 2019),https://www.cnbc.com/2019/05/06/apple-buys-a-company-every-few-weeks-says-ceo-tim-cook.html.同樣,谷歌在2001 年至2018 年間,平均每個月就會收購約一家公司。⑤Marc Bourreau & Alexandre de Streel, Digital Conglomerates and EU Competition Policy, SSRN (March 11, 2019), https://ssrn.com/abstract=3350512.根據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壟斷分會2020 年10 月對谷歌、亞馬遜、臉書和蘋果(以下簡稱GAFA)的最新調查數據⑥U.S.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顯示,亞馬遜在1998 年至2020 年期間共實施了104 起收購,平均每年約4.5 起;蘋果公司在1998 年至2020 年期間共實施了120 起收購,平均每年約5.2 起;臉書在2007 年至2020 年期間共實施了86 起收購,平均每年約6.1 起;谷歌在2001 年至2020 年期間共實施了256 起收購,平均每年約12.8 起。從被收購企業的領域來看,亞馬遜、臉書和谷歌均收購了針對移動設備優化服務的公司,從而推動平臺向移動服務領域的拓展。同時,還注重對具有先進數據分析技術(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企業的收購,可以預期這些合并有助于提高平臺的計算效率和預測能力。
相應地,國內數字平臺也在2015 年前后進入到并購的白熱化階段。阿里巴巴在電商新零售、媒體娛樂、物流、生活服務及健康等五大領域推進一系列投資并購,其通過多輪投資的手段,實現了對高德、銀泰、優酷土豆、UC Web、餓了么等企業的全資收購與私有化。⑦陶娟:《收割者:騰訊阿里的20 萬億生態圈》,載新財富網2020 年11 月13 日,http://www.xcf.cn/article/5f929c8a254b11ebbf3c d4c9efcfdeca.html。騰訊則聚焦于娛樂、媒體領域的投資并購,目前已成為美團、京東、蔚來、58 同城、虎牙直播等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此后,兩大數字平臺及其“代理人”在更多垂直領域和細分市場展開并購,旨在將分裂的小眾市場整合到平臺的生態系統之中。
值得關注的是,初創企業正成為數字平臺投資、并購的主要目標。根據《經濟學人》的報道,谷歌、亞馬遜、蘋果、臉書和微軟僅在2017 年一年,共花費316 億美元用于收購初創企業。⑧The Economist, American Tech Giants are Making Life Tough for Startups, (June 2,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8/06/02/american-tech-giants-are-making-life-tough-for-startups.Lear 的統計數據顯示,谷歌、亞馬遜和臉書在2008 年至2018 年期間收購的目標企業,其成立時間集中在2.5 年到6.5 年不等。⑨Lear, Ex-post Assessment of Merger Control Decisions in Digital Markets, (June 2019),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ssessment-of-merger-control-decisions-indigital-markets.盡管國內沒有具體統計數據,但從另一組關于對“獨角獸”企業的投資情況可以看出,年輕的創新型公司一直受到數字平臺投資的青睞。阿里與騰訊對“獨角獸”及資本市場的占有率甚至遠超美國平臺企業。⑩同前注⑦。更為令人擔憂的是,相當程度的初創企業在并購結束后迅速被終止。在臉書發起的并購中,部分并購將獨立的應用程序和網站轉化為臉書獨有的功能,而其他產品在并購后的幾天或幾個月內就被關閉了。?Mark Glick & Catherine Ruetschlin, Big Tech Acquisitions and the Potential Competition Doctrine:The Case of Facebook, Working Paper No. 104(October 2019), https://doi.org/10.36687/inetwp104.有研究統計了GAFA 和微軟在2015 年至2017 年之間的175 起并購發現,目標企業的品牌在收購后的一年內即被終止的共有105 起。?Axel Gautier & Joe Lamesch, Merger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8056,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529012.這一方面可能意味著被收購企業的人才、技術、產品等得到了很好的整合,但這些并購同時也可能會引發潛在的反競爭問題,即通過并購獲得補充服務,可能會幫助數字平臺企業鞏固其在市場中的支配地位,加之不斷增加的包含個人信息的大數據收集以及廣泛的網絡影響,數字平臺企業可能使新進入者難以開發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并為競爭對手進入市場制造難以逾越的障礙。?See Elena Argentesi et al., Tech-over: Mergers and Merger Policy in Digital Markets, voxeu (March 4, 2020), https://voxeu.org/article/mergers-and-merger-policy-digital-markets.
二、初創企業并購的競爭隱憂
(一)數字平臺并購初創企業的動因詮釋
并購是企業實現自我發展的重要戰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在短期內擴大生產經營規模,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競爭優勢。經濟學關于企業并購動因的研究趨近成熟,一般而言,依據并購的類型可將其動因劃分為三個基本類別:橫向并購主要受規模經濟效益的驅動,縱向并購源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因驅動,而混合并購的動因則建立在范圍經濟和風險分散理論的基礎之上。?參見崔保軍:《企業并購動機綜述》,載《企業經濟》2004 年第8 期。進入到平臺經濟領域,商業模式和盈利方式的創新,促使企業并購的動因更加復雜化和多元化,一項并購活動可能受到多種動機的混合驅動,從而超出傳統的理論分類范疇。數字平臺針對初創企業的并購動機可主要歸結為以下三種。
第一,獲取初創企業資產。通過并購來獲取初創企業資產,是數字平臺的常見做法。例如,臉書和谷歌一直在以快速的步伐收購初創企業,很多情況下,其收購的主要動機是為了雇用初創企業的軟件工程師或其他高質量員工,通過并購來滿足其對技術人才的強烈需求,并逐步形成所謂的“購-聘”(acqui-hires)策略,?See John F. Coyle & Gregg D. Polsky, Acqui-hiring, 63 Duke Law Journal 281 (2013).這比單獨招聘員工更有效率。除此以外,目標企業的技術、專利、用戶、數據和信息等,也是數字平臺期待通過并購以獲得的寶貴資產。
第二,拓展平臺業務領域。數字平臺通過并購初創企業可以開拓新市場,實現業務的多元化,該動機可視為平臺企業的一種進入策略,并成為平臺實施戰略擴張的重要手段。例如,谷歌曾為建立移動業務并適應移動計算的新興趨勢,在2005 年以5000 萬美元的估價收購安卓。盡管當時的安卓只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初創企業,并不能為谷歌帶來直接收入,但其為谷歌提供了滲透移動市場所需的技術能力。2007 年,谷歌正式推出安卓這一智能手機設備開源移動操作平臺,迅速占領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市場,安卓手機上展示的移動廣告收入也成為谷歌的重要盈利來源。?參見[美]喬治·蓋斯:《重新定義并購:谷歌是如何兼收并購的》,閭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8-121 頁。再如,阿里巴巴通過收購高德地圖,使其O2O 業務得到重點發展,二者的合作從移動互聯網位置服務及生活服務延伸至數據建設、產品開發等多個領域,實現線上線下資源的有效整合。?參見樂婷:《互聯網企業并購動因與戰略研究——基于阿里巴巴并購行為》,載《綠色財會》2015 年第10 期。
第三,消除潛在的競爭和創新。這是數字平臺的一種防御性動機,旨在以先發制人的并購手段,消除潛在競爭對手(potential competitors)或新生競爭者(nascent competitor)在未來競爭中的威脅,從而防止其市場地位及壟斷利潤遭受蠶食。?See Amy C. Madl, Killing Innovation?: Antitrust Implications of Killer Acquisitions, 38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Online Bulletin 28(2020).事實上,肯尼斯·阿羅在其著名的“替代效應”(replacement effect)理論中早已指出,在位企業依靠過去的發明獲得壟斷利潤,它們的動力是保護現有的壟斷利潤,因此其研發創新的動力遠不及競爭市場中的其他企業。?See Kenneth J. 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Invention, in Universities- 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 Committee o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609-626.而在實踐中,壟斷者不僅自己不愿意創新,還要借助并購的方式消弭競爭對手的創新威脅。據美國GAFA 調查報告披露,臉書的內部文件證實了其通過收購具有競爭威脅的公司,以保護和擴大臉書在社交網絡市場的支配地位的做法,臉書的高管將這一并購戰略描述為“鞏固市場地位的爭奪戰”。2012 年,扎克伯格在和臉書前首席財務官的信中稱,收購Instagram 等新生競爭對手的目的是消除競爭威脅并維持臉書的地位。調查顯示,當臉書收購WhatsApp 時,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及數據專家將WhatsApp 視為對臉書自有產品Messenger 的潛在威脅,并提供了進一步鞏固臉書統治地位的機會。臉書通過關鍵性收購來增加其社交網絡的使用率并擴大其在市場中的影響力。最后,臉書的連續收購反映了該公司對有潛力在完全成長為強大的競爭威脅之前將其收購。?同前注⑥。臉書的內部文件表明,一旦發現競爭威脅,便試圖通過克隆其產品功能、收購目標企業,或將其從臉書的社交圖譜中排除來壓制它們。臉書采取了這些措施來扼制競爭對手以使其免受競爭,而不僅僅是發展或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通過剖析數字平臺并購初創企業的動因機理,不難發現其中既包含提高效率和促進發展的意圖,同時也暗藏反競爭性的行為動機。特別是旨在消除潛在競爭與創新的并購動機,應當引起反壟斷執法機構的高度警覺。2018 年,來自倫敦商學院和耶魯大學的三位學者柯林·坎寧安(Colleen Cunningham)等首次提出了“扼殺型并購”(killer acquisitions)的概念,主要指市場中的主導企業為了終止目標企業創新項目的開發并搶占未來競爭優勢而進行的并購活動。21根據坎寧安等人的研究發現,美國4000 多家公司在過去25 年里發起的16000 多個藥物開發項目,約有5.3%至7.4%的項目(相當于每年約46 至63 起)遭到“扼殺型并購”。特別是存在以下三種情況時,被收購項目極可能會被終止:一是被收購的項目與收購方現有產品組合中的產品重疊;二是收購方不存在重大競爭約束;三是收購方的重疊產品在一段時間內仍受到專利保護。研究表明,假如消除扼殺型并購對新藥開發的不利影響,制藥行業的藥物研發速度會提高4%以上。但遺憾的是,由于目標企業多為小型初創企業,尚未達到反壟斷并購審查的申報標準,因此這些并購活動從未經過反壟斷執法機構的競爭評估。該研究結論迅速引發反壟斷學界和實務部門的高度關注,這一討論也從醫藥領域轉移到數字市場,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數字平臺對初創企業的并購,特別是上述第三種動機的并購,是否構成扼殺型并購。
基于數字經濟和平臺商業模式的特殊性,筆者認為,數字市場的扼殺型并購與醫藥領域的扼殺型并購存在一定區別。根據坎寧安等人的研究,醫藥領域的扼殺型并購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扼殺”行為通常表現為終止或關閉目標公司創新項目的開發;其二,收購者與目標企業存在產品或研發重疊(overlap)是產生扼殺動機的必要條件,并且重疊越多,發生扼殺型并購的可能性越高。但在數字市場,由于數字平臺具有用戶規模經濟和邊際收益遞增的特點,大規模的用戶可以產生較高的交叉網絡外部性,22只要平臺企業擁有一定數量的用戶基礎,即使其與收購者不存在任何產品(服務)重疊,仍可能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對手。正因如此,數字市場的動態性導致平臺的競爭是為了市場,而不是在市場上中競爭。23對于已形成數字生態系統的大型數字平臺而言,其更樂意將目標產品或服務整合到生態系統中,而不完全是終止或關閉。基于此,只要數字平臺出于消除潛在競爭和創新的動機所發起的并購,無論目標產品和服務是否被終止或是束之高閣,我們都有必要將其視為“扼殺型并購”予以審慎對待。這一觀點也符合近期美國對臉書收購Instagram 和WhatsApp 案調查的基本立場,Instagram 和WhatsApp 在被收購后并未終止運營,但并不妨礙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定其構成扼殺型并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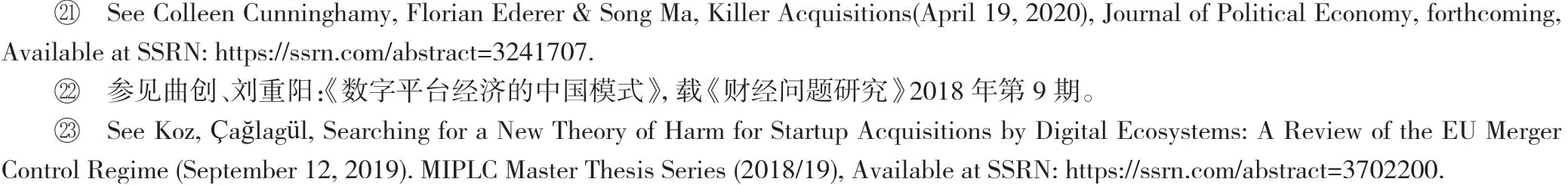
(二)初創企業并購的反競爭效應解析
初創企業在促進創業和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大型數字平臺并購初創企業并不必然具有反競爭性,也可能實現優勢互補的共贏局面。譬如,平臺可為初創企業的創新研發及其商業化提供資源支撐,被大型數字平臺收購亦可成為初創企業的創新激勵和市場退出戰略。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持續性的并購,特別是基于扼殺動機的并購可能會引發競爭隱憂。從現有的數據來看,全球范圍內的大型數字平臺對創新型初創企業的并購幾乎沒有受到過審查,現行反壟斷法采取的這種有限干預政策極有可能產生“假陰性”錯誤,24這使得本身就具有寡頭壟斷趨勢的大型數字平臺進一步鞏固其市場支配地位。從長遠來看,這種并購除了會直接扼殺初創企業的潛在競爭,還可能造成以下不利影響。
1.強化數字平臺的市場支配地位
數字平臺本身即具有高度集中的趨勢,這與平臺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等綜合特征密切關聯。由于網絡外部性的存在,平臺競爭具有馬太效應,率先形成規模的大平臺將獲得整個市場,并進入贏者通吃的階段。25盡管初創企業的市場份額微乎其微,被收購后并不會顯著增加數字平臺的市場集中度,但基于平臺經濟的特殊性,如果具有支配地位的數字平臺采取系統化模式收購創新型初創企業,則會進一步強化其市場支配地位。通過整合初創企業的數據、技術、人才和知識產權等資產,數字平臺的競爭優勢得到強化,更容易將競爭對手排除在外。特別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數據驅動型并購,會使數字平臺獲得差異化的數據資源,短期內迅速提高在相關市場中的數據集中度。26美國眾議院在其發布的《數字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中指出,在線平臺作為信息、通訊、商品和服務的“底層基礎設施”,已掌握了關鍵分銷渠道的控制權,并成為“看門人”(gatekeepers)。這種強大且持久的市場力量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其中就包括具有支配地位平臺的大量收購,即通過收購新生的或潛在的競爭對手,以消除競爭威脅或維持并擴大公司的市場支配地位。27
數字平臺的市場支配地位得以鞏固和強化,還會引發其他負面效應。一是增加市場進入壁壘。借助于大規模的并購,數字平臺的壟斷勢力會向初創企業所在的市場(上下游市場或是相鄰市場)延伸,致使競爭對手和創新者的進入變得異常困難,市場進入壁壘在客觀上會有所增加,相關市場的競爭程度也會顯著降低。二是發生濫用行為的幾率提高。基于獲取初創企業數據、技術等資產驅動的并購,可能會誘發數字平臺定向實施反競爭性歧視行為的可能,28例如強制實施搭售、濫用非公開數據跟蹤潛在競爭對手、拒絕許可相關技術等。
2.阻礙和減損創新

數字平臺的扼殺型并購動機是通過并購初創企業來消除潛在競爭和創新,避免在位者的市場地位遭受潛在競爭者的蠶食。因此,實際存活的初創企業越少,創新的重要來源就越少,這也是扼殺型并購對創新阻礙的最直接表現。同時,此類并購還會通過影響研發投資,對創新造成間接減損。數字平臺頻繁地并購舉動,會在風險投資領域形成“殺戮地帶”(killing zone),進而影響對初創企業的投資。風險投資者通常對與大型數字平臺正面競爭的初創企業持謹慎態度,因為其成功進入的機會微乎其微。由于無法成功進入而導致風險投資的減少,實際上會導致更少的進入,而更少的投資也會致使市場差異化創新的減少。29正如經合組織在2017 年發布的《20 年數字經濟展望》指出的那樣,雖然小型初創企業更能抓住數字技術提供的新機會,但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可能會破壞這一潛力,有限的資本可能會進一步削弱進入者引入新產品、技術和網絡的能力。30
與此同時,對初創企業的持續性并購活動還會“反向扼殺”數字平臺自身的創新投資。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集中度較高且競爭較少的企業對研發的投資率相對較低,31這種投資缺口正是由行業領導者驅使的,競爭程度的下降是出現投資疲軟的主要原因之一。32大型數字平臺通過收購初創企業提供的新產品或服務,可能會停止或放棄自己開發競爭產品的內部努力,一旦這種并購模式成為數字平臺的常態化策略,則會消除平臺自主創新的投資和動力。33
三、初創企業并購的反壟斷規制困境
(一)游離于反壟斷審查門檻之外
從各國或地區的反壟斷法對企業并購控制的形式看,有事后監督審查制和事前申報審查制兩種形式。34絕大多數的反壟斷司法轄區主要采取事前申報審查制,35即參與并購的企業達到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申報標準時,須向有關主管機構申報,經審查許可后方可進行并購交易。為了避免增加企業申報和執法機構審查的負擔,申報標準通常會根據一定的營業額、市場份額、資產額等制定。這實際上是一種結構性的假設,如果并購只涉及營業額和/或市場集中度較小的增加,發生嚴重競爭損害的可能性較低,執法機構無需介入審查。36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營業額或市場份額的申報標準可以起到很好的篩選作用,有利于節約執法成本,提高審查效率。但在互聯網領域,大型數字平臺針對初創企業的并購幾乎很難達到當前的申報標準,因而不受強制申報義務的約束。對于大多數初創企業而言,其正處于集聚用戶群體、收集分析數據以及研發的早期階段,尚未實現產品(服務)的商業化和盈利化,因此營業額和市場份額通常很低,企業甚至會犧牲短期利潤,處于一種虧損階段,這導致針對初創企業的并購交易不會引起反壟斷執法機構的注意,盡管可能會產生扼殺潛在競爭和創新的反競爭效應。37也就是說,目前反壟斷法的并購審查門檻可能過高,無法涵蓋到數字平臺對初創企業的并購,并且這種并購政策低估了那些營業額或市場份額較小的初創企業對數字平臺施加的競爭約束,也忽視了數字平臺基于扼殺動機的并購活動。這一弊端在實踐中已愈發凸顯,例如,GAFA 在過去的十年中收購了數百家公司,其中許多并購消除了實際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在某些情況下,平臺企業完全關閉或終止了目標企業的產品,發生了所謂的“扼殺型并購”,但囿于當前過高的審查門檻,美國反壟斷執法機構極少介入,也沒有阻止任何一起交易。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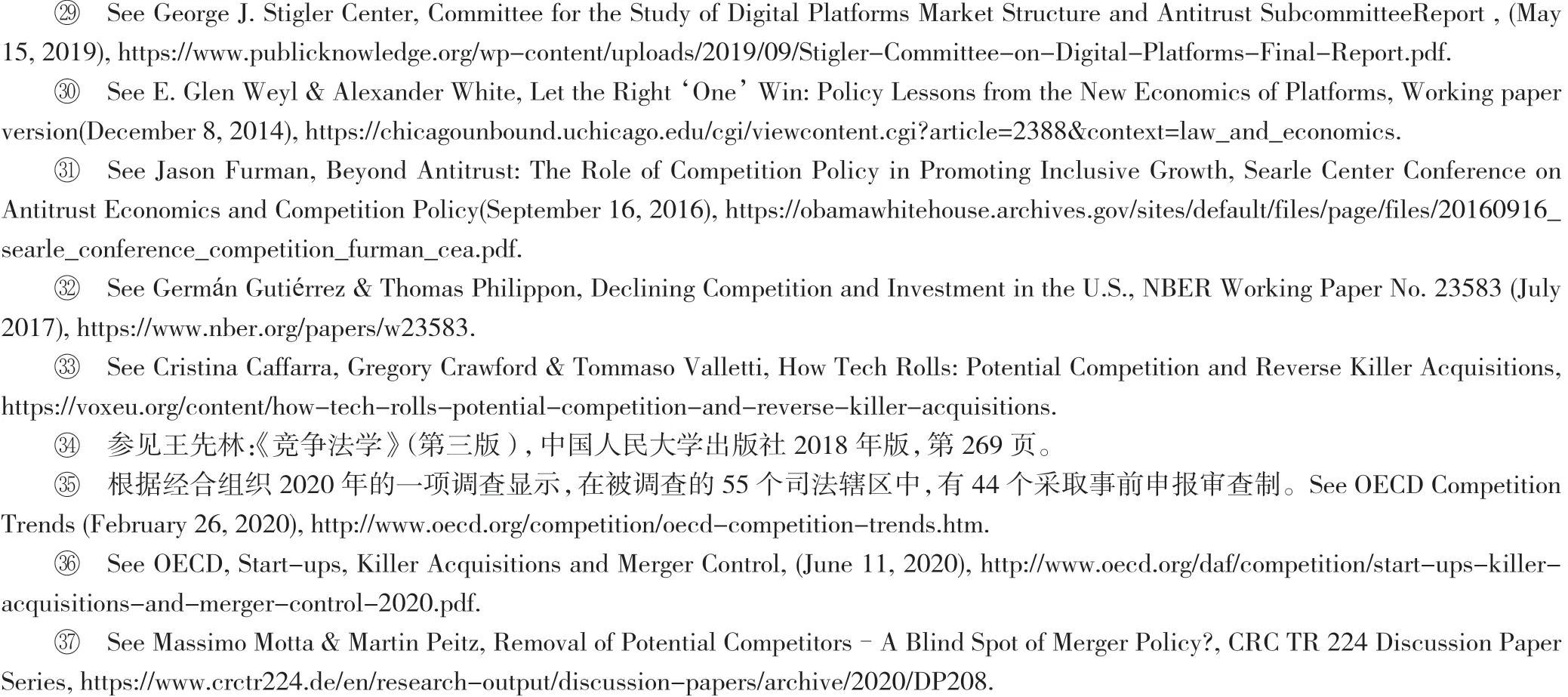
除此以外,有觀點認為,針對初創企業的并購交易游離于反壟斷審查門檻之外,還與競爭主管機構在數字市場過于保守的執法政策有關。受芝加哥學派的廣泛影響,一直以來,反壟斷執法機構更傾向于消極干預而非積極干預,因為后者的錯誤成本更高,其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持續更久。39反壟斷執法機構在評估對初創企業的并購交易時,主要涉及其對未來競爭的影響,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執法機構很少采取深思熟慮的措施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更多情況下是堅守一種近乎“不作為”的保守立場,以避免發生“積極失誤”。40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數字市場集中度增加、平臺并購浪潮迭起的原因之一。
(二)損害分析框架的適用局限
現有的反壟斷分析框架在處理數字平臺并購初創企業時,具有一定局限性。傳統的反壟斷法理論主要關注競爭的一個方面,即價格和競爭對手對價格的約束,41相關損害理論分析也主要著眼于并購交易的短期價格影響及對靜態市場結構的改變。42因此,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審查重點,是并購發生后短期內產生的靜態價格效應,通常不會對未來競爭的影響做出預測。這種靜態價格效應的分析,依賴于企業既有的市場份額和定價活動等數據。但正如前文所述,初創企業往往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其對商品(服務)價格的影響能力和市場份額尚不顯著,既有的分析框架很難作出有損競爭的分析結論。事實上,反壟斷執法機構真正需要考慮的,應當是此類并購對未來市場競爭和創新以及消費者長期福利的影響。例如,被收購的初創企業能否成長為一個積極而富有創新精神的競爭對手?該初創企業的重要價值是否源于創新,并且這種創新是否有利于降低相關市場的集中度?數字平臺借助該并購獲得數據和技術,是否會讓其更難被挑戰?43可見,在動態創新的數字市場,特別是對于那些試圖抑制潛在競爭和創新的并購,需要更具動態性和長期性的反壟斷分析框架,充分考慮該類并購對競爭損害的方式與可能性,但這恰恰是目前并購控制制度的一種局限。
另一個重要的局限,是當下對并購的分類及其適用的損害理論,無法完整地評價數字平臺對初創企業并購的復雜類型。一般而言,反壟斷并購審查的第一步,需要判斷擬議的并購是橫向并購、縱向并購還是混合并購,基于并購類型的不同,執法機構所適用的損害理論也存在區分。例如,橫向并購主要適用單邊效應(unilateral effects)和協調效應(coordinated effects)的損害理論,非橫向并購(即縱向并購與混合并購)主要適用封鎖效應(foreclosure effects)的損害分析框架。44但數字平臺對初創企業的并購,既可能是橫向并購,也可能是縱向并購或是混合并購,這導致損害理論的適用存在不確定性,并很難用一種損害理論對并購作出全面分析。

首先,初創企業可能與數字平臺在現有的市場存在產品(服務)重疊,此類并購屬于典型的橫向并購,執法機構可以適用單邊效應的損害理論,分析其對潛在競爭和非價格競爭(創新)的影響。45但具有挑戰性的是,執法機構如何在當下分析并購對未來市場的競爭與創新的影響。
其次,初創企業的產品、服務或技術可能是數字平臺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此時很難將其視為平臺的競爭對手。基于這種原因,部分針對初創企業的并購會被假定為縱向并購,某種意義而言,它們是不可證明的橫向并購。46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數字平臺通過并購阻止其他競爭對手獲得初創企業開發的有前景的新技術,則可能存在反競爭效應,例如強化平臺的市場支配地位、實施技術封鎖、阻礙創新等,但目前縱向并購中的損害理論尚不能對此作出有力回應。
再次,初創企業還可能與數字平臺不存在任何產品(服務)重疊,并且很難判斷其在未來會產生重疊,這類并購往往最為常見,其可被歸類為混合并購。47但在數字市場,受網絡外部性的作用,即使當下沒有產品(服務)重疊,一個擁有大量用戶基礎的初創企業可能會在未來進入該市場,并成為平臺的競爭對手。此時,平臺發起的并購會減少市場上的潛在競爭,然而這種反競爭效應很難在混合并購所適用的損害理論框架下得以評估。
(三)難以證明的反事實
反壟斷執法機構調查初創企業并購面臨最大的實踐挑戰,是如何確定相關的反事實(relevant counterfactual),即未發生并購時的預期事實。這也是損害分析中的關鍵環節,但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客觀上加大了執法機構的證明難度,致使反壟斷執法變得異常困難。一是反事實本身的不確定性。承前所述,在大多數情況下,初創企業對數字平臺造成的僅僅是一種潛在的競爭威脅,并可能處于不同“賽道”的競爭,尚未成為一個成熟的競爭對手。如果不存在并購,初創企業能否保持獨立?是否會進入數字平臺所在的產品市場?是否會形成以及能夠形成多大的競爭約束?這些不確定的反事實,在執法實踐中往往很難證明,任何過高或過低地估計,都會顯得很投機。二是數字平臺在信息獲取與分析方面比執法機構更具優勢,雙方信息的不對稱加大了執法難度。依托于強大的數據資源和技術優勢,數字平臺在早期便具有能力識別和跟蹤可能對其造成威脅的潛在競爭對手。平臺會利用這一信息優勢,構建卓越的“情報系統”以識別初創企業的競爭威脅,并采取并購、復制或扼殺這些初創企業的策略。48例如,臉書在收購WhatsApp前曾對其進行過密切監視活動,臉書的數據專家利用相關數據對WhatsApp 的參與度和影響范圍進行建模,以確定其對臉書自有產品“Messenger”構成競爭威脅。49相比之下,執法機構在對這些重要信息的獲取與分析能力方面存在劣勢,致使執法者難以識別并購的真實動機,也很難證明并購產生的反競爭效應。
四、初創企業并購反壟斷規制的應對方略
(一)事前審查與事后調查的協同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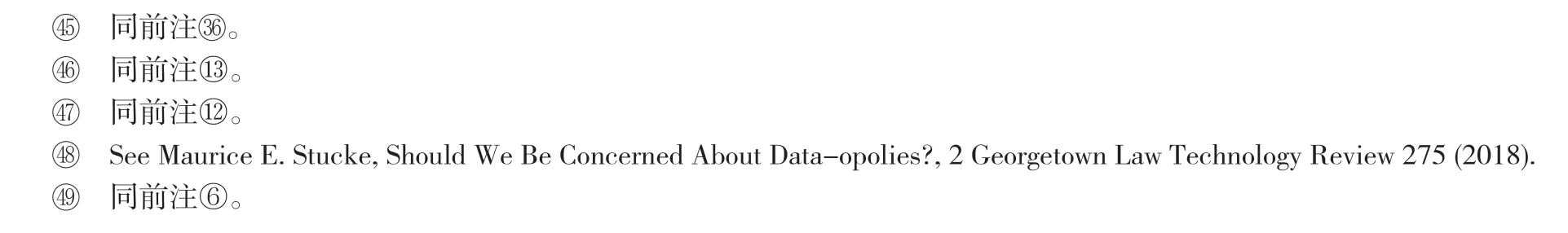
基于數字市場企業發展的特殊性,初創企業的競爭潛力無法反映在營業額或市場份額的標準之中,因而逃脫了反壟斷事前審查。為了補足這一缺漏,反壟斷執法機構有必要調整并購申報門檻,在當前營業額標準的基礎上引入能夠有效篩查具有反競爭效應的并購的其他適當標準。一些國家在修訂反壟斷法時,新增了基于交易價值的申報門檻。例如,德國在2017 年對《反限制競爭法》進行第九次修訂時,引入了所謂的“交易額條款”,對于并購交易價值超過4 億歐元的,應當事前向聯邦卡特爾局申報。在隨后的2017年5 月,《奧地利卡特爾與競爭法修正案》也引入了交易額條款,規定交易額達到2億歐元,參與并購交易的企業就有申報的義務。50該標準的補充意味著執法機構需要對此類并購保持高度關注,因為高價收購一家低營業額的初創企業極可能暗含妨礙創新的過程,有必要開展進一步的反壟斷分析。正如兩國反壟斷執法機構共同指出的那樣,“領先市場的企業有能力通過收購仍處于發展初期的競爭對手,改變或者終止后者的原始活動,來完全整合新型競爭對手,或者將其資產整合至自身的業務之中。相應地,這類收購所體現出的高額收購價款就意味著創新型商業理念具備重大市場競爭潛力。從競爭政策角度來看,這類收購就需要事先的并購審查,尤其是為了保護創新潛能,以及技術市場中的創新競爭。”51有研究建議,應當對具有戰略市場地位的數字平臺科以更嚴格的申報義務,要求其向反壟斷執法機構及時報告所有的并購交易,以使執法機構擁有更多的機會審查這些合并。52該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我國目前的市場發展階段和反壟斷執法力量而言,不具有現實性。特別是過度的并購審查,可能會堵死初創企業退出市場的正當途徑,抑制初創企業的業務形成,從而損害經濟創新的動力和創業生態系統的良好運行。53有鑒于此,我國反壟斷執法機構可適當地調整并購申報門檻,在明確合理的營業額標準的基礎上,也引入交易價值的申報標準,確保執法機構有更多機會審查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應的初創企業并購。值得關注的是,《平臺反壟斷指南》第19 條明確規定,即便未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反壟斷執法機構仍可以主動調查,這事實上進一步擴大了執法機構的事前審查權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此外,多國反壟斷執法機構近年來還展開了針對數字市場并購案件的事后調查,以評估當前的并購政策和交易完成的并購案件。例如,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CMA)在2019 年委托Lear 咨詢公司,對亞馬遜、臉書和谷歌在2008 年至2018 年期間公開披露的299 起并購案件展開全面分析,就是否存在扼殺型并購以及英國當前的并購政策能否應對進行檢視。加拿大競爭局在2019 年成立了并購情報和通知小組(MINU),對未達申報門檻但可能引發實質性競爭問題的并購進行監測和調查。54目前,美國、日本、巴西、加拿大、英國、匈牙利、愛爾蘭、瑞典和立陶宛等國家的反壟斷法,明確賦予了反壟斷執法機構在并購交易完成后仍享有一定的調查權。這種事后調查模式,有助于彌補執法機構因數字市場并購中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假陰性”錯誤,不失為一種有益舉措,值得我國反壟斷法借鑒與推進。
(二)執法工具的革新
數字平臺并購初創企業的動因復雜,包括效率驅動的資產整合,拓展市場的策略進入,以及扼殺潛在競爭與創新的競爭防御等。基于數字平臺的信息優勢,執法機構往往很難掌握其并購的真實動因。同時,針對初創企業并購的類型也具有多樣性,既可能構成橫向并購,也可能構成非橫向并購(即縱向并購與混合并購)。反壟斷執法機構如何快速、有效、便捷地識別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應、需要加強審查的初創企業并購,是執法實踐面臨的一大挑戰。對此,有必要革新目前的反壟斷執法工具。通過考察域外的創新實踐,以色列競爭管理局(ICA)探索出的并購交易分類審查模型,55可為我國提供有益參考。
根據收購方的交易動機和被收購產品(服務)的具體特征,ICA 創建了一個基本模型(見上頁表格),將并購交易區分為“綠色”和“黃色”兩個類別。其中,歸類為“綠色”的并購交易除了在實體市場中進行一般審查外,不需要進行其他審查,而歸類為“黃色”的并購交易則需要結合數字市場中可能出現的特定競爭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審查。具體來看,交易動機主要以收購方旨在獲取初創企業的何種資產作為依據,將其區分為“購-聘”、技術、數據和信息三個類別。被收購產品(服務)的特征則分為接口產品和獨立產品兩個類型。所謂接口產品(interface products),是指為了改進或擴展平臺功能而有意開發的補充產品,如果被收購產品的唯一開發目的就是與特定平臺集成,此類并購不太可能損害競爭或阻止潛在競爭對手的發展,但如果除了特定平臺,被收購產品還能與其他數字平臺進行集成,相關競爭分析將變得復雜,需要進一步審查。獨立產品(stand-alone products),是指獨立于平臺而單獨運行的產品。ICA 認為,收購開發獨立產品的初創企業可能會引發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中的各種競爭問題。特別是在被收購企業有潛力發展該獨立產品并進入數字平臺產品市場的情況下,并購初創企業可能會導致反競爭效應。
基于以上兩個維度的分類,針對初創企業的并購交易總體上可劃分為兩大類別。“綠色”類別包括對特定平臺接口產品的初創企業的并購,以及旨在實現雇傭員工目的的初創企業并購,這兩類并購一般不會出現特別的競爭損害,只需一般審查即可。“黃色”類別意味著需要結合數字經濟的特殊性進行更為深入的特別審查:第一,并購初創企業的主要動機是獲取技術,需要特別關注傳統的橫向或縱向并購的問題,以及數字平臺是否會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提高進入壁壘等。第二,被收購產品為獨立產品的,需要特別關注混合并購帶來的競爭問題。例如,數字平臺是否會實施搭售以阻止市場競爭,初創企業是否有潛力開發新產品并進入平臺的產品市場。第三,并購初創企業以獲取信息和數據為主要動機的,除了需要關注傳統的橫向和縱向并購的問題外,還需要考慮混合并購帶來的競爭隱憂,特別是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作用下,大型數字平臺的數據整合可能導致市場的進一步集中,從而削弱競爭對手當前或未來的競爭。
盡管上述并購交易分類模型只是初步的審查框架,但為執法機構提供了一個高效率的執法工具,能夠快速分辨和篩查可能具有高違法風險和競爭隱憂的初創企業并購。我國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考慮吸收和引入,將其補充到現有的反壟斷執法“工具箱”,以提高并購審查的效率。
(三)損害分析框架與證明責任制度的改進
數字市場的初創企業并購對現行反壟斷法的分析框架造成一定沖擊和挑戰,但總體來看,既有的損害理論仍可以適用,只不過需要在損害分析框架上作出適當改進和調整。譬如,人們普遍關心的潛在競爭與創新損害,事實上在橫向并購的單邊效應損害理論中已有所涉及。歐盟《橫向合并指南》認為,并購雙方即使未在任何相關市場產生實際競爭,并購也可能產生單邊效應,歐盟還在若干案件中評估了單邊效應因消除潛在競爭而產生的風險。57同時,歐盟《合并控制條例》所確立的“嚴重妨礙有效競爭”(SIEC)實質評估標準,也涵蓋了包括因妨礙創新而對消費者造成的損害,并將競爭壓力降低所致的創新損害與價格、產量的損害等同起來。58美國《橫向并購指南》同樣在單邊效應損害理論中確立了對創新與產品種類多樣性的分析考察,“執法部門會考慮一項合并是否可能通過鼓勵合并后企業將其創新努力降低至不合并時水平之下,來減少創新競爭。創新的減少可能表現為減少繼續現有的產品開發努力的激勵,或減少開發新產品的激勵。”59我國《平臺反壟斷指南》第20 條也特別強調了并購“對經營者創新動機和能力的影響,對初創企業、新興平臺的收購是否會影響創新”。但正如前文指出的,初創企業并購往往不局限于橫向并購,也可能是縱向并購或者混合并購,這使得損害理論的適用存在局限。基于此,筆者建議可以采取一種綜合性的損害分析思路,不再狹窄地將其區分為橫向并購、縱向并購與混合并購,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特殊的并購類別,綜合適用各種損害理論。換言之,此種綜合性的損害分析框架,就是在目前的非橫向并購損害理論中注入橫向并購損害理論的內容,以更好地考察并購對潛在競爭和創新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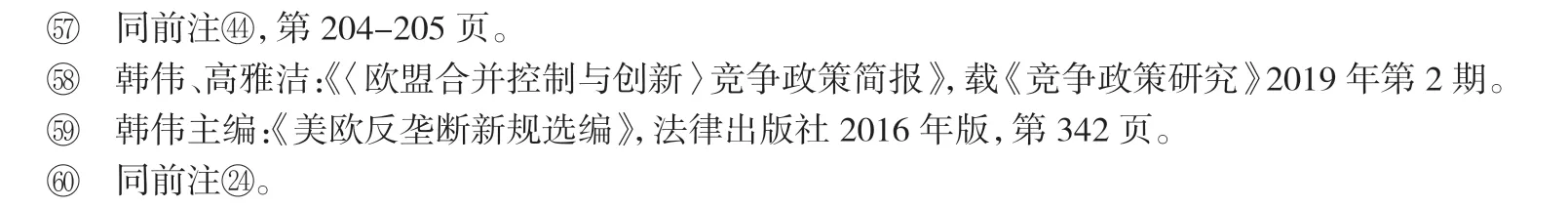
然而,反壟斷執法機構如何在實踐中評估這些影響與反事實,特別是基于動態性和長期性的考察視角作出執法決策,還涉及到具體損害測試方法的創新。對此,理論界嘗試提出了一些新方法,例如“損害平衡”標準(Balance of Harms)。該方法旨在為反壟斷并購審查提供一個經濟的方案,主張執法機構不僅要看預期損害發生的可能性,還要看預期損害發生后反競爭效應的可能規模,在權衡利弊可能性和影響程度的基礎上,決定并購是否應當被阻止。60這是一種數學意義上的“預期”與“平衡”,假設一項并購有20%的機會導致2.5 億美元的競爭損害,80%的機會產生5000 萬美元的效益,那么交易應該被阻止,因為其預期價值為負(-1000 萬美元)。61這種基于客觀計算的標準有利于提升執法決策的透明度和確定性,但現實情況是執法機構很難估計出這些概率和福利(損害)結果。
可見,在測算損害影響和反事實證明方面,反壟斷執法仍然面臨很大挑戰,這有賴于相關經濟分析工具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但這種挑戰并非是無法逾越的現實障礙,通過對反壟斷法相關制度的改革,可以有效扭轉當前的執法困局。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當前反壟斷并購控制制度采取的是一種效果分析立場,由執法機構承擔并購反競爭效應的證明責任。但數字市場的強網絡效應和高集中度特征,改變了反壟斷法的實施成本與錯誤成本間的平衡,62數字平臺與執法機構的信息不對稱,進一步加劇了執法機構的舉證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對既有的規則作出調整,例如向大型數字平臺施加證明其行為促進競爭的舉證責任,而不是完全由執法機構證明并購對市場的負面影響。這種證明責任制度的改進,有助于扭轉反壟斷執法機構當前在數字市場中的執法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