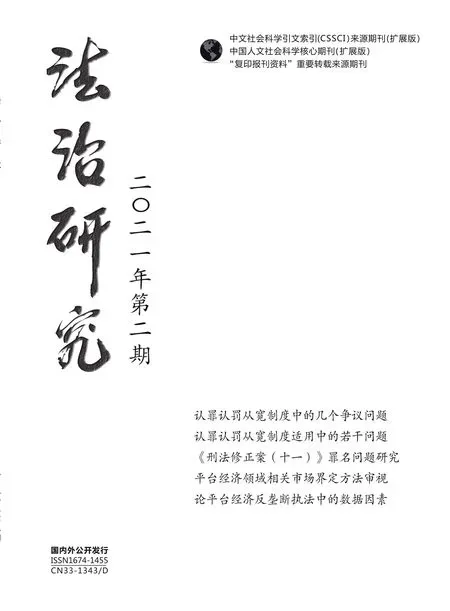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問題研究
趙秉志 袁 彬
2020 年12 月26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是我國因應社會形勢變遷、回應社會重大熱點進行的一次重大刑法立法。該刑法修正案不僅降低了刑事責任年齡、對已有犯罪的調整范圍和處罰進行了調整,而且修改、增設了20 余種罪名。這就涉及罪名的修改和新設問題,需要明確罪名確立的基本原則,并具體確定《刑法修正案(十一)》相關條文的罪名。
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確立的基本原則
罪名是對罪狀的概括和抽象。“罪名對犯罪行為作出認定,在人際互動中約束人們的行為,其人際意義表現為對行為的價值評判。謀殺、敲詐、勒索等行為對外界施加了不好的結果,是不道德的、邪惡的,評價意義雖然隱性但強烈,傳達了對非正當行為的譴責,其消極的人品裁決賦予罪名負面的評價意義。”①王振華、方碩瑜:《刑法罪名中的名物化現象——基于英美法律體系與中國法律體系的比較》,載《語言與法律研究》2020 年第1 期。人們主要是通過罪名識別罪行并據此判斷行為的性質。從這個角度看,罪名對于刑法目的和功能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罪名的確立需要堅持以下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準確性原則。罪名的準確性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具體體現。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罪”和“刑”的法定。其中,“罪”多被理解為“罪行”。但實際上,“罪名”的法定也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我國刑法對部分犯罪的罪名實現了法定,如貪污罪、受賄罪、行賄罪。但刑法對絕大多數犯罪都沒有規定罪名,沒有實現罪名的法定。從罪刑法定原則的角度,罪名的確立必須立足于罪狀,即罪名的確定必須嚴格按照刑法規定的罪狀進行,既不能超越具體條文的含義,也不能遺漏犯罪的重要特征和性質。“罪名的法定性特征要求應深刻把握犯罪性質、準確確定罪名,這樣才能維護法律權威。”②劉劍:《罪名功能新探》,載《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8 年第1 期。
但問題是,在不少場合,刑法關于具體犯罪構成的規定比較分散、具體,罪名與具體罪狀之間難以實現有效的對應,罪名確定的行為范圍要么大于罪狀要么小于罪狀。③參見晉濤:《論罪名的法定化:機遇及路徑》,載《政法學刊》2016 年第6 期。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七)(征求意見稿)》④該《征求意見稿》于2020 年12 月31 日向有關單位和部分專家學者征求意見,其計劃確定罪名的范圍包括《刑法修正案(十)》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修正的罪名,以及根據近年來司法實踐反映的情況而需要調整的罪名。(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中,既有罪名范圍大于罪狀的情況,也有罪名范圍小于罪狀的情況。前者如《征求意見稿》將刑法典第280 條之二(《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2 條)的罪名確定為冒名頂替罪,該罪名對應的行為范圍要遠大于罪狀的范圍;后者如《征求意見稿》不主張對刑法典第141 條第2 款、第142 條第2 款單獨設立罪名(適用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生產、銷售劣藥罪),⑤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七)(征求意見稿)》(2020 年12月31 日)。但該款對應的行為“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明知是假藥/劣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其“提供”的行為范圍要明顯大于“銷售”行為,《征求意見稿》將該行為納入“銷售假藥罪”“銷售劣藥罪”的范圍,罪名對應的行為范圍要小于罪狀。在此情況下,如何確定罪名才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對此,我們認為,罪名對應的行為范圍必要時可以大于罪狀,但不能小于罪狀。這是因為:
一方面,罪名對應的行為范圍大于或者小于罪狀都不契合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最大化地發揮刑法語言的明確性,以增強民眾對自身行為的預測可能性。在此情況下,罪名要發揮其應有的行為預測功能,就要求其準確反映罪狀的內容。因為罪狀才是對行為進行定罪的依據,罪名不能準確反映罪狀的內容,必然削弱人們通過罪名預測自己行為后果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罪名對應的行為范圍大于罪狀還是小于罪狀,都不契合罪刑法定原則。不過,由于語言表達的有限性,在個別場合,罪名的用語與罪狀的內容要完全對應,這對罪名的確立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甚至在一些場合是根本無法做到罪名與罪狀的完全對應。造成這種現象也有立法方面的原因,即立法者對罪狀的描述沒有周全地考慮到罪名確立的需要,導致最高司法機關在制定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時無法找到合適的詞語用于確定罪名。
另一方面,兩者相比較,罪名范圍大于罪狀的情形更接近契合罪刑法定原則。在罪名范圍大于和小于罪狀這兩種情形都不完全契合罪刑法定原則的情況下,相對于罪名范圍小于罪狀的情形,罪名范圍大于罪狀的情形更接近契合罪刑法定原則。這是因為前者會導致人們對自己行為后果的完全錯誤判斷,后者只會導致人們對自己行為后果的不準確判斷。從罪名的預測功能上看,在罪名范圍小于罪狀范圍的情形下,人們如果僅從罪名上進行判斷,是無法對罪名范圍之外的行為后果進行判斷的,在此情況下如果還要依據罪名進行行為后果的判斷,則只會得出完全錯誤的判斷。而導致這種錯誤發生的主要原因,無疑在于確定罪名的最高司法機關。相反,在罪名范圍大于罪狀范圍的情形下,人們如果僅從罪名上進行判斷,只會在一定范圍內限制其合法行為的范圍,并不會導致人們因誤判而陷入犯罪。簡而言之,在罪名與罪狀范圍不一致的場合,罪名大于罪狀的,人們更可能限縮其合法行為的范圍;罪名小于罪狀的,人們更可能擴張其犯罪行為的范圍。兩害相權取其輕,罪名范圍大于罪狀范圍的,顯然相對有利于保障人們的權利,進而相對更接近契合罪刑法定原則。
第二,合理性原則。這里的合理性是指因罪名確立而導致的處罰合理性。該合理性在形式上體現為罪名數量確定的合理性,即如何合理地把握是確定一個罪名還是數個罪名。⑥同前注③。在刑法上,罪名的個數關乎罪數的處理,也關乎數罪并罰制度的適用。例如,對于行為人實施的兩個以上行為,如果這些行為雖然不同但觸犯的是同一罪名(包括選擇罪名),根據我國刑法是不能對其進行數罪并罰的。但如果這些不同行為觸犯的是不同罪名,根據我國刑法則可能要對其進行數罪并罰。在通常情況下,數罪并罰比不數罪并罰的處罰要更重。以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為例,行為人如同時實施了四個行為,按照選擇罪名對行為人只能定一個罪名(即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如該罪名不是一個罪名而是四個罪名(即走私毒品罪、販賣毒品罪、運輸毒品罪和制造毒品罪),則要對行為人定四個罪并進行數罪并罰。一般而言,后者對行為人的處罰要更重。按照合理性原則,在對某種行為是否單獨確立罪名、確定一罪名還是多罪名,需要考慮處罰的合理性。對于行為之間關聯性不高的不同行為,原則上應當單獨確立罪名或者確立不同的罪名。但對于一些關聯性很高的不同行為,則可以不確立罪名或者只確立一個罪名(如選擇罪名)。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司法上普遍存在的多罪一名現象⑦參見丁勝明:《以罪名為討論平臺的反思與糾正》,載《法學研究》2020 年第3 期。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
第三,簡潔性原則。簡潔性原則關乎罪名的長短。過去,“兩高”確立的罪名中有些罪名的表述很簡潔,如危險駕駛罪,也有些罪名的表述很冗長,如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致人重傷、死亡罪。與準確性、合理性原則相比,簡潔性原則是為了便于掌握、適用,它的正當性是建立在罪名的準確性、合理性之上,不能為了簡潔而犧牲罪名的準確性和合理性。一般而言,罪名要做到簡潔要求罪名對罪狀進行較高程度的概括,個別情況下可能要求舍棄部分構成要件的表述。由于罪名在詞語構成上的完整結構是“主語+謂語+賓語”,因此罪名的簡潔只能在結構上下功夫,包括分別對“主語”“謂語”和“賓語”進行高度概括,也包括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下舍棄部分結構(如舍棄“主語”“賓語”,但不能舍棄“謂語”即行為)。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的具體確定
根據罪名確定的準確性、合理性和簡潔性原則,對比《征求意見稿》,筆者主張將《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新增的罪名確立如下:
(一)妨害安全駕駛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 條是在刑法典第133 條之一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33 條之二,其罪狀包括兩類:一是“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危及公共安全的”(第1 款);二是“前款規定的駕駛人員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第2 款)。該條的罪名宜規定為“妨害安全駕駛罪”。主要理由是:
第一,該條兩款涉及的行為具有高度的關聯性甚至行為交叉性,不宜規定為兩個罪名。例如,該條第1 款的“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和第2 款的“前款規定的駕駛人員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可能是對向行為,即駕駛人員與乘客互毆。對于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行為,確立為一個罪名更合適。
第二,該條罪狀的結構較為復雜、繁瑣,需要進行高度概括。從結構上,該條兩款罪狀的結構較為繁瑣,其主語是“一般主體+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謂語是“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賓語是“駕駛人員+駕駛操控裝置+他人”。這意味著,該條罪名的確立要求對罪狀要素進行必要的概括和舍棄。將該罪的罪名概括為“妨害安全駕駛罪”,一方面是舍棄罪狀結構的主語和賓語,因為該罪狀的主語和賓語都包含了一般主體和普通對象,沒有單獨納入罪名的必要;另一方面是概括了該罪狀的謂語結構,以第1 款的罪狀為基礎,將該條規定的兩個行為(實為四個具體的行為)概括為“妨害安全駕駛”。從“妨害安全駕駛”的內涵上看,它可以較好地涵蓋該條第1 款的行為,同時也能涵蓋該條第2 款的行為。不足之處是“妨害安全駕駛”更多的是反映駕駛人員以外的人對駕駛的妨害,駕駛人員對駕駛的妨害可以納入“妨害安全駕駛”的范圍,但不是典型行為。
(二) 組織、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 條規定的罪狀是“強令他人違章冒險作業,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該罪狀是在刑法典原第134條第2 款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的基礎上增加了“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的內容。筆者認為,該條的罪名宜確定為“組織、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理由主要是:
第一,原罪名“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無法涵蓋新增罪狀內容。與刑法典原第134 條第2 款的規定相比,《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冒險組織作業”行為。從內容上看,該“冒險組織作業”無法為“強令違章冒險作業”所涵蓋。在此基礎上,如果不對原有的罪名進行修改,將出現罪名的行為范圍要明顯小于罪狀的行為范圍情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無法體現罪名的準確性原則,應當進行修改。在筆者看來,反對修改該罪名的理由難以成立。⑧反對修改該罪名的理由包括:一是雖然此次修正增加了情形,但“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可以解釋為廣義的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目前的罪名表述既可以反映核心特征,涵蓋新增罪狀表述;二是本罪名適用多年,不論司法工作者還是廣大人民群眾均已適應,不動為宜。參見前注⑤。
第二,將該罪名確立為“組織、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能較好地概括新增內容。這是因為:一方面,“強令”無法涵蓋“組織”行為,需要將“組織”行為在罪名中予以體現;另一方面,新增的“冒險組織作業”和“組織違章冒險作業”意思完全相同,“冒險組織”實為“組織冒險作業”,而“冒險作業”肯定是違章的,如果是不違章的冒險作業不應成為刑法懲治的對象。
(三)危險生產、作業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 條是在刑法典第134 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34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是“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的行為,并列舉三種違反規定嚴重的行為,即“關閉、破壞直接關系生產安全的監控、報警、防護、救生設備、設施,或者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數據、信息的”“因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被依法責令停產停業、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關設備、設施、場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險的整改措施,而拒不執行的”和“涉及安全生產的事項未經依法批準或者許可,擅自從事礦山開采、金屬冶煉、建筑施工,以及危險物品生產、經營、儲存等高度危險的生產作業活動的”。筆者認為,該條規定的罪名宜確定為“危險生產、作業罪”。主要理由是:
第一,應將該條的生產、作業限定為“危險生產、作業”。這是因為,該條規定的違反安全管理規定的生產、作業都是“具有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現實危險的”生產、作業行為,而非所有違反安全管理規定的生產、作業行為,應當對其作一定的限定。
第二,應將生產、作業并列規定于罪名上。在罪名研討過程中,有觀點主張將該罪的罪名設定為“危險作業罪”,認為作業能將生產涵蓋。⑨同前注⑤。但實際上,生產與作業雖然在內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兩者并不等同,生產可以體現為一種作業,但并不僅限于作業,也可以是常規的生產管理活動。從這個角度看,該條第1、2 項規定的行為不一定發生在作業過程中,也可以發生在常規的生產管理活動之中(如尚未實際進行生產作業,但關閉了安全設施,或者作業之后隱瞞、銷毀相關數據、信息)。
(四)非法提供假藥罪、非法提供劣藥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5 條第2 款、第6 條第2 款)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5 條第2 款、第6 條第2 款是在刑法典第141 條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第142條生產、銷售劣藥罪的基礎上,增加規定: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明知是假藥/劣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的,要依照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劣藥罪的規定處罰。對于該兩款的規定,筆者認為宜確定兩個新罪名:非法提供假藥罪和非法提供劣藥罪。主要理由是:
第一,這兩款對應的行為應當規定單獨的罪名。這是因為,這兩款規定的行為都是“提供”行為(包括提供假藥和提供劣藥)。在行為內涵上,“提供”包括有償提供和無償提供,前者能為“銷售”行為所涵蓋,但后者則不能為“銷售”行為所涵蓋。在此情況下,將非法提供假藥、劣藥的行為按照銷售假藥罪、銷售劣藥罪進行定罪,名不副實,會導致人們對自身行為后果的不當評價,也無法發揮罪名的行為預測功能。從實踐的角度看,這兩種行為主要是針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在明知是假藥或者劣藥的情況下,仍提供給他人使用的行為。此種情形中并不直接支付對價,似難以解釋為銷售假藥或者劣藥。⑩同前注⑤。
第二,這兩款規定的是非法提供行為。從罪狀上看,這兩款對提供行為進行了兩個方面的限定,即“明知是假藥/劣藥”(主觀限定,即主觀違法)和“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主體限定,即主體違法)。這表明,并非所有的提供行為都是犯罪行為,只有具有特定違法性的行為才是這兩款規定的提供行為,即主觀違法和主體違法。從行為識別的角度看,將這兩款行為對應的罪名分別確定為非法提供假藥罪、非法提供劣藥罪,顯然更為合適。
(五)妨害藥品管理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7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7 條是在刑法典第142 條之后增設一條作為第142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四種違反藥品管理法規的具體行為,包括:“(一)生產、銷售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禁止使用的藥品的;(二)未取得藥品相關批準證明文件生產、進口藥品或者明知是上述藥品而銷售的;(三)藥品申請注冊中提供虛假的證明、數據、資料、樣品或者采取其他欺騙手段的;(四)編造生產、檢驗記錄的。”該條規定主要是針對《藥品管理法》修訂前部分“按假藥論處”的情形及藥品申請注冊、生產過程中的文件、記錄造假,將打擊范圍擴展至生產、銷售藥品的前后及整個過程,屬于違反《藥品管理法》關于藥品過程管理秩序的行為,宜規定單獨罪名。
而從罪狀的內容上看,該條規定的是“違反藥品管理法規”的四種具體行為。這四種行為具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行為的特定性。該四種行為都是特定的,包括生產、銷售藥品(禁用藥品、違規藥品),騙取藥品注冊,編造生產、檢驗記錄。二是行為的危險性,即要求行為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從這兩個方面看,《刑法修正案(十一)》該條規定的違反藥品管理法規的行為是嚴重違反藥品管理法規的行為。考慮到“兩高”之前對類似犯罪設置的罪名都是采用“妨害……管理”罪的表述(如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因此該條的罪名也可確定為“妨害藥品管理罪”。
(六)欺詐發行證券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8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8 條是對刑法典第160 條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的修正,其規定的罪狀是“在招股說明書、認股書、公司、企業債券募集辦法等發行文件中隱瞞重要事實或者編造重大虛假內容,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存托憑證或者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與修正前的刑法典第160 條相比,該條主要是擴大了行為的對象,即將行為對象由“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擴大至進一步包括“存托憑證或者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由于“兩高”針對修正前的刑法典第160 條規定的罪名是“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因此修正后的刑法典第160 條罪名可確定為“欺詐發行證券罪”。
(七)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3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3 條是在刑法典第219 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129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的”行為。從行為內容上,該行為也是一種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可納入刑法典第219 條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范疇。但《刑法修正案(十一)》將該行為單獨規定為一條作為刑法典第219 條之一(而非作為刑法典第219 條的一款),這意味著立法者認為該行為有單獨設置罪名的必要。考慮到“兩高”關于罪名的司法解釋已經確定刑法典分則中存在兩個類似罪名(即刑法典第111 條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罪和第431 條第2 款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軍事秘密罪),因此該條的罪名宜相應地確定為“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
(八)特殊職責人員性侵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 條是在刑法典第236 條強奸罪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36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行為。對該條罪名的確定可以有兩種方案:
第一,將該罪的罪名確定為“特殊職責人員奸淫未成年女性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 條罪狀的基本結構是主語“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謂語“發生性關系”+賓語“該未成年女性”。從行為的內涵上看,“發生性關系”主要是雙方自愿發生的性關系。結合我國刑法典第236 條奸淫幼女的表述,對“發生性關系”的準確表述應該是“奸淫”,因此從完整表述看,該條罪名應為“特殊職責人員奸淫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未成年女性罪”。考慮到該罪名較長,從簡潔性原則出發,可將該罪的罪名確定為“特殊職責人員奸淫未成年女性罪”。
第二,將該罪的罪名確定為“特殊職責人員性侵罪”。相比于前一個罪名方案,該罪名最大的特點是省略了行為的對象(賓語),更為精煉。其不足之處在于“性侵”反映的都是非自愿的情形,似乎難以涵蓋已滿14 周歲不滿16 周歲未成年女性在自愿情況下發生性關系的情形。不過,如果將已滿14 周歲不滿16 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視為不具有完全性決定能力的人,那么將該罪的行為表述為“性侵”也是可以的。
對比上述兩個罪名方案,將該罪的罪名確立為“特殊職責人員性侵罪”,似更符合罪名確立的原則,較為適當。
(九)暴力襲警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1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1 條將刑法典第277 條妨害公務罪第5 款“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從重處罰”修改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筆者認為,該條已將刑法典第277 條第5 款由妨害公務罪的從重情節改造成為獨立的罪名規范,其罪名宜確定為“暴力襲警罪”。主要理由是:
第一,該款規定雖屬妨害公務犯罪的范疇,但有成立單獨罪名的必要。這是因為:一方面,該款的罪狀具有特殊性,不僅行為方式僅限于“暴力”,而且行為對象僅限于“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具備獨立確定罪名的基礎。另一方面,該款的法定刑明顯不同于妨害公務罪,其法定刑包括兩檔(妨害公務罪只有一檔法定刑),且法定最高刑明顯高于妨害公務罪。
第二,該款的罪狀突出了手段和對象的特殊性。該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沒有體現在罪名中的必要和條件;該罪的手段和對象都是特定性,可較好地體現在罪名之中。同時,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暴力襲警的表述已約定俗成,因此可將該條罪的罪名確定為“暴力襲警罪”。
(十)冒名頂替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2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2 條是在刑法典第280 條之一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80 條之二,該條規定的罪狀包括兩種行為:“盜用、冒用他人身份,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的”(第1 款),和“組織、指使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的”(第2 款)。該條罪名的確立需要明確兩個問題:
第一,該條第1 款的罪名確立。該條第1 款的核心行為包括兩個:一是“盜用、冒用”他人身份;二是“頂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學歷教育入學資格、公務員錄用資格、就業安置待遇。由于“盜用”包括“盜取”和“冒用”兩個行為,因此將“盜用、冒用”他人身份概括為“冒名”是適當的。在此基礎上,該條第1 款的罪名確立為“冒名頂替罪”較為合適。
第二,該條第2 款是否有獨立設立罪名的必要。從行為類型上看,該款規定的行為是“組織、指使”他人冒名頂替行為。從“兩高”過去設立罪名的情況看,“組織”行為有設立獨立罪名的先例,如刑法典第284 條之一第1 款的組織考試作弊罪;“指使”行為則類似于教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教唆。因此,若將該款行為獨立設置一個罪名似并無不妥。但考慮到該行為與該條第1 款的行為具有高度關聯性,可成為該條第1 款行為的共同犯罪,基于罪名確立的合理性原則,筆者認為該條第2 款的行為沒有必要設置獨立的罪名。
綜上,該條的罪名可以統一確定為“冒名頂替罪”。
(十一)高空拋物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3 條是在刑法典第291 條之一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91 條之二,該條規定的罪狀是“從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拋擲物品,情節嚴重”。從罪狀結構上看,該罪狀的核心詞是“高空拋擲物品”。據此,在罪名上,該罪的罪名可以確立為“高空拋擲物品罪”,也可以確立為“高空拋物罪”。從罪名涵蓋上看,“高空拋物”似乎沒有包括“高空擲物”的情形,但從擴大解釋的立場看,“拋物”可以認為是“拋擲物品”的簡稱;同時,考慮到“高空拋物”的表述已經通俗易懂,因此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高空拋物罪”比較妥當。
(十二)違法催收非法債務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4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4 條是在刑法典第293 條尋釁滋事罪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93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情節嚴重的:“(一)使用暴力、脅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的。”從罪狀上看,該罪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催收債務手段的違法性,即必須采用暴力、脅迫、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侵入他人住宅、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等非法手段進行,采用合法方式(如訴訟)催收債務的不構成本罪;二是催收之債務的非法性,即催收的必須是非法債務,包括高利貸、賭債等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基于罪名確立的準確性和簡潔性原則,可以考慮將該罪的罪名確定為“違法催收非法債務罪”。
“兩高”《罪名征求意見稿》將《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4 條的罪名擬定為“非法討債罪”。?同前注⑤。應該說,該罪名具有很強的概括性,且通俗易懂,并似乎屬于約定俗成用語。不過,從罪名應準確反映罪狀的角度看,該罪名似存在過于概括的問題,而不能充分反映該條罪狀的內容,對于一般民眾而言,該罪名不具有很高的行為辨識性。這是因為,根據《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4 條的規定,采取非該條列舉的手段討要非法或者合法債務、采取該條列舉的手段討要合法債務的行為都不能構成該條規定的犯罪。因而從更準確表達犯罪構成特征的角度進行推敲,我們主張可將該條的罪名定為“違法催收非法債務罪”。
(十三)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5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5 條是在刑法典第299 條侮辱國旗、國徽罪和侮辱國歌罪之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99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侮辱、誹謗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節嚴重的”行為。該罪狀的核心結構是謂語“侵害”+賓語“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由于這個結構已經比較精煉、概括,因此可以用該罪狀的核心結構作為該罪的罪名,即“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
(十四)組織跨境賭博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6 條第3 款)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6 條是對刑法典第303 條作了修改,并在第1 款賭博罪和第2 款開設賭場罪之后增設了第3 款,該款規定的罪狀是“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參與國(境)外賭博,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對于該款罪狀,有觀點認為,不應對其規定獨立的罪名,主張根據該款“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的規定,適用該條第2 款規定的開設賭場罪之罪名。其主要考慮是:該行為可以理解為開設賭場罪的共犯或者片面共犯,在量刑時可比照適用共同犯罪的有關規定;如果單獨入罪,反而不利于區別處理,其處罰甚至可能會重于賭場“老板”。?同前注⑤。但筆者認為,應當對該款規定的罪狀設立單獨的罪名,可以確定為“組織跨境賭博罪”。主要理由是:
第一,該款規定的行為與開設賭場行為存在明顯不同。這是因為,組織賭博行為既可以是組織開設賭場的一部分或者延伸行為,也可以是聚眾賭博的一種形式,并不當然成立開設賭場罪的共犯或者片面共犯。在此基礎上,不對該款規定的犯罪設置獨立的罪名,可導致部分不符合開設賭場罪的組織跨境賭博行為無法按照開設賭場罪進行追究,也不能對該行為適用賭博罪的法定刑,導致刑法適用的尷尬和錯亂。
第二,即便構成開設賭場的共犯,對該款規定的行為以開設賭場罪規制也可能產生錯誤。這集中體現在開設賭場行為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是合法的,為合法開設的賭場招攬人員(包括組織中國公民參與賭博)可以視為開設賭場的延伸行為。由于開設賭場行為合法,開設行為不能構成犯罪,因此將組織中國公民參與該賭場賭博的從屬性行為認定為開設賭場罪,既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則,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十五)危害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安全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8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8 條是在刑法典第334 條非法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罪后增加一條,作為第334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違反國家有關規定,非法采集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或者非法運送、郵寄、攜帶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出境,危害公眾健康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情節嚴重的”行為。對該條罪名的確定,需要明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該條設立的是一個罪名還是兩個罪名?該條罪狀的基本結構是謂語(“非法采集、非法運送、郵寄、攜帶”)+賓語(“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其中又有兩個組合,分別是“非法采集+國家人類遺傳資源”;“非法運送、郵寄、攜帶+國家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出境”。因此,如果要完整反映該條罪狀的內容,那么需要設置兩個具體的罪名,即“非法采集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罪”和“非法運送、郵寄、攜帶國家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出境罪”。設立兩個罪名的好處是可以準確反映罪狀規定的行為類型,不足之處是為行為的評價和罪數的處理帶來一定困難。例如,行為人先非法采集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后非法攜帶該資源材料出境,其行為可分別構成非法采集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罪和非法攜帶國家人類遺傳資源資料出境罪,且可能因情形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以非法攜帶出境為目的而非法采集的,只定一罪(通常是第一個行為觸犯的罪名,即非法采集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罪);非法采集時沒有非法攜帶出境的目的,但非法采集后產生了非法攜帶出境的目的并實施非法攜帶出境行為的,則要進行數罪并罰。
相比于設立兩個罪名,設立一個罪名則可形成一個統一的做法并解決前述的混亂局面,即無論是非法采集還是非法攜帶,無論非法攜帶出境的目的是形成于非法采集之時還是之后,在設立一個罪名的情況下,都只能對行為人定一罪,更不存在數罪并罰的問題。因此,對該條罪狀設立一個罪名更為合理。
第二,該條罪名的具體確定。在明確了該條宜確定一個罪名的情況下,需要明確具體的罪名確定。如前所述,該條罪狀包括了兩類行為,即“非法采集”和“非法運送、郵寄、攜帶”,這兩類行為的對象和具體表現不完全相同,后者要求“出境”。因此要對這兩類行為進行準確概括,只能尋找更上位的概念,即“危害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安全”。2020 年10 月通過的我國《生物安全法》對危害人類遺傳資源的行為作了明確規定,包括非法采集、保藏、利用、提供、運輸、郵寄、攜帶等系列行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8 條只規定了四類行為,并未涵蓋所有危害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安全的行為,但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罪名的范圍大于罪狀的范圍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因此在目前情況下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危害國家人類遺傳資源安全罪”,更為合適。
(十六)非法植入基因編輯、克隆的胚胎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 條是在刑法典第336 條非法行醫罪和非法進行節育手術罪之后增加一條,作為第336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將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或者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情節嚴重的”行為。該條罪狀的核心結構是謂語“植入胚胎”+賓語“人體或者動物體內”,其行為組合包括三種:一是“將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內”;二是“將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動物體內”;三是“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需要注意,這其中并不包括“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動物體內”的行為類型。基于此,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非法植入基因編輯、克隆的胚胎罪”更為適合。
“兩高”《征求意見稿》將《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 條的罪名擬定為“非法基因編輯、克隆胚胎罪”。?同前注⑤。在筆者看來,對照該條罪狀的規定,該罪名存在兩個明顯問題:一是罪名本身的用詞搭配不合理,“非法”修飾的應該是行為,在語法上,“非法編輯基因、克隆胚胎罪”更符合一般語法;二是罪名與罪狀的行為明顯偏離。《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 條禁止的不是編輯基因、克隆胚胎行為,而是“植入”行為,即“將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或者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從行為的角度看,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非法植入基因編輯、克隆的胚胎罪”顯然更為適當。
(十七)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1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1 條是在刑法典第341 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3 款,該款規定的罪狀是“違反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法規,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第一款規定以外的在野外環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情節嚴重的”行為。對該款規定的罪名問題,需要明確以下兩個具體問題:
第一,該款應否單獨設立罪名問題。“兩高”《征求意見稿》沒有對《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1 條擬定新的罪名,認為可將該款規定的行為納入該條第2 款“非法狩獵罪”的罪名之下。?同前注⑤。不過,在一般概念上,“狩獵”的核心意思是“獵捕”,不能包括獨立的“收購、運輸、出售”行為(即未事先通謀情況下的收購、運輸、出售行為)。從這個角度看,為了更充分反映該條罪狀的行為方式和行為對象,應當對該條規定的罪狀設立單獨的罪名。
第二,該款具體罪名的確定。從罪狀規定的行為結構上看,該款罪狀的基本結構是“非法+目的+行為”。其中,“非法”是“違反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法規”,“目的”是“以食用為目的”,“行為”是“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以外的在野外環境自然生產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從非法性上看,“非法目的”也可納入非法的范疇。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陸生野生動物罪”更為合適(當然,如果想更為簡潔,也可考慮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危害陸生野生動物罪”)。
(十八)破壞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2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2 條是在刑法典第342 條非法占用農耕地罪后增加一條,作為第342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違反自然保護地管理法規,在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開墾、開發活動或者修建建筑物,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行為。從該條內容上看,該條保護的是屬于自然保護地的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行為方式是在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開墾、開發活動或者修建建筑物。因此,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破壞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罪”比較適當。
“兩高”《征求意見稿》將《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2 條的罪名擬定為“破壞自然保護地罪”。?同前注⑤。不過,該罪名針對的對象是自然保護地,但《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2 條的行為對象是“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于“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屬于“自然保護地”的下位概念,因此從準確反映罪狀內容的角度,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破壞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罪”,應該更為合適。
(十九)非法處置外來入侵物種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3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3 條是在刑法典第344 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344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違反國家規定,非法引進、釋放或者丟棄外來入侵物種,情節嚴重的”行為。該條罪狀的核心行為是“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的”行為。因此,從罪名設立的角度看,可以將該條的罪名直接確定為“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罪”。如果要進一步簡化,則可以將“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行為概括為“非法處置外來入侵物種”行為,進而可以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非法處置外來入侵物種罪”。
(二十)妨害興奮劑管理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4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4 條是在刑法典第355 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355 條之一。該條規定的罪狀是“引誘、教唆、欺騙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或者明知運動員參加上述競賽而向其提供興奮劑,情節嚴重的”行為(第1 款),以及“組織、強迫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的”行為(第2 款)。從罪狀的內容看,該條規定了三大類、六小類行為(引誘、教唆、欺騙、提供、組織、強迫)。對于該條罪名的確立需要明確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該條罪名的個數,即該條設置的是一個罪名,還是兩個或者三個罪名?從罪名設立的準確性考慮,要準確反映該條的罪狀內容,可能設置三個罪名較為合適,分別對應三種具體行為類型(即“引誘、教唆、欺騙使用興奮劑”“非法提供興奮劑”和“組織、強迫使用興奮劑”)。但從罪名確立的合理性上看,該條規定的三類行為之間具有很高的關聯性,行為人完全有可能在一個行為整體過程中同時存在這三類行為,如先引誘、教唆,引誘、教唆不成再強迫,并向運動員提供興奮劑,規定三個罪名意味著要求行為人定三個罪名并數罪并罰,會導致罪刑失衡,也將問題復雜化。因此,將該條的罪名確定為一個罪名更為合適。
第二,該條罪名的具體確定。在明確應確定為一個罪名的情況下,要對該條規定的三類行為進行概括,就需要找到這三個行為的共性:一是都與興奮劑有關;二是都是妨害興奮劑管理規定的行為,違反了反興奮劑義務(國務院《反興奮劑條例》第39 條、第40 條明確規定了相關行為的行政處罰)。基于此,可將該條的罪名設定為“妨害興奮劑管理罪”。
(二十一)食品、藥品監管瀆職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5 條)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5 條是對刑法典第408 條之一“食品監管瀆職罪”第1 款作了修改,其規定的罪狀是負有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一)瞞報、謊報食品安全事故、藥品安全事件的;(二)對發現的嚴重食品藥品安全違法行為未按規定查處的;(三)在藥品和特殊食品審批審評過程中,對不符合條件的申請準予許可的;(四)依法應當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不移交的;(五)有其他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行為的。”與刑法典原條文相比,此次修改增加了藥品監管瀆職的內容,故該款罪名在原罪名“食品監管瀆職罪”?刑法理論上對于刑法典原第408 條之一的罪名被確定為“食品監管瀆職罪”存在較大爭議,不少觀點主張將該其罪名一分為二,確定為“食品監管濫用職權罪”和“食品監管玩忽職守罪”。本文對罪名的確立是立足于過往司法解釋,注重保持罪名的延續性,因而對原有罪名的適當性不作探討。的基礎上增加藥品的內容即可,即將該款的罪名確定為“食品、藥品監管瀆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