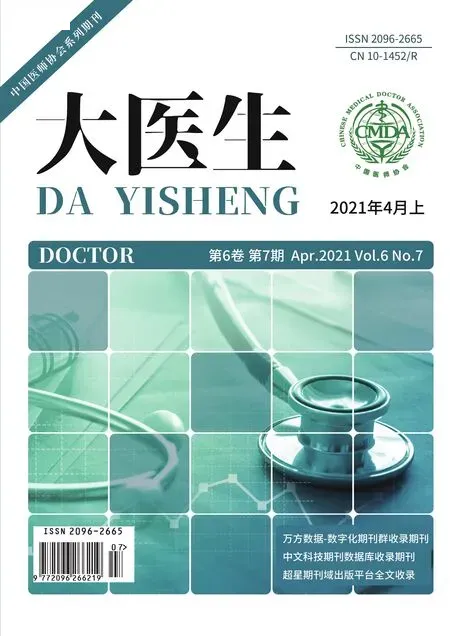腦積水的發病機制與手術治療進展
韋樹德
(廣西醫科大學附屬武鳴醫院神經外科,廣西南寧 530199)
腦積水是腦脊液生成或循環吸收過程發生障礙,導致腦脊液量過多,壓力增高,擴大了正常腦脊液所占有的空間,常伴有顱內壓升高及系列癥狀,會導致腦實質變薄,嚴重損傷患者的神經系統。目前外科手術仍是治療腦積水的重要方法,可調壓分流管、內鏡、神經導航及腹穿置管系統等新技術逐步滲透到臨床應用中,均有利于增強腦積水的手術療效,降低相關并發癥發生風險,并可提升腦積水患者的生存期,從而改善疾病預后[1]。但不同的治療方式均有相應的禁忌證、適應證,并具備各自的優點與不足,本文通過對腦積水不同手術治療方式進行探討,為提高腦積水的臨床療效提供新的思路,現綜述如下。
1 腦積水的發病機制
腦積水具有復雜的發病機制,目前臨床對于腦積水的主要機制是否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等尚未明確。
1.1 炎癥反應 炎癥反應在腦積水的發生中具有關鍵作用,尤其在出血后更為顯著。機體炎癥反應可影響脈絡叢上皮細胞腦脊液的分泌,引起室管膜纖毛發育及功能障礙等介導腦積水的發生[2]。殼多糖酶3樣蛋白1(CHI3L1)是從小膠質細胞與星型膠質細胞中衍生而來的蛋白質,神經炎癥反應與其釋放可能有著一定的聯系性[3]。此外,腦內小膠質細胞屬于腦內常駐免疫細胞,小膠質細胞被激活后主要分成2種相反作用的類型,炎癥微環境改變可能參與了腦積水的發病與進展過程。
1.2 纖維化 纖維化在腦積水發病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可作為腦積水發生后的一種纖維化指標。有臨床研究提出,通過阻滯TGF-β/Smad2/3信號通路可明顯抑制蛛網膜下腔細胞外基質沉積,有助于阻滯蛛網膜下腔纖維化,減輕腦室擴大,有效改善患者腦積水程度[4]。腦室內出血后腦積水可能和腦室系統纖維化存在關系,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屬于TGF-β亞型,多產生于腦組織損傷,同時其可聚積至腦脊液循環通路,大麻素受體2(CB2R)能夠對TGF-β1信號通路起抑制作用,可明顯抑制TGF-β1引起的側腦室擴張,緩解腦室系統纖維化,進一步阻滯腦室出血后腦積水發展。
1.3 水通道蛋白4與水通道蛋白1 腦積水與腦室擴大可引起大腦總含水量的增加。水分子通過水通道蛋白在神經細胞膜上流動,在腦脊液的產生和循環中起到重要作用。水通道蛋白4、水通道蛋白1均和腦積水有著密切聯系,其在中樞神經系統中有著廣泛表達。水通道蛋白1可促進腦脊液的形成,水通道蛋白1在脈絡叢上皮細胞頂側大量表達,當抑制水通道蛋白1時,可有效降低患者機體腦脊液的分泌,抑制腦積水發展[5]。水通道蛋白4是大腦內最豐富的水通道蛋白,其主要存在于室管膜細胞、基底細胞及星形神經膠質細胞足突的表面。水通道蛋白4可作為功能蛋白調節類淋巴系統功能,激活水通道蛋白4可激發腦脊液跨實質吸收,將其表達下調后腦積水程度加劇。因此水通道蛋白可作為臨床診治腦積水的重要靶點。
1.4 基因表達 先天性腦積水的發生主要與遺傳因素有關,腦積水患者親屬的發病風險明顯超過普通人群,現階段已發現部分基因缺陷或突變和腦積水的發生存在相關性,此外室管膜上皮細胞的纖毛能夠激發腦脊液流動,而基因缺陷將引起纖毛功能異常,并導致先天性腦積水[6]。其次,在敲除(基因敲除是用含有一定已知序列的DNA片段與受體細胞基因組中序列相同或相近的基因發生同源重組,整合至受體細胞基因組中并得到表達的一種外源DNA導入技術)水通道蛋白4等基因后,雖然導致先天性腦積水的情況較少,但腦室擴張程度還是存在明顯差異。
1.5 鐵代謝 鐵離子源于紅細胞裂解,其會沉積到腦室壁,廣泛分布在腦中,并會隨著腦脊液的循環擴散至蛛網膜下腔。鐵離子在少突膠質細胞中具有較強濃度,在出血后腦積水中,腦組織中鐵蛋白水平和腦脊液中鐵離子濃度均有所增長,且鐵離子可對Wnt信號通路進行激活,促使蛛網膜下腔纖維化調節,導致腦積水的發生[7]。在腦室內注射血紅蛋白會導致脂質運載蛋白(LCN2)上調,而LCN2是一種參與鐵代謝的蛋白質,上調后引起腦室擴張。去鐵胺能夠對Wntl/Wnt3a信號通路予以阻滯,繼而改善腦室內出血后的慢性腦積水。
1.6 凝血酶 凝血酶是在腦出血后即刻在腦室內產生,腦出血后早期的顱腦損傷有凝血酶的參與。凝血酶會導致腦室擴張和腦室管膜纖毛的嚴重損傷,形成腦積水,乙酰唑胺用于凝血酶誘導的腦積水,可明顯抑制腦積水的進展。
2 腦積水的手術治療
2.1 分流手術 分流手術主要涉及腦室穿刺外引流、腰大池 -?腹腔分流、腦室腹腔(VP)分流術、腦室 -?心房分流等術式。陳楠等[8]提出,在選取分流手術時機方面,主要取決于能否給予早期診斷,患者可否接受和耐受手術等因素,其基于腦室大小分析、患者狀態伴隨時間的變化等各個因素決策。此外,對于預后不良的嚴重創傷性顱腦損傷患者,是否可予以分流手術還需慎重考量,這是由于手術與麻醉作用可能導致患者病情加劇。若預后良好的患者,狀況不斷好轉,才可能考慮采取分流手術,客觀上延遲分流時機。
2.1.1 腰大池?-?腹腔分流 腰大池 -?腹腔分流術最大的優點就是微創,該術式不經顱腦穿刺放置分流管,對顱腦神經的損傷非常小,其皮下分流管長度較短,對患者身體的創傷也是大大降低,且該術式相對簡單,手術的時間與麻醉的時間大大縮短,同時可預防腦室置管致腦出血,降低過度引流風險。李劍等[9]在研究中發現,腰大池 -?腹腔分流術后短期效果和腦室 -?腹腔分流術沒有明顯差異,但感染與堵管的發生風險低于腦室 -?腹腔分流術組,但具體的應用價值還待深入分析。在強化腰大池 -?腹腔分流術療效、控制并發癥方面,袁軼愷等[10]認為必須做好有效的術前評估,通過CT與MRI等術前影像學檢測,及時發現和排查椎管狹窄、小腦扁桃體下疝等對腰大池置管造成影響的相關疾病。另外,在手術開展之前,可借助腰椎穿刺術對顱內壓進行評估,實施腦脊液生化檢查等,作壓頸壓腹測試,觀察蛛網膜下腔的情況,將30~40 mL的腦脊液進行釋放,預估分流作用[11]。另一方面,通過抗生素應用、無菌操作等避免感染的發生,盡可能將手術時間安排至當天的第一臺,預防和其他手術交叉感染。
2.1.2 腦室?-?腹腔分流術 腦室 -?腹腔分流術具有操作方便、適應證廣、療效確切等優勢,因此在臨床中的應用較為廣泛,是治療腦積水的首選手術方式。劉暢等[12]經臨床研究后發現,腦室 -?腹腔分流術組在手術后7 d的日常生活能力(ADL)評分、格拉斯哥預后(GCS)評分均高于腰大池 -?腹腔分流術組;與腰大池 -?腹腔分流術組比較,腦室 -?腹腔分流術組的腫瘤壞死因子 -α (TNF-α)、白介素 -6 (IL-6)水平、改良Rankin量表(mRS)評分降低,白介素 -10 (IL-10)水平升高;此外,腦室 -?腹腔分流術組術后7 d的CD4+、CD3+百分比、CD4+/CD8+比值也高于腰大池 -?腹腔分流術組患者,CD8+百分比低于腰大池腹腔分流術組,提示對創傷性腦損傷腦積水患者予以腦室 -?腹腔分流術治療,有確切的臨床療效,同時可改善T淋巴細胞水平,降低炎癥因子指標。
但值得注意的是,腦室 -?腹腔分流術的失敗率較高,有文獻報道提出,影響手術失敗的因素較多,尤其是發生分流管感染,將進一步促使顱內感染,易產生不良預后[13]。其次,分流裝置阻塞也是多發因素,現階段尚無較好的解決方式,但在多數情況下,可利用針對性方式進行控制,嚴格把握腦室 -?腹腔分流術的適應證,改進標準化操作流程,保持嚴密觀測,及時解決并發癥的發生。此外,要求注重引流裝置的選取,盡可能選有抗老化、抗虹吸可調壓式引流設備,并根據不同患者的實際情況,選用個體化方式治療[14]。
2.1.3 腦室?-?心房分流術 近幾年,腦室 -?心房分流術的治療方式和材料得到一定程度的優化,腦室 -?心房分流術可作為治療難治性腦積水的輔助補救方式。在一項臨床研究中,對腦室 -?心房分流術進行改良,以防止再次行腦室穿刺術,避免患者引發醫源性顱腦損傷,減少麻醉和手術時間,并且能省去了常規術式中的部分環節,但該研究的樣本數較少,有關腦室 -?心房分流術改良的輔助補救效果還待深入分析,且目前腦室 -?心房分流術在臨床中的應用較少[15]。
2.2 神經內鏡手術
近年來,神經內鏡技術、影像技術得到快速發展,伴隨顯微解剖研究逐步深入,神經內鏡手術進一步在臨床中普及。當前神經內鏡手術在治療腦積水中已日趨成熟,臨床效果與傳統單純分流手術比較更為顯著。
2.2.1 三腦室底造瘺術 三腦室底造瘺術是改善梗阻性腦積水的首選途徑,即選取腳間池和三腦室底部之間進行造瘺,促進梗阻的腦脊液經瘺口進至蛛網膜下腔實現循環吸收[16]。三腦室底造瘺術通常適用于梗阻區域于蛛網膜顆粒之前的腦脊液梗阻,有助于對腦脊液通路進行重塑,與生理性腦脊液循環較為相符,可防止出現腦脊液過度引流,且不用置入分流裝置,避免分流術失敗再次置管,并可預防低齡患者由于生長發育需重復換管的痛苦。婁四龍等[17]選取了后顱窩腫瘤并發重度梗阻性腦積水者作為研究對象,其認為在后顱窩腫瘤顯微切除術前同期三腦室底造瘺術中具備的優勢在于其創傷小,在開顱顯微手術前同期進行可以明顯減少住院和手術時間,且三腦室底造瘺術不會置入引流管與分流管等,可降低顱內感染的發生概率。在某項研究中發現,有3例病患在三腦室底造瘺術后的腦積水沒有顯著緩解,術后腦脊液電影示造瘺口的腦脊液流動不佳,后予以腦室-腹腔分流,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術中出血致蛛網膜下腔粘連或是手術前慢性腦積水,引起腦脊液吸收異常[18]。
2.2.2 內鏡下透明隔造瘺術 內鏡下透明隔造瘺術是指經內鏡于透明隔部位造瘺,對梗阻腦脊液進行引流,多用于單側室間孔梗阻誘發的一側側腦室擴大的不對稱性腦積水,若患者的臨床表現輕微或是腦室輕度擴大,則可行隨訪干預,如果癥狀加劇,腦室擴大顯著,中線移位,則需要盡快行手術治療。內鏡下透明隔造瘺術的優勢表現為出血少、創傷小、術后反應輕,并且經內鏡能徹底切除室間孔小腫瘤[19-20]。
3 小結與展望
目前腦積水的發病原因、作用機制等尚未完全明確,伴隨患者年齡、臨床特征等不同,在腦積水的臨床治療上應有所針對性,必須通過完全客觀的評估后制定可行性較高的個體化治療。雖然分流手術、造瘺手術等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但仍然沒有較為理想的手段可以有效縮短引流時間,并可降低感染與其他并發癥的發生風險,如何嚴格把握不同的手術方式的禁忌證、適應證,發揮其特點和優勢是研究學者所面臨的重要挑戰。今后還需對腦積水手術指征、手術時機及手術方式的選擇進行深入分析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