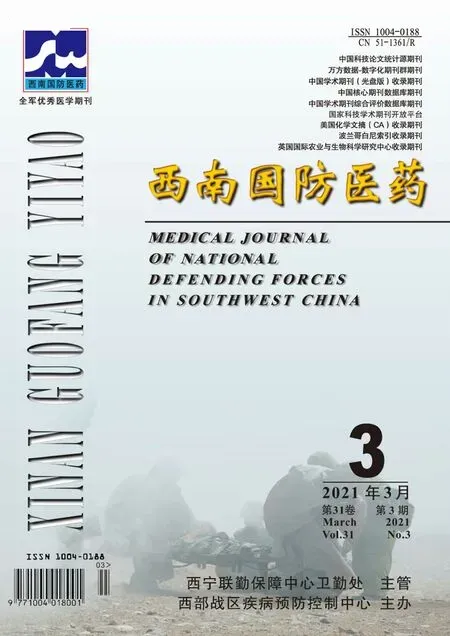鉛的神經毒性研究進展
陳 晨,顧媛媛,李惠子,屈明玥,祝成紅
鉛作為一種常見的重金屬污染物,一般認為在較低濃度時不會引起人體出現癥狀,但積蓄到一定數量水平時會造成多器官功能損傷,尤其是對神經系統的毒性作用尤為突出,其損傷類型通常為不可逆性神經損傷。因此鉛中毒問題始終是公共衛生領域重點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學術界在鉛的神經毒性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故筆者就該領域近10年的新發現、新理論進行了梳理,重點探討鉛中毒導致的認知障礙及相關問題。
1 鉛化合物組分與神經毒性的關系
鉛在自然界中主要以離子的狀態存在,這種存在形式相對于其有機化合物的形態,在人體毒性作用方面要更強一些,因為離子態更容易被人體吸收,而有機化合物的溶解度較小且易分解[1]。
鉛化合物組分的形成,是受鉛所處的環境基質(空氣、食物和水等)作用的影響,在不同的暴露基質會產生各異的化學反應,形成種類繁多的鉛化合物,鉛的組分差異決定著鉛化合物的毒性動力學(鉛物質吸收、分布、儲存和消除等過程)特性,進而影響著其產生的神經行為效應[2]。
有學者設立實驗小鼠對照實驗,實驗組飼料中含40%動物脂肪,水中含300 ppm鉛混合物,對照組設為兩組,一組為普通飼料和水,另一組為普通飼料+含鉛混合物的水,喂養42 d后,利用水迷宮、高架橋等手段檢驗其行為能力,并檢測乙酰膽堿和血鉛濃度與對照組進行比對后發現高脂肪飲食可以增加小鼠大腦中的鉛濃度,促進幼齡小鼠衰老過程,導致記憶障礙、膽堿能功能減退、氧化應激升高和神經退行性變等情況出現,表明營養物質可與鉛發生作用,影響鉛的代謝和毒性效力的產生[3]。
還有國外學者對烏拉圭5~8歲兒童鉛濃度與飲食模式的關系進行研究后發現,攝入含鐵量或維生素C較多的食物與鉛濃度沒有關聯性,且攝入鈣含量高的食品(奶制品)的兒童鉛濃度反而偏低[4]。
有學者使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光譜儀(ICP-OES)測定母乳捐獻庫中106個樣本鉛、砷、鎘、錳等離子的濃度,結合樣本提供者職業特點、生活習慣、所處環境等因素分析,發現產婦的胎次數量和每日鈣攝入量,以及母乳喂養狀況都會對產婦血液和母乳中的鉛濃度產生影響,母乳中鉛濃度反映的是當前人體所處的鉛暴露水平,而鉛在骨中的分布則取決于既往鉛暴露積累的情況[5]。
不同的鉛化合物組成成分(硫化鉛、硫酸鉛、氧化鉛和碳酸鉛等),其鉛的吸收效率是有區別的。鉛化物的溶解度和溶解速率的高低取決于其pH值、顆粒大小和它們的溶解動力學等因素,例如,大腦中鉛的攝取與HCO-濃度成正比,與H+濃度成反比,因此鉛所處的環境基質與鉛的神經毒性作用關系十分緊密[6]。
2 鉛濃度與神經毒性的關系
大腦的發育包括細胞分裂、遷移、突觸形成、中斷、修剪、髓鞘形成、神經元遷移、神經膠質相互作用等過程,鉛作為一種神經毒物,會在上述神經發育的過程中抑制大腦的發育[7]。人體鉛暴露程度的測量方法,主要是采用X射線熒光光譜法(對脛骨和髕骨的骨皮質和骨小梁處進行測量)進行測量的[8]。骨中鉛的生物半排期因年齡、部位、暴露狀態和其他影響骨代謝的因素不同而有所區別。據報道,骨小梁生物半排期為8~20年,而骨皮質內的生物半排期為10~50年。而鉛暴露的程度水平的呈現方式,往往是通過血液和骨骼中的鉛濃度來呈現的,并且鉛濃度與神經毒性的表現呈正相關[9]。
當血鉛濃度≥60μg/dl時,人體會有明顯的神經毒性表現,因此一般認為人體承受的最大血鉛濃度為40μg/dl。即使血鉛濃度在20~40μg/dl時,人體也會出現與血鉛濃度有關的認知狀態改變,因此,現在世界衛生組織對人們的建議是,血鉛濃度要控制在10μg/dl以下。但也有報道即使血鉛濃度在10μg/dl以下,人體也會出現輕微神經反應[10]。
為了確定這種低鉛水平對人群的影響,有學者采用韋氏兒童智力量表(WISC)和康納斯-韋爾斯青少年自我報告量表(CASS:L)分別評定了299名11~14歲的青少年(49.2%為女性)的認知和行為能力。他們的平均血鉛濃度為1.71μg/dl,平均智商為106.3(言語智商=102,表現智商=109.3)。根據多元回歸模型(已考慮其他變量影響)得到結果是,血鉛濃度增加兩倍會導致智商降低2.4左右。這些結果表明,極低水平的鉛暴露對青少年的認知功能有顯著的負面影響[11]。
此外,有學者還分析了240萬名1~21歲人群的血鉛濃度與個人健康的關系,得到結果是,有91.7%的被調查者的血液中檢測到鉛,各年齡血鉛濃度范圍為1.02μg/dl~2.88μg/dl,有相當一部分兒童即使鉛暴露低于10μg/dl,卻面臨者不良健康影響的風險,可見鉛濃度對神經毒性的閾值水平評判應更為謹慎[12]。
3 鉛的神經毒性與人體認知障礙的關系
鉛的職業環境暴露與人體認知障礙密切相關。有項研究是通過核磁共振成像(MRI)技術探討長期暴露于鉛職業環境中工人的大腦結構和功能是否發生了改變。該研究將15名鉛接觸者分為暴露組,19名健康志愿者分為對照組,鉛暴露組和對照組的平均血鉛濃度分別為63.5μg/dl和8.7μg/dl。MRI檢查顯示暴露組的大腦海馬體積顯著減少(P<0.01),而且,這些鉛暴露者即使離開從事鉛行業后的約20年時間里,鉛對其大腦的損傷仍然存在,其損傷特征是腦組織蛋白受損,以及較大(如全腦、葉狀灰質和白質)和較小(如扣帶回、島葉、胼胝體)的大腦組織區域體積有所減小,此時腦組織的主要代謝物含量也會發生相應改變[13]。
在流行病學橫斷面調查中,鉛職業暴露也與學習、記憶和復雜認知功能關系密切,會產生如反應遲緩、視覺運動障礙、言語記憶缺失和靈活性降低等方面的問題,常伴有認知障礙和共濟失調、震顫和深部反射異常、運動強度減少等運動行為方面的異常表現[14]。國外學者對美國馬里蘭州50~70歲的城鎮老人進行了一項血鉛濃度調查,其中發現骨鉛濃度(脛骨中的鉛濃度)與認知功能顯著相關,特別是與視覺構建能力的關聯性最強[15]。隨著骨鉛濃度增加,認知功能會逐漸降低,尤其是在視覺空間運動測試中,認知功能下降與視覺反應時間長短呈正相關[7,16]。
4 鉛的神經毒性與嬰幼兒神經發育的關系
鉛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因多種原因而影響嬰幼兒的神經發育。有學者采集了重金屬濃度較高地區和重金屬濃度較低地區的新生兒臍帶血,并對其DNA全長進行高通量測序發現,重金屬濃度較高地區的新生兒有79個基因中的125個位點存在甲基化差異,臍帶血中鉛濃度也較高。推測嬰兒早在其母親懷孕或哺乳期間就已經接觸鉛化物了,由此引發嬰兒大腦神經元DNA甲基化,進而會影響孩子大腦發育[17]。還有學者通過研究1301份嬰幼兒糞便以尋找重金屬、有機氯、有機磷等污染物線索,最終在41份樣本中發現污染標記物,同時比較了樣本對應的產婦教育、就業狀況和家庭富裕程度等社會經濟因素后發現,孕婦懷孕期間的污染物暴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會影響胚胎組織發育[18]。此外,鉛環境暴露也可能與其他危險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疊加效應,如產婦腹腔壓力增加,使骨骼中的鉛釋放到血液中,可增加胎兒鉛接觸量,從而對胎兒神經發育產生負面影響[19-20]。
由此可見,較高的血鉛濃度是嬰幼兒神經系統發生缺陷的重要因素,在出生之前,鉛已經可以通過單獨或聯合作用的方式對孩子后期的認知行為功能產生負面影響[21]。鉛暴露會引起兒童一氧化氮合酶的改變,從而改變大腦的血管系統,進而影響血清素系統和血清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水平,這些變化會增強兒童的攻擊性行為[22-23]。
5 鉛的神經毒性與阿爾茲海默病的關系
通過調查大量阿爾茨海默病病例表明,環境因素可能是誘發阿爾茨海默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阿爾茨海默病的顯著病理特征是淀粉樣蛋白斑塊,此特征在正常老年人群體中也同樣出現,這一現象提示阿爾茨海默病可能是由大腦中正常的與年齡相關的組織蛋白加速衰減引起的一種疾病,加速這些組織蛋白在腦部以淀粉樣形式積聚的分子,也許在大腦發育的早期階段就已經形成了[24]。
科學家通過對209例因阿爾茲海默病去世的患者進行的尸檢,驗證了腦部淀粉樣斑塊這一病理特征與阿爾茲海默病的關系,并指出鉛暴露可能作為一種生理加速劑,加速這一病理特征出現,導致人的認知能力下降[25]。
運用核磁共振技術對30名鉛行業從業人員進行檢查后發現,他們的腦部出現了與阿爾茲海默病患者一樣的海馬區-乙酰天冬氨酸(NAA)顯著下降這一現象,再次顯示了鉛與阿爾茲海默病關系密切。海馬區-乙酰天冬氨酸的降低與神經元損傷或神經軸突結構變性關系密切,這些神經結構的改變,又與包括阿爾茲海默病在內的許多神經退行性疾病相關[26]。
種種臨床病例研究結果顯示,鉛參與了阿爾茲海默病的病理改變,鉛暴露增加了阿爾茨海默病的罹患率,但鉛暴露在阿爾茨海默病或其他神經退行性疾病發病機制中發揮的具體作用還未完全明了。
6 小結
在橫向和縱向研究中,鉛暴露與人類認知功能障礙相關。盡管隨著汽油改為無鉛汽油,很多地區的血鉛水平大幅下降,但暴露水平升高仍然是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特別是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和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慢性鉛神經毒性仍然是一個很大的世界性問題。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仍然有大量與鉛長期接觸的工人,人們對鉛導致的認知障礙等后遺癥的重視程度還需增強,鉛中毒的分子機制及防治手段仍需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