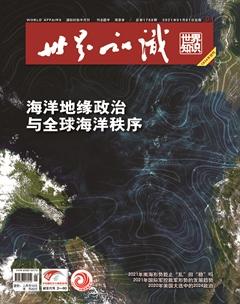地緣政治視角下公海保護區的發展與演變
鄭苗壯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之間的關系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領土擴張和勢力范圍爭奪,轉向合作構建伙伴關系,謀求共同安全、發展和繁榮。當前,大陸塑造和影響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海洋國際規則不斷演化。拓展于己有利的海洋空間是各國海洋競爭的核心,對塑造海洋地緣政治格局的作用尤為重要。
公海占全球表面積的64%,是人類發展的新空間、國家安全的新戰場和各國競相拓展的戰略新疆域。各國圍繞公海保護區在政治、外交和法律等領域全面展開角逐,形成國家管轄海域外生物多樣性(以下簡稱“BBNJ”)國際協定談判、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海洋目標和南極公海保護區相互關聯的態勢。一旦出現顛覆性改變,則會呈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公海保護區將短時間內在全球快速布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重構了世界海洋政治邊界
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至80年代早期,美英法等前殖民帝國控制的殖民地陸續獨立,但仍有一些偏遠小島嶼受美英法等的托管或控制。隨著全球人口膨脹、海洋科技進步、自然資源的消耗速度加快,海洋在國家發展和安全利益以及在國際政治、軍事和科技競爭中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建立的專屬經濟區制度和大陸架制度,“變革性”地改變了世界海洋的政治邊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將12海里的領海向外延伸至200海里,大陸架甚至可拓展至200海里以外更遠的區域。
《公約》規定特定島嶼和陸地享有同等權利,據此,美英法等前殖民帝國占據的偏遠島嶼以及托管的非自治領土可合法管控的海域得到大幅擴張。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七個國家擁有的專屬經濟區總面積達到4500萬平方公里,其中約70%(3200萬平方公里)是依托散布在遠離大陸、地處偏遠海域的島嶼和海外領地獲得的,美英法海外專屬經濟區的面積遠遠超過其本土的專屬經濟區。這些海外島嶼地處邊緣地帶,扼守途經三大洋的海上通道要道,在地緣政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美國奉行“離岸平衡”戰略,英國和日本則充當圍堵陸權國家最為重要的離岸平衡手角色。尤其在印太方向,美國所依賴的正是夏威夷群島、關島、琉球群島和英屬查戈斯群島等偏遠島嶼。美國在這些島嶼部署了其在印太地區最為關鍵的海空軍事基地,作為實施軍事力量投射布局的重要支點,用來扼守全球地緣政治中最為重要的邊緣地帶,憑借強大的海上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對陸權國家形成戰略包圍態勢。
歐美國家以建設海洋保護區為由變相加強并拓展其在管轄海域的權利
《公約》為規范人類海洋活動提供了法律框架,最大限度地平衡沿海國和內陸國、地理條件優越國和不利國的海洋利益分配,賦予各國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享有不同的權利。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對自然資源擁有主權權利以及保護海洋環境、建造人工設施和開展科學研究的管轄權,而其他國家則保留了船舶航行、漁業捕撈、海洋科學研究、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等權利。歐美國家在新時期為加強對邊緣島嶼及其管轄海域的控制,依據《公約》規定的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內擁有海洋環境保護的管轄權,引領并掀起海洋保護區的建設浪潮。
當前,歐美國家及其控制的小島嶼國家共建立近40個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大型海洋保護區,約占全球海洋面積的5.5%、保護區面積的72%。這些大型海洋保護區大多是在2006年美國建成西北夏威夷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之后建立的,分布在遠離大陸、人類經濟社會活動密度較低的偏遠島嶼周邊海域,普遍采取禁止捕撈、采礦和鋪設海底電纜等管理措施,嚴格管控船舶航行和海洋科研活動。歐美國家以建設海洋保護區為由,變相加強并拓展其在管轄海域的權利,在加強對海洋控制的同時,排斥其他國家進行根據《公約》規定可開展的海洋活動。
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海洋保護區是養護生物多樣性、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2002年聯合國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峰會提出“到2012年建立具有代表性的海洋保護區網絡”,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通過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要求到2020年保護10%的海洋,歐盟以及英國聯合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帕勞等小島嶼國家組建“高雄心”聯盟,呼吁定于2021年在我國昆明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設立“到2030年保護全球30%海洋,其中10%禁止一切海洋活動”的目標。
1970年全球僅有27個國家建立了118個海洋保護區,2000年全球海洋保護區面積約為200萬平方公里。至2020年11月底,全球已建立17000多個海洋保護區,面積超過2700萬平方公里,占全球海洋面積的7.9%。其中,美國是最為強大的海權國家,前總統奧巴馬以美國歷史上首位太平洋總統自居,在夏威夷和關島等太平洋偏遠島嶼地區建立了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的保護區,進一步加強了對太平洋地區的控制。歐盟圍繞海外領地實施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計劃(BEST),加緊拉攏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島國,以海洋保護區強化對加勒比海、南太平洋、中南印度洋、南大西洋、亞馬遜(法屬圭亞那區域)、馬卡羅尼西亞、極地和亞極地等七個重點海域的控制。
2020年5月,歐盟委員會發布《歐盟203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讓自然重回我們的生活》,把制定“3030目標”(30年保護30%的海洋)、BBNJ國際協定及通過歐盟提出的南極威德爾海和東南極公海保護區提案作為重要議題。同年12月,歐盟委員會發布《全球變局下的歐美新議程》,謀劃與美國在跨大西洋和全球范圍內,構建其共同引領的國際海洋治理新秩序,其中把“3030目標”和南極公海保護區作為優先事項。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包括海洋保護區在內的環保議題上立場有所倒退,2020年11月,拜登新政府提名力推南極羅斯海公海保護區建設的前國務卿克里為氣候變化事務特使,不排除未來與歐盟“合流”、將海洋保護區由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向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拓展的可能。
公海保護區制度將深刻改變國際海洋秩序
200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59/24決議,決定在《公約》框架下就公海保護區在內的BBNJ問題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定,當前正就該協定的案文條款進行政府間磋商。部分地理有利國提出在毗鄰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以外的區域(以下簡稱“毗鄰區域”)建立公海保護區時,它們擁有選劃公海保護區的優先權、保護區提案協商和決策的否決權并由其實施管理,排斥其他國家在“毗鄰區域”開展活動,預謀將管控范圍繼續向管轄外海域拓展。
歐美國家以及小島嶼國家提出,公海保護區是長期存在的,一旦建立則永久存在。發達國家又不愿承擔保護區管理和監測等方面的資金和資源投入,建而不管導致選劃和管理脫節,使保護區難以撤銷或動態調整。歐美發達國家在海洋保護區建設方面處于絕對優勢,若按其利益快速全球布局,會進一步鞏固并固化其主導的國際海洋治理格局。
歐美國家從未放緩對海洋的控制,把保護區作為新時期鞏固其主導世界海洋秩序、遏制新興國家的重要工具。歐美國家掌控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及其話語權,海洋保護區建設和管理經驗豐富,在公海保護區建設的國際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自本世紀初開始,歐盟以及美國、日本等國在全球重點海域組織實施了國際海洋生物普查十年計劃、“地平線2020”和歐洲地平線等調查計劃,獲得大量重要海洋物種的分布范圍和洄游通道的一手資料。

2016年10月28日,來自24個國家和地區以及歐盟的代表共同簽署一份協定,一致同意在南極羅斯海域設立首個海洋保護區。圖片為拍攝于2016年11月12日的南極羅斯海域。
此外,已基本確定在BBNJ協定下新建管理組織。歐盟和非洲集團還提出新建的這一管理組織,凌駕于其他國際組織之上,即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海底管理局和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等國際組織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必須執行新建管理組織所定的各項措施。這將對現有國際海洋治理框架和治理體系產生極大沖擊。
BBNJ協定一旦通過,歐美國家即可憑借占據海外小島嶼的地理區位、擁有的數據資料、具備的較強監測監督能力等優勢,率先從符合其利益的角度選劃公海保護區,以合法化方式達到對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的實際管理效果,發揮事實上的“管理者”作用,并排斥其他國家的利用或管理。這樣就可以將“自由開放的公海、勘探開發資源的國際海底區域”轉變為“約束海洋活動的保護區”,變相改變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的性質,使之成為歐美國家主導圈定的“緩沖區”或“軟屏障”,從而進一步固化其主導的世界海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