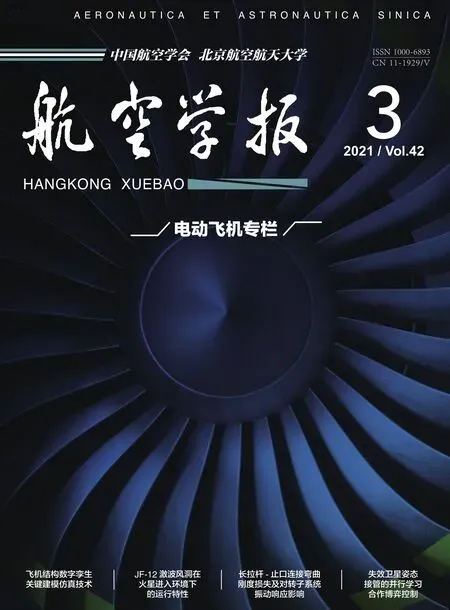基于翼面壓力的飛行器氣動力感知技術與自由飛驗證
陳尹,顧蘊松,*,孫之駿,黃紫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航空宇航學院,南京 210016 2. 沈陽飛機設計研究所揚州協同創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揚州 225002
飛行器在大迎角狀態下,其表面附著與分離、旋渦生成與破裂、非對稱渦的產生等復雜流動會產生難以預測的非定常氣動力,導致諸如抖振、機翼搖滾、航向發散等非指令飛行運動出現。非指令運動會隨飛行器的布局形式、來流條件、飛行工況的變化而呈現各不相同的運動方式,這種隨機特性嚴重影響了飛行器的操控性能[1]。
Nelson和Pelletier[2]就非指令運動現象指出:“飛機在早期設計階段無法預測這些現象的起始與嚴重程度,大部分的非指令運動現象往往需要在試飛階段才能發現。”美國“超級大黃蜂”F/A-18 E/F機型就曾在試飛階段出現非指令性的機翼搖滾(Wing Rock)和掉翼(Wing Drop)現象,這使得飛行員無法在跨聲速飛行包線中實現穩定盤旋與精確跟蹤。為此,美國NASA與NAVAIR通過AWS(Abrupt Wing Stall)項目[3-5],歷時5年提出了跨聲速FTR(Free-To-Roll)試驗技術[6],并改進了非線性現象的模擬方法,解決了F/A-18 E/F機型這一非指令滾轉運動問題。但遺憾的是,AWS項目僅能為飛機構型提供橫向飛行品質的評估,仍無法幫助設計單位在飛機早期設計階段避免該問題的發生。在國內,鄧學鎣團隊[7-9]提出了以人工微擾動為主的抑制大迎角機頭偏離和機翼搖滾等非指令運動的控制技術,并指出:針對非指令運動問題,“應充分研究所設計布局的大迎角流動形態及其相應的非指令運動的形態”[1]。
飛行器繞流的狀態決定了其受到的氣動力/力矩,進而決定了其運動狀態。如何通過飛行器在大迎角狀態下的流動狀態精準推算其受力狀態,并正確預測甚至控制非定常氣動力對飛行器運動趨勢的影響,將是未來戰斗機設計中亟待解決的空氣動力學和飛行控制的關鍵問題之一。
現有的飛行器飛控系統多依賴于慣性傳感器,以慣性元件為核心的機載設備無法直接提供大迎角復雜流動產生的非定常氣動力參數。故在大迎角狀態下,傳統飛控設備只能在飛行器對非定常氣動力做出慣性響應后才能檢測到慣性傳感器的輸出信號,這種測量和控制方式其系統響應存在固有的時滯[10]。Mohamed等[11]通過實驗發現,基于慣性傳感器的MAVs(Micro Air Vehicles)對陣風擾動的滾轉響應時滯大于0.52 s。為此,也有學者嘗試利用表面壓力數據對飛行器進行氣動載荷的預測,Burelle[12]和Thompson[13]等分別利用展向與弦向陣列式的壓力數據分別實現了特定小迎角下三角翼的升阻力預測和俯仰力矩預測;Provost等[14]利用散布式的壓力數據也實現了特定小迎角下,UCAS(Unmanned Combat Air System)機翼滾轉力矩的實時預測。可見,通過稀疏的表面壓力數據可以很好地預測小迎角條件下模型氣動力分量,但大迎角強分離和復雜多渦系條件下的氣動力分量預測的研究工作仍需要進一步開展。
由圖1可見,典型雙三角翼背風區特征截面的壓力分布對應了表面流動結構,并且能夠反映空間多渦系信息[15]。表面壓力分布曲線可以很好地捕捉模型在大迎角下產生的非對稱渦系結構,進而為大迎角下非線性渦升力的預測提供了可能性。本文開展利用有限的表面壓力數據信息對飛行器進行氣動力感知研究,提出通過特征截面滾轉力矩系數Clsec推算飛行器在大迎角狀態下的非定常滾轉力矩,進而基于此判斷飛行器的滾轉運動。本文選擇了80°/48°雙三角翼平板模型,對不同迎角下穩態、動態條件下進行了風洞試驗,利用NI數據采集系統實現了模型翼面壓力與氣動力/力矩的同步測量,研究了模型背風區處特征截面的翼面壓力數據與模型整體滾轉力矩的對應關系,并對此進行了非定常擾動下的風洞試驗驗證;其次設計并形成嵌入式翼面壓力測量裝置,可以實現翼面壓力存儲和信號的無線收發;在風洞模型試驗數據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減少測壓孔數量,設計制作了搭載該系統的無人試飛模型驗證機,選擇飛行器大迎角平飛這一典型飛行動作,驗證在模型自由飛試驗中利用Clsec進行飛行器滾轉運動趨勢預測的可行性。

圖1 76°/40°雙三角翼壓力分布與渦量云圖 (α=30°,Re=4×104)[15]Fig.1 Pressure distributions and vorticity of 76°/40°double delta wing(α=30°,Re=4×104)[15]
1 系統與設備
1.1 風洞與模型
風洞試驗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空氣動力學系1 m非定常回流低速風洞進行,來流風速v∞=15 m/s(Re=4.0×105),試驗迎角范圍為0°~50°,步進2°。試驗整體布置如圖2所示。
模型選用80°/48°雙三角翼,弦長c為425 mm,厚D=9.5 mm,頭部為80°后掠的三角翼,主翼為48°后掠三角翼,主翼展長b為480 mm,參考面積S為0.09 m2,前緣采用45°的尖形倒角設計,材料為光敏樹脂。模型還在80%全長處設計了展向測壓帶,孔徑為1.2 mm,測壓帶孔數為32個,根據展長以0.05b的間距均勻分布。模型其X軸沿弦向指向機頭、正對來流,Y軸方向指向模型右弦為正,Z軸方向法向垂直于模型表面,指向迎風區為正。

圖2 風洞試驗布局Fig.2 Experimental setup
1.2 風洞試驗設備
為準確獲得雙三角翼滾轉力矩變化,采用滾轉力矩量程較小的五分量桿式天平進行測力實驗,天平技術參數見表1。
模型連接桿式天平,并通過尾撐以側裝的方式,架設到三維模型姿態控制機構上,實現其俯仰、偏航和滾轉的靜態姿態控制,見圖2。天平與模型同軸安裝,以右手準則確定滾轉力矩Mx方向,即如圖3所示順時針為正。
天平在不同工況產生的微電壓信號經放大器放大后,通過16位采集板卡進行采集,天平數據采集最大速率為2 kHz。
表面壓力測量系統為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飛行測控創新實驗室自主研制,該系統其壓力量程為0.15 PSI(約1 034.2 Pa),壓力測試精度為0.05% FS,最大設計采樣率為2 kHz。

表1 五分量天平Table 1 Five-component internal force balance

圖3 80°/48°雙三角翼模型Fig.3 80°/48°double delta wing model
依托NI數據采集系統可將表面壓力測量系統和測力天平系統進行集成,實現了壓力與氣動力/力矩的同步測量。
1.3 飛行驗證模型與設備
本文設計并制作了無人試飛驗證機和嵌入式翼面壓力測量裝置,以驗證風洞試驗研究結果。
1.3.1 無人試飛驗證機
為便于置放測壓裝置及增加試飛模型在實際飛行過程中的穩定性,無人試飛驗證機在不改變風洞雙三角翼平板模型背風區復雜多渦系這一特性的前提下,整體根據風洞平板雙三角翼模型,采用帶中心體的雙三角翼雙垂尾布局。主翼最大翼展為960 mm,模型采用了PU發泡塑料材料,并在機艙、機翼內部鋪設了碳纖維支桿以保證強度,整機如圖4所示。其他全機特征參數如表2所示。
根據風洞試驗研究結果,試飛模型在x/c=0.8截面(以下簡稱0.8c)處的測壓孔數量減少至18個。

圖4 無人試飛驗證機Fig.4 Unmanned flight test aircraft
飛機頭部設有五孔球頭探針,其直徑為8 mm,探針外伸200 mm;翼面測壓帶位于模型上表面的0.8c截面處,測壓孔在左右翼面均勻分布,共18個。嵌入式翼面壓力測量裝置安置于機艙內,并通過外徑1.2 mm、長約500 mm的氣路軟管與測壓帶進行連接,氣路軟管固定在機翼下表面,從機腹通向機艙,其管損延遲(含傳感器響應)為60 ms。

表2 試飛驗證機全機參數Table 2 Parameters of flight test aircraft
1.3.2 嵌入式翼面壓力測量裝置
為實現飛行器基于壓力數據的氣動力感知功能,設計了微型化、集成化的嵌入式機載多通道翼面壓力測量裝置。該裝置具備以下功能:24通道壓力測量、壓力數據的存儲及傳輸、無線控制信號的收發。主要參數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嵌入式翼面壓力測量裝置主要參數

表4 壓力傳感器主要參數Table 4 Specifications of pressure sensors
2 試驗結果與分析
2.1 模型表面壓力與氣動力/力矩對應關系分析
細長三角翼背渦存在“尾部占優”的特征[16-17],即尾部截面滾轉力矩占據了三角翼滾轉力矩的主要部分,而截面滾轉力矩由三角翼尾部附體渦對的流動形態決定。并且,利用不同截面處的展向翼面壓力分析流動結構特征這一研究方法也一直應用在細長三角翼流動機理研究中[18-24]。
基于以上研究基礎,本文選擇80°/48°雙三角翼平板模型,探究模型表面壓力與氣動力/力矩的對應關系。
首先對80°/48°雙三角翼模型在來流風速v∞=15 m/s(Re=4.0×105)進行了不同迎角情況的氣動力和翼面壓力數據同步采集。0.8c截面的各測點壓力系數Cp通過10次測量結果進行平均,計算公式為
(1)
式中:ptap為測壓孔壓力;p∞和q∞分別為來流靜壓和動壓。
模型整機滾轉力矩為
(2)
0.8c截面處的滾轉力矩系數Clsec利用式(3)進行壓力積分
(3)
式中:Mx為天平測得的模型滾轉力矩;b和bsec分別為模型最大展長與截面展長;S為參考面積;Cp為特征截面測點壓力系數。
為適應自由飛驗證及后續飛行測量,試飛驗證機模型上的測壓裝置存在一系列的限制,如測壓孔位置、機翼強度、管路排布、傳感器體積與數量等,故應對模型特征截面處的測壓數據進行壓縮,使其可以根據盡可能少的測壓數據實現整機滾轉力矩的最優化重構。為此,將積分的測壓孔孔數從32孔分別均勻減少至16孔和8孔,獲得不同壓力積分曲線,與天平數據進行相關性對比與分析,獲得合適的測壓孔間距。
2.1.1 模型各靜態迎角下Clsec與Cl對應關系分析
得到模型各靜態迎角下的截面滾轉力矩系數Clsec和天平測得的滾轉力矩系數Cl對比曲線,并進行7次重復性實驗,結果平均后如圖5所示。
對比Clsec與Cl曲線,雖然僅利用0.8c截面的Clsec無法準確反應模型整體Cl的精確值,但在迎角0°~50°范圍內,Clsec和Cl的變化趨勢一致。對于不同測壓孔數量積分的Clsec,可以發現由8個測壓孔積分而得的Clsec曲線,在迎角0°~10°范圍內波動較大,其他范圍內與32孔、16孔積分的Clsec曲線變化基本一致。故對于80°/48°雙三角翼,在迎角0°~50°范圍內,0.8c特征截面壓力分布與機體受力存在強相關性,可以判斷該模型Cl變化趨勢。

圖5 不同靜態迎角下平均Clsec與Cl曲線Fig.5 Mean Clsec and mean Clvs different static α
2.1.2 動態變迎角下Clsec與Cl對應關系分析
以上都是在給定靜態迎角下測得的相關特征截面滾轉力矩系數和模型整體滾轉力矩系數Cl平均數據。為模擬飛行器姿態變化這一動態過程中,0.8c截面作為特征截面,其Clsec能否正確判斷模型整體滾轉力矩的變化趨勢。同步記錄雙三角翼模型從迎角穩定、變化、再穩定這一動態過程的天平信號和翼面壓力信號,利用Pearson相關系數R(見式(4)),對比分析32個測壓孔積分的Clsec和Cl曲線變化趨勢的相關性,見圖6。
R=

(4)


圖6 動態變迎角下的Clsec與Cl實時曲線Fig.6 Clsec and Cl vs dynamic changing α
對比不同數量測壓孔積分的Clsec曲線與Cl的相關系數,如表5所示。
在迎角大于20°后,各過程其相關系數R均大于0.85,兩條曲線表現出了高度相關性。對于迎角α從20°~10°這一過程,由8孔積分的Clsec曲線其相關性表現較差為0.629 0,與其他孔數積分差異較大。對于80°/48°雙三角翼模型,由16孔以上(測壓孔間距<0.1b)積分的Clsec曲線在各迎角范圍內其相關系數表現較好。

表5 不同壓力積分曲線相關系數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Clsec
2.1.3 非定常擾動下Clsec與Cl對應關系分析
飛行器在陣風等非定常擾動情況下,其流場中旋渦會發生如破裂、移動等現象。為模擬該復雜來流飛行條件,設置模型迎角為15°,側滑角為0°,并從風洞外部在模型上游處伸入擾動棒以約為0.3 Hz的頻率左右交替干擾模型兩側,如圖7所示。

圖7 模擬非定常擾動示意Fig.7 Simulation of model unsteady disturbances
這種非定常擾動會干擾背風區兩側旋渦渦系,使作用在左右翼面上的渦升力交替增減,進而導致模型整體氣動力/力矩發生相應變化。

圖8 非定常擾動下的Clsec與Cl實時曲線Fig.8 Clsec and Cl with unsteady disturbances
圖8為擾動過程中天平測得的滾轉力矩與通過測壓獲得的截面滾轉力矩系數同步信號對比,包括天平測得的模型Cl曲線(簡稱“天平”)和不同測壓孔數量積分的Clsec曲線(簡稱“測壓”)。
圖8表明,天平力矩曲線隨擾動棒的左右交替移動而表現出正負變化,說明擾動棒的確影響了模型背風區流動結構,進而使模型左右翼面上的受力發生相應變化。
分析不同數量測壓孔積分而得的Clsec曲線與Cl曲線相關性,其R分別為0.885 7(32孔)、0.855 7(16孔)、0.780 7(8孔),可見兩條曲線的相關性隨測壓孔數量的減少而下降。
利用Pearson相關系數計算兩條信號曲線的時延(圖8(a)),0.8c截面Clsec曲線(32孔)與天平Cl信號曲線表現基本一致,Clsec曲線較Cl曲線遲滯約0.01 s,此時的相關性系數最大,為0.892 4,呈高度相關。

圖9 Clsec與Cl的時滯和功率譜密度分析Fig.9 Time lag and PSD between Clsec and Cl
對其進行時滯和功率譜密度分析,如圖9所示。圖9(b)中兩條曲線其頻率分布一致,天平信號和測壓擬合信號所測得的頻率與擾動棒干擾頻率一致。可見,在迎角α=15°時,0.8c截面Clsec仍能夠正確反應模型左右側旋渦受非定常擾動時天平輸出力矩值的變化情況。
根據以上試驗結果,0.8c截面的確能夠作為80°/48°雙三角翼模型的特征截面,來判斷模型整體額外滾轉力矩的變化情況。通過設置間距不大于0.1b的測壓孔,該截面展向壓力積分得到的截面滾轉力矩系數能夠穩定地在穩態、動態變迎角條件下,基本反映出利用桿式天平測得的模型整體非定常滾轉力矩,并能在非定常擾動情況下反映滾轉力矩值的變化。
2.2 試飛驗證數據分析
如圖10所示,當飛行器處于大迎角狀態時,其背風區的旋渦作用會導致翼面壓力分布的不一致性,進而產生非定常氣動力,施加在機翼上的力矩使得飛行器本身產生了滾轉角加速度,最終產生滾轉角。受制于慣性元器件測量特性,陀螺儀和加速度計只能對角速度和角度進行測量,而兩者分別與角加速度間存在一階和二階時滯。這種時滯還會影響到氣動力模型的準確性。因此,傳統方法通過慣性元器件所測運動歷程預測飛行器受力狀況,往往存在控制延滯、過調、發散的風險。

圖10 非指令滾轉運動歷程Fig.10 Sequence of uncommanded motions
利用基于表面壓力的Clsec這一參數,有望克服傳統的基于慣性傳感器的控制方法其固有時滯。為驗證該設想在模型自由飛試驗中進行飛行器氣動力矩感知和運動趨勢判斷的可行性,設計并制作了相關試飛模型,并在航模上表面的0.8c截面處進一步減少測壓孔孔數至18處。
試飛模型進行了一段大迎角平飛狀態的飛行,并出現了非指令滾轉運動。圖11是模型進行自由飛試驗驗證中大迎角平飛階段所記錄的飛行數據,在該階段,飛行器發生了非指令性的滾轉運動,該階段飛行空速v為5~7 m/s。試驗現場氣溫為31.5 ℃,大氣壓為100.437 kPa,場地處于微風狀態。

圖11 自由飛試驗飛行數據Fig.11 Flight log of free flight test
將實時翼面壓力數據根據式(3)計算出截面滾轉力矩系數Clsec,并與迎角曲線進行對比,如圖12所示。
根據圖12,試飛模型僅在筋斗過程和大迎角平飛階段出現了較大的滾轉力矩系數波動,此時模型迎角均大于30°。而在其他飛行階段其截面滾轉力矩系數值均不大于0.5。
圖13為實時同步的截面滾轉力矩系數曲線與滾轉角曲線。當Clsec增幅超過0.5時,模型開始順時針滾轉;Clsec減幅超過-1時,模型開始逆時針滾轉。經過峰峰值對比,截面滾轉力矩系數Clsec能夠比慣性器件提前約200~700 ms預測模型滾轉運動的變化趨勢。模型慣性元器件所測得的數據隨飛行工況的復雜變化及各階段的數據處理形式而產生不同的時滯。在實際飛行中,手動操控難以保證試飛模型在復雜工況下的大迎角穩定飛行,因此慣性元器件所導致的時滯大小不等。
可見,Clsec能夠反映模型整機滾轉力矩的變化情況,則根據非指令滾轉運動歷程中非定常氣動力與角加速度的關系,將Clsec進行定積分形成ωp曲線,應能反映模型滾轉角速率的變化情況。

圖12 非指令滾轉運動階段實時Clsec曲線Fig.12 Real-time Clsec flight log of uncommanded motions

圖13 Clsec與φ的實時飛行記錄曲線Fig.13 Real-time flight log of Clsec and φ
將其與機載陀螺儀記錄下的滾轉角速率(以下稱ωx)曲線進行對比,如圖14所示。

圖14 ωp與ωx的實時飛行記錄曲線Fig.14 Real-time flight log of ωp and ωx
因時滯大小不等,選擇在整個飛行過程的第37~41 s,此階段模型的迎角變化速率小,便于對比慣性元器件所導致的時滯。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ωx曲線較ωp遲滯230 ms,如將該時滯修正后,兩條曲線的Pearson相關系數R由0.061 3變為0.609 9,呈強相關性。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截面滾轉力矩系數Clsec能夠比慣性器件提前預測模型滾轉運動的變化趨勢。
3 結 論
本文針對基于翼面壓力的飛行器氣動力感知技術進行了相關風洞試驗研究與試飛驗證,研究結果表明:
1) 對于80°/48°雙三角翼,通過x/c=0.8位置的特征截面展向壓力積分得到的滾轉力矩系數Clsec,在迎角0°~50°范圍內,與模型整機受力存在相關性,可以反映該模型滾轉力矩受力變化。
2) 試飛模型發生非指令的滾轉運動,會使得0.8c截面的Clsec值大幅波動。
3)試飛結果表明:較傳統慣性傳感器,Clsec能夠比慣性器件提前預測模型滾轉運動趨勢變化,為飛控預判控制提供一定基礎。
4 展 望
本文提出通過特征截面滾轉力矩系數Clsec,估算飛行器在大迎角狀態下的非定常氣動力/力矩,并對該設想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驗證,實現了飛行器在大迎角平飛這一典型運動下的非定常滾轉力矩判別。但以下工作仍需開展進一步研究:
1) 利用基于翼面壓力的飛行器氣動力感知技術,實現如舵面操控介入等不同實際飛行工況中其他氣動力/力矩分量的精確推算。
2) 進一步利用特征截面壓力分布,感知表面流動狀況,提高氣動力預測時的準確性和魯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