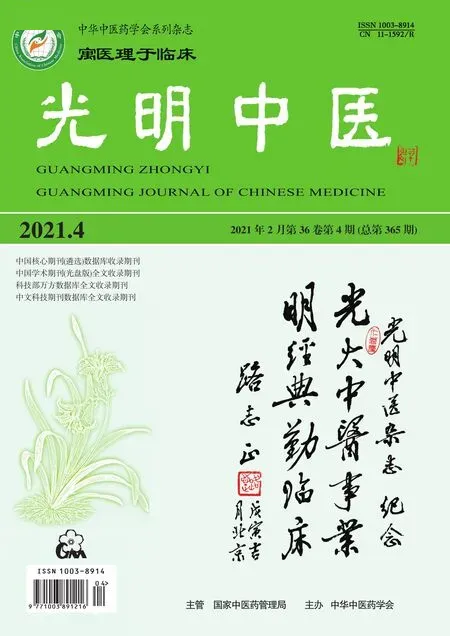芻議營衛與白癜風
霍曉玲
白癜風是一種常見的后天性色素脫失性皮膚黏膜疾病,可累及毛囊,臨床表現為白斑或(和)白發。世界范圍內發病率為0.1%~2%,我國人群患病率為0.56%,其中9.8%的患者有家族史[1]。青少年發病較多,影響患者外貌,給患者帶來嚴重心理負擔,常常使患者感到自卑,難以很好地融入社會生活。
中醫學對白癜風的診療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認為白癜風多由于“風邪搏于皮膚,日久血氣不和”所致。有學者通過對302首治療白癜風的內服處方分析發現,治療多補益肝腎、調和氣血、祛風活血通絡。進展期以祛風為主,配合疏肝理氣治療,穩定期以補益肝腎為主,兼活血化瘀治療[2]。經臨床觀察和實踐,體會到皮毛腠理的結構、功能全依賴于營衛功能正常與否,營衛調和是皮膚健康的生理學基礎。肌表營衛氣化失常為白癜風的關鍵發病環節和最終病理表現,為病之“標”,內部臟腑氣血不和為病之“本”。在白癜風的治療中應標本兼顧,在補益肝腎、活血祛風的基礎上,注意調和營衛,可提高白癜風的療效。
1 “營衛不和”與白癜風發病的關系
對于白癜風的病因病機,古代醫家多認為由風邪搏于皮膚,日久血氣不和所致。如:《諸病源候論·白癜候》記載:“白癜者,面及頸項身體皮肉色變白,與肉色不同,亦不癢痛,謂之白癜。此亦是風邪搏于皮膚,血氣不和所生也。”《證治準繩》記載:“夫白駁者,是肺風流注皮膚之間,久而不去之所致也……”。《醫林改錯》記載:“白癜風血瘀于皮里”。
以上可以看出白癜風的發病,“風邪”為重要誘因,“血氣失和”為基本病因病機。風邪為“虛邪”“虛風”;“血氣不和”包括經絡的營衛失和、臟腑的氣血失和。
導致白癜風發病的“風邪”非一般意義之風邪,正如《靈樞·刺節真邪》所言:“邪氣者,虛風也,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其有強大的破壞力,如《素問·移精變氣論》所謂“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邵學鴻教授認為:虛邪在體表經脈則傷衛氣而成寒證,郁遏衛氣便為熱證。若入肌肉,可隨體質陰陽從化為寒證或熱證,其寒則傷真氣。如若邪風深入于里,則是因不同的寒熱轉化而表現出真氣或陰精的損傷。在微觀世界被發現的今天,對邪風本質的理解,也應包括致病微生物和眾多有害物質在人體內積淀為病的因素,而決非一般意義上的風[3]。中醫學對于虛邪病機特點的描述與白癜風病機相吻合,虛邪久留,傷及空竅肌膚之營衛、真氣、陰精,致使皮毛虛、寒,導致白斑發生。
對于白癜風病因病機,在以前的文獻中多提及“血氣”,很少提及“營衛”,但是“血”與“營”、“氣”與“衛”實為一而二、二為一也。“血氣不和”必然存在“營衛不和”。正如明·張景岳《類經·營衛三焦》論述:“人身不過表里,表里不過陰陽,陰陽即營衛,營衛即血氣。”再如《醫宗金鑒》有言:“營即血中之精粹也,衛即氣中慓悍者也,以其定位之體而言,則曰氣血,以其流行之用而言,則曰營衛。”營衛無質無形,即使解剖亦無法取證,它是《黃帝內經》用陰陽哲理解釋人體氣血循環的一種假設,是在判斷出客觀存在的色、脈、證的基礎上,進一步推究人體氣血輸布運行以及其效應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它是相對存在的氣血功能的反映[4]。“營衛由絡以通,交會生化”[5],營衛二者通過脈絡末端之孫絡進行氣血津液的相互轉化,從而濡養臟腑肢節,維持人體的陰陽平衡。
對于皮膚組織來講,皮膚結構可分為:皮膚(內皮曰皮,外皮曰膚)、肌(白而肥),皮膚表面有玄府、腠理、毛發,皮膚賴衛氣充實,有少數血液運行其間。肌之分隙謂之分腠,行營衛而會元真。皮膚組織各部無處不有營衛六元五真之氣。營氣借助于衛氣的“慓疾滑利”,方能達到濡養全身臟腑肌腠的目的;衛氣借助營氣的營養滋潤,方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合。營衛調和方能發揮滋養、溫煦肌肉皮毛的功能。《靈樞·天年》說:“五臟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致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能久長。”營衛失和則皮膚腠理氣血津液氣化失常,皮膚不得溫養,導致白斑發生。
2 調營衛在白癜風辨證論治中的實踐體會
有學者對比了運用活血化瘀,扶正祛邪,標本兼治的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白癜風前后病理變化:毛細血管擴張、血流量增加,微循環得到改善,而經過治療后的皮損區,末梢微血管、管袢數明顯增加,血管袢得到充分的開放,微血管、血液循環比較充實,供血狀態得到改善,皮損區可見新的色素斑片出現:而這些色素斑點首先從血管袢周圍處開始產生,然后向四周擴張,以致相互融合。這也表明了白癜風病的皮損區色素斑的恢復與末梢微循環改善的關系十分密切[6]。目前很多中西醫結合的學者認為:營氣相當于人體的營養代謝系統,衛氣相當于人體的免疫系統,營衛與孫絡構成人體的微循環系統。從而說明了調節營衛氣血治療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治療中,調營衛為治療靶向之一,肌表“營衛和”為治療目標之一。在白癜風的治療中,調和營衛藥物的使用頻率是非常高的,應作為基礎組方構成之一,不可或缺。目前也有報道從調和營衛角度治療白癜風,如張麗軍等[7]用桂枝湯治療白癜風,張敏等[8]認為衛病傷營是營衛不和的重要病機、滋營化衛是和營調衛的前提條件,調營治衛是辨治思路、建中調營是關鍵環節的觀點。
導致皮損局部營衛失和的因素主要為:虛邪賊風傷及營衛;經絡郁滯,營衛不暢;化源不足,營衛氣虛;內部臟腑血氣失和。因此,相應的治療也主要有以下幾種:①祛除風邪;②通絡和營;③調理脾胃以養正;④調整臟腑氣血,補肝腎、調肺衛、理氣血均可直接或間接起到調節營衛作用,改善皮損局部營衛失和,促進復色。在調整臟腑氣血的基礎上,可辨證選用一些具有“升、散、透、竄、通、燥、動”特性的藥物一方面可祛除外邪,另一方面可將內部氣血精華輸達皮毛,使補而不滯,直達病所,固護溫煦皮毛。營衛氣化歸于平和,陰平陽秘,皮損復色。此類藥物包括:活血通絡藥物、祛風濕藥物、蟲類藥、宣發肺衛藥及引經藥物等,如蜈蚣、地龍、僵蠶、烏梢蛇、雞血藤、鉤藤、橘絡、白蒺藜、羌活、防風、桂枝、桔梗、麻黃、浮萍、白芷等。在白癜風的治療中,改善皮損局部營衛失和至關重要,我曾醫治一位白癜風患者,根據四診信息,辨證為肝腎不足型,予口服滋補肝腎、活血化瘀藥物治療2周,無明顯療效。經考慮缺少調營衛藥物,調整處方后又服用2周,皮損區出現復色。從此以后,每次開方特別注重調和營衛藥物的使用。
臨床上白癜風的治療多內外治相結合,外用藥物直接作用于皮損局部,經透皮吸收可調和局部營衛、祛風活血通絡,加速黑色素生成。膚色為五色調和外顯而成,“以色治色”多選用五臟五色藥物組方制成藥酒外用,如補骨脂、菟絲子、白芷、烏梅、紅花、紫草、何首烏、骨碎補、白蒺藜、墨旱蓮等。曾用此方法治療一對雙胞胎姐妹,皮疹均在腰臀局部(約占體表面積5%),考慮屬于兒童穩定期皮損,為避免長期口服藥物不良反應,予外治療法:皮疹局部梅花針扣刺1次/d,扣至局部輕微充血即可;扣刺后外涂以上藥酒;自行購買家用紫外線治療儀照射局部皮疹,3日一次,堅持治療3個月,白斑面積明顯縮小,已不明顯。
3 典型醫案
患者某某,男,64歲。2015年10月6日初診。主因“全身皮膚散發白斑10年,增多1年余”就診。患者于10年前,胸腹部起少量小片狀不規則白斑,無痛癢,當地醫院診斷為“白癜風”,曾先后服用活血祛風中草藥口服、外用“鹵米松軟膏”和“補骨脂酊 ”治療無效,皮疹逐漸擴大增多,形成大面積白斑,邊界清楚,呈瓷白色。近1年來,面部開始出現白斑。刻下癥:前額和發際、前胸、肩背和腹部、四肢可見蠶豆至拳頭大小瓷白色白斑,邊界清楚,無色素島生成,白斑面積約占體表面積的30%左右。平素四肢不溫,畏風,經常失眠,納可,二便正常,舌淡、苔薄白,脈沉細。化驗血、尿、便,肝腎功能、甲狀腺功能,心電圖和微量元素均無異常。診斷:白癜風(尋常型),穩定期。中醫辨證為肝腎虧虛,氣血不足,營衛失和。治法:滋補肝腎,益氣養血,調和營衛。方藥:黃芪30 g,桂枝10 g,白芍 15 g,太子參15 g,白術12 g,茯苓15 g,補骨脂9 g,菟絲子9 g,枸杞子9 g,女貞子9 g,當歸12 g,川芎6 g,桑椹15 g,紅花9 g,白蒺藜15 g,雞血藤15 g,桔梗9 g。日1劑,水煎200 ml分2次口服。配合外治:皮疹區予梅花針扣刺后,外用復色酒(補骨脂、菟絲子、烏梅、紅花、骨碎補等)。以上藥物打粗末,用75%酒精浸泡 7 d 后濾渣外用,根據皮膚耐受程度每日外涂 3~5次,并囑患者每日曬太陽5~10 min。1個月后復診,近期無新發皮疹,部分白斑出現點狀色素島,睡眠稍有改善,仍感畏風,舌淡、苔薄白,脈沉。前方加生姜6 g,余同前。3個月后復診,患者白斑消退30%左右,畏風、失眠等癥狀明顯改善,飲食、二便均正常。復查肝腎功能未見異常。效不更方,藥量適當減少,繼續治療。用藥至2016年4月10日,白斑消退60%,暴露部位皮疹復色良好。病程長的皮損復色較慢,但也有色素島出現,畏風、四肢不溫的癥狀基本消失,患者非常滿意,要求停服藥物。予停服藥物,繼續中醫外治。2016年10月復診,遺留四肢小片白斑,復色80%左右。
按:本例患者病程10余年,皮損以軀干為主,邊界清楚,病屬白癜風靜止期。患者男性,64歲,男子“五八,腎氣衰,發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發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發去。”患者肝腎不足致精血虧虛,脾胃氣虛致氣血營衛生化不足,畏風、四肢不溫、失眠均為營衛失和表現。結合舌質淡,脈沉細,診斷為肝腎虧虛、氣血不足,營衛失和之證。故治以滋補肝腎、益氣養血、調和營衛。初診予補骨脂、菟絲子、枸杞子、女貞子、桑椹滋補肝腎精血;當歸、川芎、紅花、桔梗、白蒺藜行氣活血祛風;雞血藤養血活血通絡;桂枝、黃芪、白芍調和營衛;太子參、白術、茯苓健脾益氣。二診增加“生姜”增強調和營衛作用。并配合皮損區梅花針扣刺、外用復色酒,加強調和營衛、活血通絡作用。經過治療,白斑復色良好,隨診無復發。在治療過程中,注重調和營衛,收到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