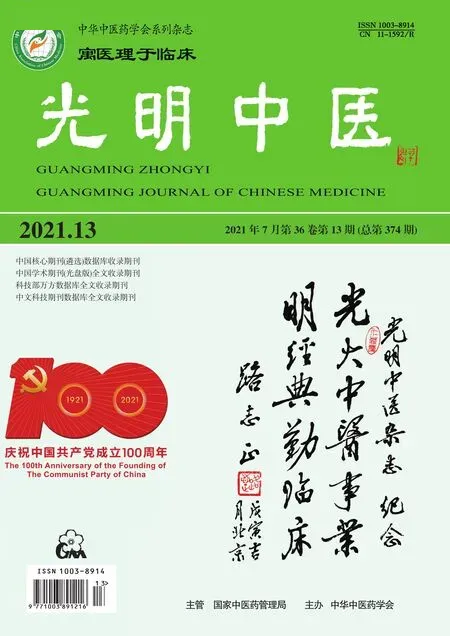基于《黃帝內經》形神理論議心身疾病的論治*
王 鑫 馮 雷 朱俊楠
“心身疾病”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是指心理社會因素在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軀體功能性障礙,而廣義的概念則還包括了心理社會因素在發病、發展、轉歸和防治過程中都密切相關的軀體器質性疾病[1]。
西方之所以提出“心身疾病”,是因于西方醫學將心理與軀體割裂研究的傳統。這一概念雖于20世紀中葉提出,中醫學對這類疾病的認識卻是古已有之。在中醫學看來,形神本是一體,軀體疾病與心理疾病的相互影響是普遍現象,這種形神理論的形成建立在氣機上,通過氣的運動將“形”與“神”聯系起來,而對于“形”與“神”的具體邏輯關系,筆者試結合《黃帝內經》相關條文進行梳理,作具體辨析。
1 氣一元論是萬物化生的基礎
生由乎動,氣有聚散離合的運動,是以有物生化滅,“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素問·五常政大論》[2])。對于生命的本初,《黃帝內經》中更多提及的是天地氣交感合而來,包括人在內的萬物自此而生。這點的認識是自氣一元向陰陽二元的遷移,“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積陽為天,積陰為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之“輕清薄靡者而為天,重濁凝滯者而為地”,亦是由氣之聚散而分。
“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靈樞·本神》[3]),“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素問·天元紀大論》),“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生命是由天地之氣交感、互動、相合而生。“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素問·六微旨大論》),“器者生化之宇”,作為一個有生命的個體,不斷化生延續,維系的基礎就是氣的升降出入,通過升降出入聯系著個體內部間以及內外之間,完成了交流代謝,這是生命的最基本特征,也是氣機理論的最基本涵義。
2 氣是神志產生的基礎
生命個體,因散而息,因聚而生,皆氣之所為。人在秉受此氣后,如何有了智慧,成為萬物之靈,《靈樞·本神》中這樣論述道:“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摶謂之神,隨神往來為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謂之魄,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該段闡述了《黃帝內經》時代對生命形成及延續過程的認識,精的聚散與神的生滅由氣的運行而變化。
“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摶謂之神”,“精”在《說文》[4]中謂“擇也”,引申為聚集的意思,如“陰者,藏精而起亟也”(《素問·生氣通天論》)就是指的氣聚集貯藏的狀態,并有時刻準備補充化為動力的能力。“生之來謂之精”就是陰陽二氣的積聚,在自然界為地為天,在人則為父精母血,二者相合,“兩精相摶謂之神”,陰陽“兩精”氤氳感合而成,這里并未言及形體,而是用“神”來名之,“神”到底為何,首先,其應在兩精感合基礎上所產生,最原始的那個生命本原體,也就是這個時候已經具備了升降出入的能力,而主宰形體這種能力的存在就是“神”,接下來便給出了解釋。
“隨神往來謂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說文》:“魂,陽氣也”“魄,陰神也”。“血舍魂”(《素問·六節藏象論》),“人臥血歸于肝”(《素問·五藏生成》)。往來者,血氣之流注相貫是也,人睡眠時陽氣內舍于血,醒則出衛于外,“魂”為陽氣舍于里的狀態。“肺藏魄”,舍于胸中,主呼吸精氣,所以并精出入,主管物質交換,飲食氣味化生為精氣,排泄糞便的出口也稱為“魄門”。陰神內藏,外彰宣降,也是氣之升降出入的體現,而這個由“精神”所掌控,“精”為“神”的基礎,“神”的功能就是主管氣之升降出入。器官組織這些有形的東西有了,但并不能具備生命,得需要空靈中的一點,讓其內部之間以及與外界有交流才是活物,古人把這個稱之為“神”,“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靈樞·天年》),神為生命所賴的最重要的東西,“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問·移精變氣論》)。
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之后,人就可以與外界進行物質、信息交換,“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就有了感受、認知事物的能力,繼續儲存信息,有了初級的非條件反射;反復的感受、認知會固化信息的提取和反饋,形成條件反射,智能學習就出現了,進而思考、謀劃遠期的事情,繼而制造工具、改造世界。
人的智能發展就像一座大廈,這座大廈的根基就是精氣。精氣化神,神御氣,氣之升降出入,無器不有,然而其為神所主;反之,形體氣機又是“神”的物質基礎,二者生理上相互影響,病理上又相互聯系。
3 形神一體,五臟為樞紐
形與神統一于一身之氣的觀念應用于指導實踐,是通過構建形神一體的五臟模型來實現的。
《素問·宣明五氣》云:“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五臟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將形體與神志通過五臟連成了一個整體。《素問·調經論》提出百病虛實“皆生于五臟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臟。五臟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五臟主宰形體,又藏神志,五臟通過聯系內外的經隧來調節氣血運行;血氣運行失常則影響五臟形神,從而導致心身疾病的發生。
4 社會心理影響氣血情志
“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其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素問·舉痛論》),是情志刺激引起氣血紊亂而致病。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靈樞·本藏》),指出了精神因素對人體免疫力的影響。
“淫氣喘息,痹聚在肺;淫氣憂思,痹聚在心”(《素問·痹論》),“有所墮恐,喘出于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于肺,淫氣傷心”(《素問·經脈別論》),情志太過會引發或加重喘疾等。
《素問·疏五過論》中論述了人生境遇對影響疾病的發生發展,“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后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后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后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為攣”,心理因素、社會因素也好,都是通過影響氣,波及情志五臟氣血,而演變成心身疾病。
5 應用發揮
5.1 四時養神《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根據四時氣機特點,給出了不同的養形以養神的具體方法:春生則舒緩以利升發,夏長則外張使所愛在外,秋收則內斂以靜神氣,冬藏則伏匿以順蟄閉。通過形體的鍛煉,來調節氣機,順應天地四時之氣的生長收藏,繼而來調養“神”,使神志順應四時天地之氣的變化,達到預防和治療心身疾病的目的。
5.2 方藥發揮《神農本草經》[5]中記載了許多既能夠治療軀體疾病,又能夠作用于神志的藥物,如:人參“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木香“主邪氣,辟毒疫溫鬼,強志,主淋露,久服不夢寤魘寐”;遠志“主咳逆,傷中,補不足,除邪氣,利九竅,益智慧,耳目聰明,不忘,強志倍力”。后世對于形神共病的治療,也多基于氣機理論而發。《金匱要略》[6]中半夏厚樸湯治療“咽中如有炙臠”,宣降氣機、化散痰結,既能夠治療由精神情志異常所致的神經官能癥,又能夠治療痰氣郁結、與情緒相關的慢性咽炎。《備急千金要方》[7]有大續命散,既能夠治療“手足拘急疼痛,不得伸屈;頭眩不能自舉,起止顛倒”的形體病證;還能治療“風入五臟,甚者恐怖,見鬼來收錄;或與鬼神交通,悲愁哭泣,忽忽欲走”這種精神病證。時方中也不乏此類方藥,逍遙散可通過疏肝理氣治療單純的情志郁結,又多用來治療與情志相關的肝氣郁結的脾胃病及婦科病證;歸脾湯補益氣血、養心健脾,既可以安神定志治療失眠心悸等證,也可以益氣攝血治療血證,皆為久傳至今、形神共治的良方。《臨證指南醫案·郁》中直言:“悲泣乃情懷內起之病,病生于郁,形象漸大,按之堅硬,正在心下。用苦辛泄降,先從氣結治”[8],以半夏、瓜蔞、木香、烏藥散結理氣,也是形疾起于神病,身心同調。
5.3 移情療法氣機理論除了在形體鍛煉和方藥應用外,古代醫家還將其應用于移情療法,張子和在《儒門事親》中多載此類醫案,其中一則:“一富家婦人,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兩手脈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進,脈得其平”[9]。思則氣結,怒則氣上,張子和通過情志相勝,使郁結之氣汗出得散,雖未用藥是勝用藥,考慮到心身疾病本身的病證特點,方法的選用亦需隨機而變,情與藥之法雖異而道實同。
6 小結
綜上所述,氣機理論是構建形神理論框架的基礎,貫穿于對心身疾病的認知和診治整個過程。以氣機理論為基礎、以五臟為核心的形神一體觀,使得中醫學對心身疾病的診療有著天然的優勢。立足于氣機之常,不拘于方法,通過調節氣機、安和五臟,達到調養形神、心身同治的目的。本文通過梳理理論淵源脈絡,總結前賢經驗,愿能對現今臨證的診治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