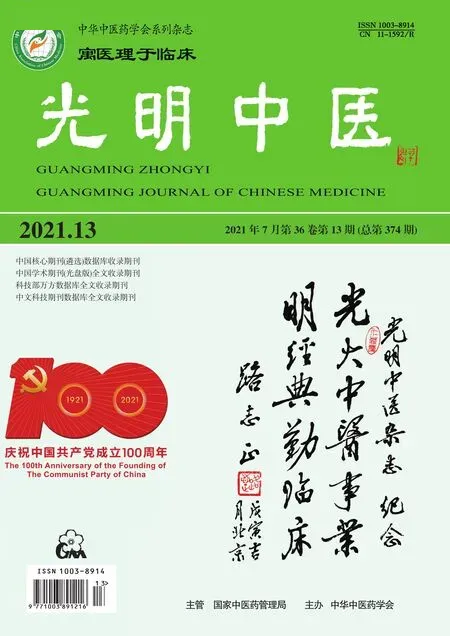中醫藥辨治糖尿病神經源性膀胱研究進展*
靳 鴿 馮志海 李先行 王曉靜 馮文帥
糖尿病神經源性膀胱(Diabetic Neurogenic Bladder DNB)是糖尿病自主神經病變中常見的慢性并發癥,屬中醫“消渴”“淋證”“癃閉”范疇[1]。其特征性表現為膀胱感覺神經受損,逼尿肌收縮力下降,殘余尿量增加[2]。本病起病隱匿,前期癥狀不明顯,如未得到及時有效診治,嚴重者可并發尿路感染、急性腎功能衰竭、敗血癥等系統性疾病[3]。流行病學研究顯示[4,5],DNB發病率高達40%~80%,即使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況下仍約25%,呈世界流行性。DNB發病機制尚不明確,其可能與高血糖毒性、氧化應激損傷、膀胱結構重塑、神經功能障礙等相關[6]。目前西醫以對癥治療為主,但存在停藥復發、不良事件發生率高等問題[7]。近年來,眾多研究表明中醫治療本病具有一定優勢。臨床醫生可據患者病情辨證論治,予以個體化治療方案,可較好地展現出以患者為中心的診療思想。結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就中醫辨治DNB相關研究進展作一綜述,旨為臨證應用提供參考,以饗同道。
1 DNB的中醫病因病機認識
中醫文獻本無“糖尿病神經源性膀胱”病名的記載,據其尿頻、尿急、小便不盡、尿潴留等癥狀可將其歸屬“消渴”“淋證”“癃閉”范疇。本病病因復雜,或因飲食不節,或傷于外邪侵襲,亦或體虛久勞發為本病。DNB病位首在腎與膀胱,與肺、脾密切相關,源于中醫理論所述腎主水,膀胱藏水,肺為水之上源,脾主運化水液。《圣濟總錄》[8]指出:“消渴日久,腎氣受傷……開闔不利”,DNB主因消渴日久,素體虛弱,耗氣傷陰,瘀血阻絡,腎陽衰憊,氣化不及,膀胱失約所致,即所謂氣虛則無以推動血液運行,陰虛則無力資以陽氣化生。呂仁和[9]認為,本病分為3個階段,早期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久而重損陰液,肝腎虧虛,以致膀胱氣化不利;繼則傷及心脾,中氣下陷,運化失常,水失制約;晚期則病久不愈,腎元損傷,經脈失養客于膀胱引發本病。邵經明[10]認為DNB源于外邪久擾正虛,精疲神衰,脾腎受損,《醫宗必讀》云:“脾土主運行,腎水主五液”,若脾腎失調,必然會出現水液代謝失常,痰水瘀血互結于膀胱,氣化不利而溺不得出,病機特點:虛實夾雜,標本并存。唐紅[11]認為脾腎陽虛為發病之本,氣化失常為致病重要環節,瘀血既為病理產物,又反作為致病因素加重血瘀水停,內阻膀胱。
2 DNB的中醫辨治思路探討
《靈樞·五變》言:“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中醫理論認為,人體是有機統一整體,中醫辨治DNB不應拘泥于膀胱本腑,亦不必拘泥于陰陽上下,有其癥即可用是法。正所謂《黃帝內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結合文獻分析及眾醫家對DNB的診療思想,本文總結出三大辨治思路,治當宣肺肅降,提壺揭蓋,以上下相召;調和脾胃,辛開苦降,以升降相因;溫腎化氣,行水布津,以陰陽相合。
2.1 提壺揭蓋 上下相召《證治匯補》[12]言:“一身之氣關于肺,肺清則氣行,肺濁則氣壅,故小便不通”,即闡明了中醫辨治DNB可從肺調治。肺、腎雖分居人體上、下二焦,但肺主氣,為水上之源,主通調水道,宣發肅降。若肺氣虛損,失于宣降,上下不通,可致氣不行水,制約無權,如《丹溪心法·破滯氣》云:“人以氣為主,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窮壤判”。可見,肺氣條暢對體內尿液排泄具有重要作用。張達等[13]將肺與膀胱的關系比作為“滴水之器,閉其上竅則下竅不通,開其上竅則下竅必利”。根據上竅開則下竅自通的道理,立足全身氣機,不再一味通利下竅,而是通過開宣肺氣,調暢上焦,引邪外出,使小便從膀胱出,宛若“提壺揭蓋”。誠如《黃帝內經》所記載的“病在下取之上”“開鬼門,潔凈府”。楊震[14]亦認為人體肺竅與前陰之氣相通。一者從五行學說闡釋,肺為腎之母,腎為肺之子,二者母子相及,金水相生,若肺氣無權,腎水不能攝,治腎者必應治肺;二則從經絡理論分析,“足少陰腎經之脈……其直者……入肺中,其支者,從肺出”[15]。肺經與腎經遙遙相對,腎經與膀胱經又相互絡屬,環環相扣,肺竅閉可直接影響腎與膀胱功能通調。因此,從肺調治DNB,可使肺腎兩臟上下相召,以達水道自調之效。在臨證遣方用藥時應注重使用淡滲氣薄之藥,如越婢加術湯、防己黃芪湯等為常用宣肺治上利水代表方[16]。
2.2 辛開苦降 升降相因消渴患者素喜嗜肥甘,易釀濕熱于脾胃,復由久病腎陽虛損,易致寒熱錯雜蘊結中焦,使中焦失和,升降失常。脾、胃同屬中焦,升降相宜,為氣機、水液代謝之樞紐。若邪困中焦,氣機失于升降,則水液上不能達肺以通調,下不能達腎以氣化輸膀胱,癥見尿路閉阻,水道不通[17]。因此,臨證辨治時可從脾胃論治。朱章志等[18]提出DNB病位雖在腎與膀胱,但與脾胃密切相關,治應辛開苦降,調其寒熱,益脾和胃。《素問·六微旨大論》[19]亦言:“少陰之右,太陰治之”,脾、腎雖分居人體中、下二焦,但其通過經別、經筋遙相感應,從脾經、胃經入手,佐以寒溫適中的藥物,調和中焦氣機,使脾胃升降相因,再伍以溫藥開太陽、利膀胱,使少陰之邪從太陽之表而解,固護腎陽以溫下焦、利寒水,方可關其效。錢秋海[20]以脾胃為切入點論治DNB,常運用自擬半夏瀉心湯進行治療,方以辛溫半夏為君;臣以辛熱之干姜溫中散寒,苦寒之黃芩、黃連泄熱;佐以肉桂補下焦之元陽;又酌加黃芪補氣固表;生白術化濕;柴胡、葛根通調肺脾;白茅根清熱利尿。諸藥相配,共使中焦得運,納化相得,燥濕相濟,升降相因。臨證運用時,可根據兼癥進行辨證加減。若久病入絡,血瘀下焦者,可配牛膝、益母草等活血通絡之品;兼情志抑郁者,可加郁金、龍膽草疏肝利膽;兼心煩失眠者,配伍酸棗仁、遠志寧心安神。現代藥理研究發現[21],半夏瀉心湯不僅可改善腸道菌群失衡,還具有調控胃腸內分泌功能紊亂等功效。
2.3 溫陽化水 陰陽相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22]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保證陰陽的沖和調達乃為疾病發展進程中之綱鑒。消渴日久,素體陰竭陽衰,陰陽失調,乃使腎與膀胱輸瀉失常。《辨證錄·小便不通門》云:“人以為膀胱之水閉也,誰知是命門之火塞乎,命門火旺,而膀胱之水通……命門火衰,而膀胱之水閉矣”。腎精常以腎陰、腎陽為劃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為用,是以腎者可表現為陰陽的雙面性。DNB病機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若以腎陰不足為主,則虛熱內生,虛火客于膀胱,可癥見小便短赤頻數;至后期傷及腎陽時,則機體失于溫化,水飲停于膀胱,便可癥見小便量少,閉塞不通。因此,治當調其陰陽,溫陽化水。李賽美[23]常用自擬加味五苓散以溫補腎陽,通化水氣,使濕邪從小便去。全方以薏苡仁代替豬苓,直達下焦,利水滲濕;臣以烏藥、黃芪、炮附片溫陽化氣,行水布津;兼水熱互結傷陰者,可合用豬苓湯加減以養陰清熱,利水滲濕。現代藥理研究表明[24],加味五苓散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DNB大鼠逼尿肌功能,保護和修復受損膀胱組織。烏藥,味辛氣溫,歸肺、脾、腎、膀胱經,長于溫腎散寒,行氣化水。《本草正義》記載民間常用烏藥單藥治療下元虛寒,小便不利之病。
3 DNB的中醫治療方法概況
3.1 中藥內服中藥組方是歷代醫家臨證經驗的結晶,長期以來療效顯著,歷久彌新。其不是單味藥物有效成分的簡單疊加,而是中藥多成分、多靶點的協同增效。以人為本,據方加減是中藥內治療法的優勢所在。劉麗娟等[25]研究發現,丹芪縮尿方(黃芪30 g,野山參8 g,葶藶子10 g,大黃5 g,橘核10 g,川芎12 g,丹參30 g,三七10 g,川牛膝30 g,茯苓30 g,澤瀉10 g,威靈仙10 g,地膚子10 g)具有活血化瘀、益氣養陰、利尿消腫之功效,可顯著改善DNB患者膀胱殘尿量、尿流率、逼尿肌壓力、尿道壓力。王芳等[26]對腎陽虛型DNB患者Meta分析發現,中藥濟生腎氣丸聯合西醫藥物治療相較單純西醫基礎治療可明顯改善患者臨床不適癥狀,減少排尿次數,且未發現不良反應。康莉娟等[27]將64例脾腎虧虛型DNB患者分為西醫對照組和口服平消癃清方(熟地黃15 g,山藥15 g,山萸肉15 g, 澤瀉12 g,茯苓12 g,巴戟天10 g,仙茅10 g,淫羊藿10 g,菟絲子12 g,牛膝10 g,杜仲12 g,豬苓10 g,益母草15 g,烏藥10 g,小茴香10 g)治療組。結果顯示,平消癃清方在改善患者尿流率、膀胱殘余量、臨床癥狀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并且降糖效果明顯。車前子性味甘寒,入腎、膀胱、肝、肺經,功善利水通淋、滲濕止瀉。張恒等[28]通過動物實驗研究發現,車前子提取物可通過調節胰島素代謝過程中藥信號通路(PI3/AKT)相關因子的表達,降低小鼠體內血糖濃度,延緩DNB病程的發展。
3.2 針灸療法針灸療法是我國傳統的中醫外治療法,歷史悠久,療效明顯。其主要優勢是可針對病變部位進行局部施治,起效快。徐嘉敏等[29]基于數據挖掘技術對DNB取穴規律研究發現:①最常用的腧穴為關元、三陰交、中極等,《備急千金要方》記載:“胞轉不得尿,刺關元”,針刺關元穴可溫補下元,緩解尿潴留癥狀;②選穴以腹部穴位為主;③任脈為運用頻率最高的經絡,任主胞胎,總任一身之陰經,循行于腹部正中,覆蓋膀胱體表投影;④募穴為最常用特定穴,對六腑疾病有特殊的治療功效。呂婷婷等[30]研究證明,電針療法可雙向調節膀胱反射-陰部神經及尿道括約肌的收縮,調控尿道內壓及膀胱逼尿肌的活動,改善膀胱順應性,促進排尿功能恢復。近年來多項研究表明[31,32],艾灸療法可改善微循環,營養神經,興奮神經突出前腎上腺素能反應。陳翠芝等[33]研究發現艾灸(關元、中極)療法相比甲鈷胺注射治療更能明顯改善患者臨床不適癥狀,臨床總有效率高達90.0%。秦文[34]在西醫常規療法上采用針刺配合溫灸療法,根據不同證型在關元、中極、水道、陰陵泉、三陰交等穴位施以補虛瀉實手法,治療組總有效率86.67%,對照組總有效率67.86%,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3 穴位貼敷療法穴位貼敷療法,是指將載有某些中藥的貼敷劑置于體表特定穴位上,使其既可發揮中藥藥理作用又能達到穴位刺激雙重作用的一種中醫特色療法。李銀娣等[35]臨床觀察60例DNB(腎陽虧虛型)患者。研究顯示,中藥益氣溫陽方穴位貼敷比西醫常規治療效果明顯,在膀胱殘余尿量、中醫證候積分以及臨床癥狀改善等方面更為顯著。何瑩瑩等[35]認為DNB與消渴日久,腎陽虧虛密切相關。分別觀察了溫陽利水方穴位貼敷治療和超短波治療的臨床效果,研究顯示穴位貼敷組總有效率為94.2%,超聲短波組總有效率為78.8%,表明溫陽利水方穴位貼敷治療效果更為明顯。
3.4 中醫其他療法中藥封包療法是中醫傳統外治療法,從成本-效益角度分析,中藥封包療法不僅臨床有效率高,安全無不良作用,而且價格低廉,操作簡便易行,具有一定的推廣價值。莫小書等[37]探究中藥封包聯合糖癃通利方治療效果,研究發現中藥封包組可顯著減少患者膀胱殘余量,改善臨床癥狀。其原因可能是藥物和封包的溫熱刺激(吳茱萸50 g,王不留行50 g,肉桂50 g,小茴香50 g,烏藥50 g,車前子100 g,粗鹽100 g)協同作用于膀胱,共奏溫腎助陽、化氣行水之功。蘇珊平等[38]發現丁香-厚樸封包療法(川厚樸250 g,丁香50 g研磨打粉)在減少膀胱殘余量、改善DNB癥狀方面療效顯著,臨床有效率高。魏云飛等[39]研究發現針灸配合耳穴貼壓療法在改善膀胱殘余尿量、排尿功能方面也具有一定優勢,療效確切,安全性高,不良反應較小,便于推廣。推拿療法是一種無創養生療法,王琳等[40]為探究走罐療法治療DNB的療效,選取足太陽膀胱經、督脈、夾脊穴進行背部走罐,同時配合局部穴位拔罐。研究發現,治療后患者排尿無力、淋漓不暢、尿潴留、尿失禁等癥狀均得到明顯好轉。陳寶春等[41]通過檢測殘余尿量、臨床證候、不良反應評價穴位注射(足三里、三陰交)治療DNB的療效。結果表明,穴位注射組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基礎治療組。
4 討論
DNB病程纏綿難愈,嚴重影響了糖尿病患者的預后,對患者心理、經濟及家庭多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負擔。本文就近年來中醫辨治DNB相關研究進展進行了初步探討和總結,我們發現中醫療法優勢明顯,方法多樣,療效顯著,可較好地彌補西醫在本領域的不足。整體觀念、辨證論治是中醫學兩大特點,在深入挖掘眾醫家臨證思想經驗的基礎上,從中醫陰陽、五行、經絡理論出發,將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提出了3種辨治DNB的新思路,為DNB中醫臨床論治提供了新參考。大量臨床研究證明,無論是中藥內服、針灸、穴位貼敷、中藥封包、亦或是推拿、耳穴貼壓、穴位注射等中醫特色療法都能較好的緩解患者不適癥狀,改善相關實驗室指標,且成本低廉,操作簡單。但中醫辨治DNB體系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筆者認為今后研究可從以下方面加以改進:①基于生物信息學技術,對DNB疾病靶點在分子功能、細胞成分、生物進程等層面進行分析,以探明具體發病機制。②嚴格管控科研設計各個環節,規范各項實驗操作流程,開展隨機、雙盲、前瞻性、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研究。③基于數據文本挖掘技術對歷代文獻或名中醫醫案經驗進行歸納總結,以探求更為有效的用藥規律。換言之,只有推進理論研究、臨床研究、實驗研究與各項先進技術結合,深入探討其發病機制,充分發揮中醫藥的優勢,才能科學準確地幫助其提升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