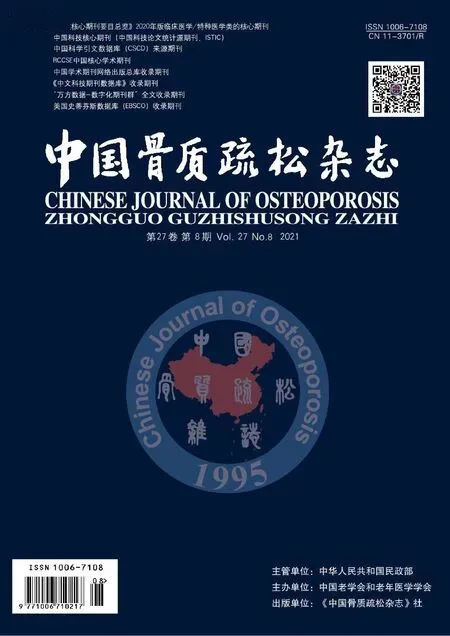骨內血管作為骨質疏松癥治療靶點的研究進展
桑曉文 詹紅生
1 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陜西 咸陽 712000
2 上海市中醫藥研究院骨傷科研究所,上海 201203
骨組織是一種富含血管的結締組織,血液供應由小動脈網絡提供,并通過血管新生過程發展[1]。脈管系統可向骨細胞輸送氧氣、營養素、激素、神經遞質和生長因子等,并對于骨發育、再生和重塑起到重要作用[2-3]。隨著血管結構生物學發展,人們對于骨內血管在生理和病理條件下的特點有了更深入了解,而靶向骨內血管促進新骨形成可能成為治療骨質疏松癥的新治療靶點。
1 血管及血管新生過程
血管由內層血管內皮細胞、外周壁細胞(包括周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組成[4]。血管新生包括血管發生(vasculogenesis)和血管形成(angiogenesis)兩種形式,前者指從中胚層來源的內皮前體細胞(angioblast 成血管細胞)新形成血管,而后者指從原始血管床出芽形成新血管[5]。vasculogenesis一般發生在胚胎期,成人體內的血管新生大多通過angiogenesis過程產生[6]。血管形成過程中,新形成的小毛細血管由外周壁細胞支持的內皮細胞構成的中空管腔,并有基底膜和細胞外基質(ECM)包繞[7]。在成人中,血管和內皮細胞保持靜止狀態且很少被激活形成新的分支,而內皮細胞周圍的基底膜和周細胞維持內皮細胞穩定的位置,僅在特定刺激如缺氧、炎癥狀態時,血管形成才啟動[8-9]。首先,周細胞分離,ECM和基底膜被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降解,這導致血管的不穩定和血管通透性增加。此外,細胞外基質的分解過程釋放諸多促血管生成因子和趨化因子,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FGF-2)和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SDF-1)[9]。此類細胞因子可與內皮細胞受體結合,激活內皮細胞,并誘導內皮形成新的出芽分支。此過程需要特定的“尖細胞”(tip cell)和“桿細胞”(stalk cell)在VEGF/Notch信號通路調控下完成[6,10]。內皮細胞形成諸多偽足,來協調細胞遷移方向,而stalk cell跟隨tip cell方向增殖生長,而stalk cell通過細胞內囊泡融合和結構排列形成新的管腔[11],并伴隨新的細胞外基質沉積和周細胞的招募,最后形成穩定的血管。如果沒有周細胞的附著,血管形成不穩定,并可以被迅速分解退化[11]。促血管新生因子(VEGF、FGF-2、SDF-1、EGF)與血管抑制因子(thrombospondin、endostatin、angiostatin、angiopoietin-2)在局部微環境中保持動態平衡是維持器官穩態的重要機制,而血管形成功能下降是損傷后修復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8,12]。
2 骨內血管結構特征
骨組織具有豐富的血管網絡,消耗大約10%~15%的心臟輸出,骨內血管的分布可有效地將氧氣和營養物質輸送至骨髓腔。研究[1,3,13]表明無論骨骼形態,骨的血管供應大多都來源于來自皮質骨區域的營養動脈,通過骨內縱向的Haversian管內動脈和橫向的Volkmann’s 管內動脈,與干骺端或骨內膜毛細血管連接,最終完成靜脈回流,而骨骺區域動脈血管有其獨立動靜脈系統。骨內毛細血管的直徑通常為5~10 μm,并由單層排列的內皮細胞構成,其一般分連續型、孔隙型和血竇型[14]。連續型毛細血管的網絡屏障在體內普遍存在,內皮細胞緊密相連。此類毛細血管的獨特結構允許水、小分子和脂溶性材料擴散到周圍組織或間質液中,而不會損失循環細胞和血漿蛋白,而較大的分子如葡萄糖和其他營養素通過轉胞吞作用通過單層內皮細胞。孔隙型毛細血管具有穿透內皮細胞襯內的隔膜,孔隙存在不僅加速了水的交換,而且還允許溶質通過。血竇型內皮細胞在細胞之間具有間隙,這種特征導致水的自由交換,并為等離子體和間質液之間的大量溶質如血漿蛋白提供導管。由于在這些器官中需要廣泛交換,血流在血竇中減速以延長跨越血竇屏障的外部變化的時間。與此同時,沿著肝臟、脾臟和骨髓血竇分布的吞噬細胞充當著處理和吞噬外源性病原體、受損細胞和碎片的作用[15]。在骨骼系統內,孔隙型毛細血管和血竇型毛細血管占大多數,且與其他器官毛細血管類型不同,骨內毛細血管不表達VEGFR3[16]。
3 骨內血管與促骨形成偶聯調控
骨內血管灌注不足與骨折愈合障礙和骨質疏松癥密切相關[17-18]。通過卵巢切除(OVX)骨質疏松癥模型發現,骨內血流灌注減少的同時發生骨量下降的比例幾乎同步[19];通過小鼠的活體成像顯示,當血流受損傷可導致骨內血管生成和骨形成減少,以及內皮細胞Notch信號通路的下調;在老年小鼠中,骨內血流和內皮細胞Notch活性也降低,導致血管生成和成骨減少[3]。研究表明,骨系細胞可以產生血管因子,而內皮細胞同樣可以貢獻促成骨的細胞因子,在成骨細胞與內皮細胞共培養體系中發現血管生成和骨的礦化作用均得到增強[20],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21]、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FGF-2)[22]、血小板衍生因子BB(PDGF-BB)[23]、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24]、表皮生長因子7(EGFL7)[25]及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趨化因子4(SDF1/CXCR4)軸[26]在血管形成和骨形成偶聯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樣內皮細胞Notch信號傳導可促進出生后長骨中的內皮細胞增殖和血管生長,Notch信號傳導的破壞不僅損害了骨血管的形態和生長,而且還導致骨生成減少,長骨縮短,軟骨細胞缺損,骨小梁減少和骨量減少[27]。目前研究[28]發現,骨生長活躍區域如干骺端、骨膜區域具有CD31+/endomusin+的H亞型血管,其周圍有osterix陽性骨祖細胞聚集,并與成骨明確相關,而髓腔區域具有CD31-/endomusin-的L型血管,在結構上H型血管在干骺端、骨膜區域呈現柱狀排列,而L型血管在髓腔內呈現網狀結構。通過對骨內微循環的測定,H型血管內血流流速更高[3,29],通過測量活體小鼠氧分壓(PO2)得出,在H型血管豐富的骨內膜區域的氧分壓比L型血管分布的髓腔組織高[30]。此外發現,骨內血管特殊類型CD31+/PDGFRβ+陽性血管周圍,小動脈形成明顯增加,而老年小鼠此類血管明顯減少。國內學者[31]研究發現在老年人群和骨質疏松癥人群中H型血管數量同樣減少,骨內H型血管可能是成人骨量的生物標志物。
4 骨內血管與骨質疏松癥治療
在哺乳動物體內,骨形成與骨吸收共同維持骨穩態,但由于成骨與破骨偶聯機制,在抑制骨吸收同時骨形成同樣受到抑制[32]。而近期臨床研究證實,對于重度骨質疏松癥患者,促骨形成優于抑制骨吸收治療[33]。骨形成效應是從根本治療骨質疏松癥的關鍵所在,而靶向骨內血管促進新骨形成可能成為治療骨質疏松癥新的研究方向[34]。研究[35]表明,促骨形成藥物特立帕肽在對卵巢切除(OVX)大鼠干預后發現可以提高骨量,同時可促進缺損部分新血管形成。Notch信號通路是一條在物種進化過程中高度保守的信號通路,該通路在骨質疏松癥、骨性關節炎及骨腫瘤等疾病中均有表達,對骨骼系統有重要影響[36]。Notch信號通路通過調節內皮生長因子受體2(VEGFR2)影響內皮細胞向尖端細胞(tip cell)與莖細胞(stalk cell)的分化選擇,調節血管生成[37]。通過激活內皮細胞Notch信號通路,可以促進出生后長骨中的內皮細胞增殖和血管生長及造血干細胞微環境的擴張[38];此外,破骨細胞前體細胞分泌的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PDGF-BB)能誘導血管新生及骨形成,利用外源性PDGF-BB增加了骨內H型血管并刺激骨形成[23]。小鼠中內皮細胞特異性ZEB1的缺失,可損害骨內H型血管形成,導致成骨減少,ZEB1的缺失減少了Dll4和Notch1啟動子上的組蛋白乙酰化,從而抑制Notch信號傳導[39]。通過激活NOTCH通路可釋放蛋白noggin,外源性noggin可以使Dll4-NOTCH信號突變小鼠的長骨長度、骨量恢復正常化[38]。此外,Slit3可由脈管系統中的內皮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表達和分泌,并且Slit3同源受體Robo1和Robo4由內皮細胞普遍表達[40]。體內實驗表明,Slit3敲除小鼠在胚胎發生期間顯示出血管生成的破壞,而成骨細胞分泌的Slit3可促進H型血管形成,并使H型血管內皮細胞大量表達其受體Robo1,小鼠敲除Slit3可減少骨內H型血管數量,導致低骨量的發生;當給予重組Slit3可同時增強骨折愈合和對抗骨質疏松小鼠骨丟失[41]。
5 展望
隨著血管生物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骨內血管結構、功能有了更多認識。骨內血管不僅為循環系統發揮作用,而且在骨骼系統疾病中也有重要意義。內皮細胞與骨系細胞互相調控,對于維持骨穩態、促骨形成有重要意義,通過對骨內血管新生、血管形成與骨形成偶聯調控、內皮細胞Notch信號通路及骨內H型血管展開深入的研究,可為骨質疏松癥防治提供新的治療思路和防治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