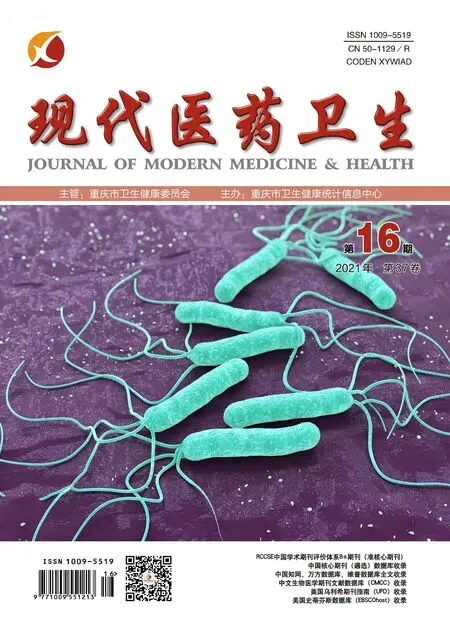嬰兒沙眼衣原體肺炎的臨床特征和預后分析研究進展
高 峰 綜述,羅 健 審校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呼吸中心/國家兒童健康與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兒童發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兒科學重慶市重點實驗室,重慶 400014)
沙眼衣原體(CT)多存在于女性生殖道中,孕期生殖道有CT感染的母親在生產時可經母嬰傳播,引起嬰兒包涵體結膜炎、衣原體肺炎,甚至出現呼吸窘迫、呼吸衰竭和遠期并發癥如哮喘等。近年來,CT肺炎發病率有增高趨勢,隨著分子生物學、免疫學等技術的飛躍發展及對該病的認識,CT肺炎日益受到兒科醫生的重視。本文將嬰兒CT肺炎的臨床特征及預后研究進展綜述如下,以便進一步提高兒科醫生對CT肺炎臨床特征的認識和對預后的重視,為CT的預防、臨床規范管理、減少并發癥和提高遠期生活質量提供一定的幫助。
1 病原學特點
CT的大小介于細菌與病毒之間,有和革蘭陰性菌相似的細胞壁成分,有核糖體,但缺乏三磷酸腺苷(ATP)酶,不能合成ATP,只能利用宿主的能量來合成代謝,是一類專性細胞內寄生的微生物。CT Omp1基因編碼的主要外膜蛋白(MOMP)的氨基酸序列差異,是其血清型分類的主要決定因素。目前,CT共分為19個血清型[1]。國內報道6月齡以下因肺炎住院患兒檢測CT感染情況并進行分型,發現基因型E是最常見的,其次是基因型 F、J、D、K、G 和 H[2]。CT經二分裂繁殖,具有獨特的2階段生活方式,對應2種不同的形態,包括基本體(EB),即代謝不活躍的非復制性的胞外感染期;網狀體(RB),即代謝活躍的復制性的胞內寄生期。一個完整的感染周期需要48~72 h。紅霉素、阿奇霉素等大環內酯類抗生素能抑制其生長。能夠引起長期的亞臨床感染能力通常是CT的主要特征。自然感染CT后,宿主的免疫反應并不能提供永久的免疫力,對再次感染也僅有極微弱的保護作用,且維持時間短,常有反復或持續性CT感染。
2 流行病學
CT是發達國家最常見的性病病原體,婦女生殖道CT感染常見[3]。嬰兒CT感染主要通過陰道分娩時母嬰垂直傳播獲得,經剖宮產出生的嬰兒很少感染,部分因胎膜早破上行感染。也有部分胎膜未破的剖宮產新生兒感染CT,這可能與從宮頸到羊膜腔的上升傳播或經胎盤的感染途徑有關。如果不采取預防措施,有50%~70%的患有宮頸CT感染的婦女所生的嬰兒會感染衣原體;18%~50%的嬰兒會患結膜炎,15%~20%的患兒會患鼻咽定植和5%~20%的患兒會患肺炎[4]。重慶的一項研究表明,CT母嬰垂直傳播率為24%,陰道分娩產婦垂直傳播率為66.7%,剖宮產產婦垂直傳播率為8.3%[5]。國外研究報道,6月齡以內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嬰兒CT感染率高達30%,75%嬰兒無熱肺炎與CT感染相關[6]。
3 臨床特點
CT肺炎好發于年齡3~16周嬰兒。可先有上呼吸道感染表現,如鼻阻、流涕,隨后出現特征性的(間隔時間短、斷續性)咳嗽,常不發熱,體檢發現呼吸急促,可聞及濕啰音[7]。但只有1/3~1/2的患兒可同時患有結膜炎。重癥感染病例比普通病例更易發生氣促、喘息[2],此外,重癥感染病例可有發紺、呼吸困難(呻吟、鼻翼扇動、三凹征)、呼吸暫停、嗜睡、一般情況差、喂養不良甚至體重下降等臨床表現。國內研究報道年齡是發生重癥感染的危險因素,<3個月更易發生重癥肺炎[8]。
3.1實驗室檢查 白細胞不高或輕度增高,以淋巴細胞比例增高為主,C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一般不高。多有嗜酸性粒細胞增高,有研究指出,70%~75%CT肺炎患兒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大于300×106L-1。嗜酸性粒細胞升高的原因考慮是衣原體導致的變態反應引起[9],是CT肺炎較特異的實驗室指標。
3.2影像學表現 CT肺炎患兒胸部X線主要表現為雙肺廣泛間質和(或)肺泡浸潤、常見雙肺過度充氣,偶見大葉實變[10]。部分患兒胸部X線出現明顯的結節狀或顆粒狀滲出影,易誤診為肺結核,行胸部CT檢查也難以鑒別,文獻報道誤診率達20.8%[10],在臨床上需注意結合病史、實驗室檢查鑒別。胸部CT多表現為充氣不均、節段性實變、“馬賽克”征、磨玻璃影、雙肺廣泛間實質病變,胸腔積液罕見,部分有支氣管擴張或肺不張。CT感染若發生肺不張后治療時間長,容易造成持續的氣道損害,為今后的治療和預后留下隱患[11]。嬰兒CT肺炎較少有呼吸困難而大部分胸部X線或胸部CT表現均較重,因此臨床表現常與胸部影像學表現不符合,需要引起臨床重視。
3.3病原學診斷方面 目前,《2015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性傳播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指南(續)-沙眼衣原體感染的診斷和治療指南》[12]、《歐洲沙眼衣原體感染管理指南(2015)》[13]和《梅毒、淋病和生殖道沙眼衣原體感染診療指南(2020年)》[7]均推薦核酸擴增技術用于CT感染的常規診斷。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法檢測CT的敏感性及特異性均很高[14]。鼻咽是圍生期CT感染最常見的部位,約有70%受感染的新生兒鼻咽部分泌物培養陽性。目前,臨床上多采用鼻咽深部抽吸物行CT的PCR檢測,若出現大于檢測下限的拷貝數即可確診。有研究發現,通過順產感染的CT肺炎患兒呼吸道分泌物中的CT拷貝數要明顯高于通過剖宮產感染的患兒[15-16]。
國內深圳寶安婦女兒童醫院研究人員報道大多數CT肺炎(84.2%)表現為普通病例,但是重癥感染的比例 (15.8%)依然很高[2]。而孟慶清等[17]報道重癥病例占26.5%。陳明等[18]報道重慶地區1~3月齡嬰兒重癥肺炎中CT檢出陽性率為7.1%。說明CT是導致小嬰兒重癥肺炎非常重要的病原體。研究發現,合并病毒感染更易發展成重癥病例;此外,CT肺炎嚴重程度可能與不同基因型有關[2]。同時,CT肺炎合并病毒感染可使發熱及喘息比例增加,喘息持續時間延長[19]。嬰兒單純CT感染一般癥狀較輕,若出現重癥病例,需警惕有無合并感染或患兒本身有無潛在的基礎疾病。
4 預后分析
CT肺炎經過規范治療后大部分預后良好,但近年來很多研究發現嬰兒期的CT感染與后期的呼吸系統功能障礙如哮喘等有關。CT可誘導PI3K/AKT/Bcl-2/Bax通路活化促進CD4+T細胞凋亡[20]、通過蛋白裂解、脫泛素作用、下調炎性細胞因子等抑制宿主細胞的免疫反應,導致持續感染[21]。由于CT在體內的長期復制,機體經歷漫長的氣道損傷過程,對其呼吸系統的發育留下隱患,并有助于一些慢性炎癥疾病的進展。在一項最近的美國研究里,在182例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兒中檢測142個患兒的衣原體DNA,結果顯示42%CT陽性[22]。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CT感染與喘息癥狀有顯著的相關性,是誘發兒童哮喘和反復喘息的一個重要因素。有文獻報道,嬰兒感染CT肺炎后7~8年,很多患兒出現肺功能檢測異常,大多數表現為阻塞性肺功能異常,提示嬰兒感染CT肺炎可能與兒童哮喘發作有相關性[23]。已有學者發現新生兒CT感染后,在學齡期發展為哮喘[24]。
低出生體重兒及早產兒的CT肺炎更嚴重,會出現呼吸暫停、呼吸窘迫,可能需要長期機械輔助通氣,容易出現支氣管肺發育不良,甚至死亡[25]。新生兒衣原體感染,特別是未成熟新生兒或早期新生兒,可導致氣道反應性增強、肺泡計數降低、肺泡結構改變、肺氣腫改變和肺實質喪失,從而使青少年和成人肺泡過度擴張[26]。多項研究表明新生兒時期的CT肺炎,尤其是早產兒,是持續到成人呼吸系統功能障礙的一個病因。
重癥感染患兒往往需要吸氧、無創甚至有創呼吸機輔助通氣,提示其肺部損害較重,比普通病例更容易發生慢性和遠期并發癥。盡管很多報道表明嬰兒期患CT肺炎與遠期的呼吸系統功能障礙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具體的機制仍有待闡明。
5 治療隨訪
CT肺炎的治療首選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因阿奇霉素在胃酸中比較穩定,胃腸道反應輕,半衰期長,給藥時間短,有更強的組織通過性,在肺組織中濃度高,抗感染療效好而被廣泛應用。阿奇霉素劑量10 mg/(kg·d)靜脈用或口服3 d,停用4 d為1療程,根據沙眼拷貝數、病情嚴重程度和治療效果,可用2~3個療程。但近年來有研究報道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包括阿奇霉素、紅霉素等有潛在的致命性心律失常和心臟性猝死風險,在低血鉀、低血鎂、低血鈣等電解質紊亂和心動過緩,尤其是QT間期延長患兒中更容易發生,在這類患兒中應慎用或禁用[27-28]。在使用阿奇霉素治療前及治療期間,應進行心電圖檢查[28]。若出現重癥病例或病情反復需警惕混合感染或大環內酯類抗生素耐藥可能。若有上述患兒應慎用或禁用的情況或有耐藥病例產生時,可考慮使用喹諾酮類抗菌藥物,但在小嬰兒中目前尚缺乏臨床使用經驗。CT憑借多種免疫逃避機制及特殊的兩相生活周期特點給疫苗的研制與開發帶來了極大挑戰,目前仍沒有可用于臨床有效的對抗衣原體的疫苗[29]。通過產前篩查、受感染母親及其性伴侶的治療來預防新生兒CT感染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策略。CT感染可能會引起后期的慢性呼吸道并發癥如肺功能異常、哮喘等,急性期治療出院后的積極隨訪也十分重要。
6 總 結
CT肺炎好發于3月齡以下小嬰兒,經陰道分娩獲得是主要感染途徑,臨床特點為咳嗽、無發熱或低熱、氣促、肺部濕啰音,可有喘息、眼部分泌物、常見嗜酸性粒細胞升高等。胸部影像學多表現為雙肺充氣過度、彌漫性間質和(或)實質病變。近年來,CT導致的嬰兒重癥肺炎比例有升高趨勢。CT肺炎大多數預后良好,但多項研究表明嬰兒期的CT感染與遠期的呼吸功能障礙、喘息性疾病如哮喘有關,具體的病因聯系還需進一步闡明。為了防止嬰兒期CT肺炎可能導致的遠期肺部并發癥,對CT的產前篩查、對感染孕婦的治療、對患CT肺炎患兒的規范合理治療及遠期隨訪具有重要意義。